孫昱瑩 李浩《鏡中的生活與智慧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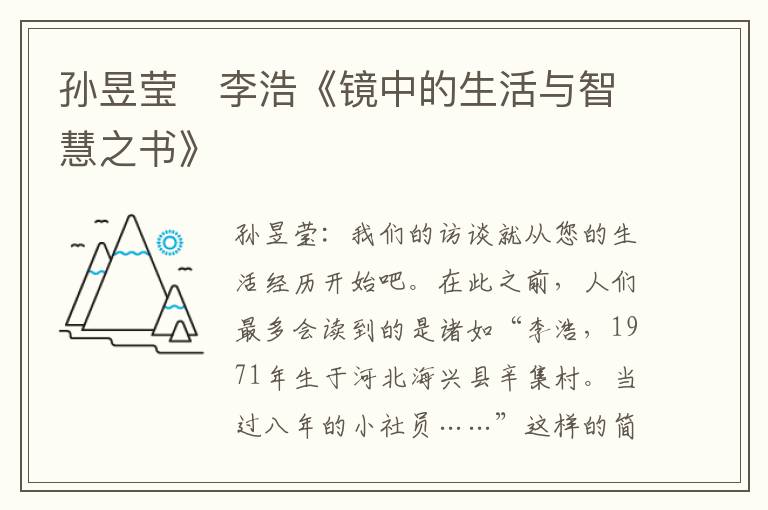
孫昱瑩:我們的訪談就從您的生活經歷開始吧。在此之前,人們最多會讀到的是諸如“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海興縣辛集村。當過八年的小社員……”這樣的簡要敘述。您對自己如何走上文學道路、在創作期間經歷過什么似乎說得很少。
李浩:是的,我承認我對自己的生活談得很少,而且也相對乏善可陳,我過著平常的日子,也甘于這樣的平常。記得在一本書中我曾讀到,福樓拜說,“藝術家(作家)應該讓后世以為他沒有生活過”,而布洛赫在談及他自己、穆齊爾和卡夫卡時說過,我們三個,不會給這個世界留什么個人的“信史”——我也極為認可這樣的行為。作為作家,我沒有留下信史的愿望,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存在超過作品的存在,哪怕是“影響到”作品的存在。所以我很少談我和我的經歷,不過,這么多年來我也很少談自己的作品,在課堂上我所講授的多是他人的、具有啟示性的經典。我更愿意對經典進行梳理,但愿有朝一日我在課堂上談及自己的作品并將它與經典并置,毫無愧色。哈,但愿不是因為臉皮的變厚。
多說幾句,我的經歷真的是沒什么,真的,我是書齋里的作家,主要是和書打交道,我的日常過于平靜……想想我的生活,有幾個點影響到了我的寫作。一是,在1998年左右,我得了一個奇怪的病,低燒,渾身乏力,疼痛。一年里我反復在縣里、保定和北京的醫院看病,卻時好時壞,難有緩解。后來我停了藥,“不管不顧”了,它反而慢慢消失,沒有再犯。那段時間讓我不得不想自己,想自己的生也想自己的死。《那支長槍》就是那時候寫下的,原來的名字叫“自殺,那支長槍”,在《人民文學》發表的時候李敬澤先生出于善意改了它。我還接著寫了另一篇——《生存中的死亡》……說我談自己的生活很少其實不恰當,我的多數作品都與我的生活和經歷有關,只是在小說中它們改頭換面。我將它們交給小說里的父親、叔叔、兄弟、張三或者李四,讓他們去承擔“必然的后果”,而我則悄悄地試圖溜走。另外一個點,是2004年,我去《北京文學》幫助工作,兩年的時間里讓我學到了許多。一是和北大師生們的接觸,讓我對學術理論的興趣更強了,一是《北京文學》的一個欄目“文本典藏”,作家們的眉批讓我極為受益。第三個點,是去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寫作,它讓我不得不梳理和整理,讓我不得不更深入、細致地對小說進行“解剖”,教學相長,我覺得其實我更從中有所得。現在,我到了河北師大,我愿意自己的所得更多一些,當然我也愿意能有好學生,我能在大學里培養出好作家——至少是,讓他們受到影響和啟發。哈,這些是我之前沒有談過的。
孫昱瑩:您小說里似乎有一種濃濃的孤獨感,揮之不去。它源自哪里?
李浩:它應當是出于天性,也多少出于我對世界的認知。我承認,某些后現代的理論對我產生了影響。許多時候,個人是不被重視和理解的,而個人理解包括他的社會理想總是在挫折和失敗中磨成粉粒,即使“理解”中也充溢著巨大的誤讀和曲解。同時,我也確實感到,世俗的巨大足以淹沒掉思考和個人的鋒利,何況我不是一個鋒利的人,在我天性里有示弱和妥協的成分。當然,骨子里也有相當凝固的東西,它時常和外在的表面發生碰撞。在一則隨筆中,我將個人的存在看成是一粒沙子,我對我自己進行追問:一粒沙,在沙漠中的存在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它存在嗎?它存在過嗎?它如何在那么多的眾多中呈現自己的存在?我思,我就在?
孤獨的另一個緣由是出于自身的封閉。我承認,在作家中,我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力較弱,我感覺,時常感覺,我和這個世界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我們相互照見,但距離永恒,無法相互融入。往往是,夜晚來臨的時候,我通過閱讀和寫作進入個人性極強的世界,這個世界和外在的世界缺少接駁與連通。在一篇小說中,我將自己看成是兩個,一個在白天生活,平常而正常,無冒險也無波折;另一個,會在夜晚變成鼴鼠,它有另一個不被人知的世界,這只鼴鼠在和一些死去的人的骨骼進行秘密交流。寫作,對于我來說一直是一面放置在側面的鏡子,它映照我的生活,只是左右時常相反。
孫昱瑩:“側面的鏡子”,您在其他訪談中提過,而且您的作品中也經常出現“鏡子”。對于“鏡子”,也許是老生常談,但我依然想問一下,鏡子在您的小說里面有怎樣的功能?為什么您愿意使用鏡子?
李浩:鏡子,首先是對寫作的隱喻,我愿意通過寫作這面鏡子寫下“我”和我的認知、理解、時而的情感。鏡子,它是觀看,我也愿意透過鏡子看見世界和他人,看見這個時代、這個世界的發生。雖然透過鏡子,“這個時代”與“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但,這既是沒辦法的事也是更為有意味的事,我其實對所謂的物理真實興趣不大。鏡子,也是創造之物,是人類創造出來幫助我們有更多發現的創造之物。我迷戀于創造,迷戀于創造的隱喻——我覺得我們對他人作品的閱讀也應算是一面鏡子,借以了解和認識“他人的生活”。還有一點,我的鏡子不只是日常的玻璃鏡,它還有古典的銅鏡,有哈哈鏡,有顯微鏡,有三棱鏡……有人說作家應是人類的神經末梢,借助這些不太一樣的鏡子,我覺得更會發現和認知“這個世界”,并完成自己的創造。
孫昱瑩:您的小說有很強的寓言化傾向,即使那些寫下故事的、很生活化的小說。我想問的是,您是怎樣書寫這類小說的,是受到生活的某個點“激發”,讓您覺得不得不寫,還是心里先有一個想法,然后再為它找素材和表現方法?
李浩:很好的問題。我知道你也是作家,首先是作家。在寫作中,這兩種情況都有。被生活激發的小說我寫過,像《爺爺的“債務”》,不過這類小說在我的寫作中占的比例很少很少。我的寫作大部分是“概念先行” 、“思想先行”,也就是說,每寫一篇作品,我都要想,我的這篇小說(或是詩歌)有無獨特的發現和提供?它是不是具有強烈的個人性?同時,我也要問,它在說什么和怎么說上是不是達到了我能力的極盡?還有沒有更好的可能?我在這篇文章中有無媚俗或媚眾的傾向?在此之后,我覺得我的這篇小說有一些個人的思考在,它在當下的寫作中有一定的異質性,至少和中國其他的作家有所區別;同時它又是藝術的,有著結構和語調上的美感的,才開始寫。當然,部分小說是出于怕自己長時間不寫手生而勉力寫出的。我承認我也寫過一些相對“通俗”的小說,過去是一年一篇——不過是想表明,你們玩的這些我也會,但它不在我的視野內。哈,當時年少輕狂啊。
在我看來,小說應當是對人的追蹤和塑造,是對人性隱秘的探尋與挖掘。在我這里,寫人和寫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當下的小說,寫事的多,寫到人的很少,當然,事寫好了也是非常偉大的,我只是標明我個人的趣味和傾向。我想,“我思,故我在”能很好地說明我的寫作:如果取消小說中的思考和智慧成分,我的小說的存在也就可以取消了。再次重復一遍,我愿意,把我的小說變成一種“智慧之書”。
孫昱瑩:您不止一次談到“智慧之書”,究竟什么樣的小說可謂“智慧”?寫當下生活的小說在您看來就不“智慧”了嗎?
李浩:挖得好大坑。但我不準備跳。寫生活的當然可以智慧,它甚至會超出作家思考的困囿,“比作家本人更聰明”。我在講座中曾反復以安布魯斯·比爾斯的《鷹溪橋上》作為典范性例證,作家的本意中包含有種植園主貝頓·法夸“罪有應得”的意思,他甚至強化了這一點,但,我們還可讀出的、更愿意強化的卻是另一點,對生命的悲憫,對生命價值的吁嘆,以及對戰爭殘酷性的反思,是一種人人可能處在的境遇的可能……小說這方面的價值更值得珍重。《包法利夫人》,作家寫作的主旨是諷刺,諷刺女主人公瑪蒂爾德的驕奢虛榮,并借用小說虛構的力量對她進行了懲罰……說實話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這篇小說的“立意”并不高,一般社會小說而已,但它所透露的另外的氣息卻是更有重量的,譬如畢飛宇談到的“責任和契約”,而我也愿意把目光注意到那個被忽略著的男人,瓦爾賽,瑪蒂爾德的丈夫,愿意借用小說的描述審視和體諒他的心理……在許多寫生活的小說中,像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奧布萊恩的《士兵的重負》、尤迪特·海爾曼的《夏屋,以后》……它們寄托了我的敬重。
我說的智慧之書,我還是先引用米蘭·昆德拉在《耶路撒冷致辭:小說與歐洲》中所說的話吧,智慧之書的理念首先是源自于他。他先是說明,小說的智慧不同于哲學的智慧,小說的智慧不是從理論精神而是從幽默的精神中誕生的;在生活被“表現得如同一條簡明易懂的因果成敗的軌道”的時候,小說卻建立了繁復的、歧義的、忐忑和兩難的另外向度,它審視流行思想,激發人貯含的詩性和幽默感,與媚俗傾向做斗爭……我覺得小說在講述故事的同時應引發思考,我們會和小說的主人公一起經歷,然后出自于他的內心向生活和命運追問:我為什么如此,我們為什么如此?有沒有更好的可能,我們該如何選擇更好的可能?能讓我們在感動、吁嘆和同情之余發問的小說即是智慧之書。
這一智慧,不是寫作者掌握所謂知識的多少,更不是知識的羅列。任何一臺電腦都會比作家們“知道”得多很多。問題是,智慧的小說會引發思考,同時它也不具備現成的、唯一的答案。我還想強調一點,就是,智慧小說的發問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它有具體的所指但更有普遍性。它會超越時代、具體環境和個人性格的困囿。
孫昱瑩:在您的小說寫作中,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想表達的東西?我看到《文學報》的采訪中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近十年時間過去了,您有沒有產生新的想法?
李浩:你不問我,我倒是明白的,而你一旦問我,我忽然覺得,一時還真不好回答。有,這個一以貫之的想表達的東西一直有。其實它的變化不大,只有微調。在那個訪談中,我談到,最早,我的想法是“為小人物立傳”,寫下卑微的生存者們的生存背影,寫他們的卑微生存和在這份生存中的自私、善良、愿望、怯懦、虛偽和隱秘的惡、世故和不抱希望。后來有一段時間我轉向對“理想”這個詞的思考和打量,寫下了《如歸旅店》、《失敗之書》等等。再后來,另一階段,我對知識分子們的命運感興趣,我想寫出他們在知識理念和生活理念之間的掙扎與妥協,我想寫出他們的盲從,我想寫出他們的傲慢中的怯懦與虛榮……時下,我想對我們人類尤其是我們民族中的“隨世俯仰”、“不思考地跟隨”提出自己的警告,它,或許會成為下一個核心。博爾赫斯有篇小說,《創造者》,他說一個野心勃勃的創造者用一生的精力畫下了一張世界地圖,并力求讓它真實。而等他完成這張地圖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他畫下的是自己的那張臉”。我寫作的題材和類型大約可以說是豐富的,有農村題材、歷史題材、現實和非現實的、中國的和外國的、幻想的和夢想的,有魔幻的、荒誕的,也有兒童文學、詩歌、散文和評論。如果談論一以貫之,它卻是在著的,一直在著的:那就是對自我的書寫,它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體驗和情感,它表達我在生存中的愛與哀愁、期望和幻想。我希望我的寫作能勾勒出“自我的繆斯獨特的面部表情”。
孫昱瑩:您的小說中,有一些是虛化歷史和現實背景的,請問這樣的虛化是出于怎樣的考慮?是您不愿意去,還是無法書寫現實呢?
李浩:說我寫不了現實多少會讓我窘迫,我很想反駁你……其實我寫了很長的一段話,不過它們被刪除了。我不做太多的辯解,因為仔細想想,我的確對現實生活缺乏敏感,即使是現實感受,我也愿意用隱喻的、變形的、曲折的方式來完成它。像《使用鈍刀子的日常生活》、《丁西和他的死亡》即是。
背景的虛化是出于我的故意。在一則訪談中我還曾狂妄地戲稱: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把我以后的小說都放置在任意的一個時間點或空間點上,唐朝、明朝或者維多利亞時代、魏瑪時期……我承認,小說貼近現實的好處是,它會極大地、充分地調動和你同時代、同經歷、同感受的人的參與感、認同感,他們也會將自己的經歷、感受“補充”進去,為你的“未及、未盡”之處直譯,拓展甚至是豐富性地、有著某種過度闡釋地拓展你的“言外之意”。我當然清楚閱讀的這一心理,因為,我在閱讀同時代的現實作品的時候也是如此。但,我更愿意多想,更愿意思考在這個時代過后的可能。對此,哈羅德·布魯姆有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在《史詩·前言》中說:“隨著我們的社會(遲緩地)改變偏見和不公,如今所謂的‘相關性’,不出一個時代,便會被棄擲在垃圾桶。文學與批評界的時尚人士總會有衰退過時。結實的老家具尚可作為古董流傳,而糟糕的文學作品和意識形態的勸誡不會有這樣的命運。”他說得比我好。
背景虛化,更重要的一點是我想寫下的是人和人類的共通問題。它不是針對一個人的,不是一個時代的,我更看重永恒性,更看重伴隨我們人類而無法隨時間、時代和區域解決的那些“問題”,它,可能更是核心性的,也是我愿意付諸心力思考和追問的。我愿意我的小說在一個英國人看來,一個德國人看來,一個日本人看來都不“陌生”,也有對它的認知和闡釋;我愿意我的小說能比我活得更長久,我們時代的一些依附性的、制度性的問題或許在下一個時代能夠得以解決,無論解決之道是不是完美;但還有些東西是下一個時代也要面對的,我愿意我的寫作,能和留到下個時代的它發生關系。
孫昱瑩:您把許多的作家、哲學家的名字鑲嵌于小說中,讓他們成為主要的或次要的人物,是想說明什么呢?開個小玩笑,這里似有顯擺閱讀量豐富的成分。
李浩:我要是回答“有”呢?的確,有。我甚至可以進一步剖析我的心理:我的學歷低,許多的學習都是“自我教育”,往往自我缺乏什么的人才更會反復標榜自己有,自己懂,我也是如此。你的問題讓我羞愧。
不過,把作家、哲學家的名字鑲嵌在小說中,一方面是出于游戲,部分地顯擺,一方面是受博爾赫斯的“毒”太深,還有一方面是,我覺得借用它們可以對我的小說“言外之意”進行某種豐富。就像中國詩歌中的“用典”那樣,如果你熟悉這個作家、哲學家,可能會把他的思想、他的寫作旁騖地想一下。而我的這個小說中,如果他和那位作家、哲學家的思考有某種同構的關系,那么,那位作家、哲學家的思考就得以部分地注入我的小說和想說中了。我的鑲嵌和博爾赫斯的方式不同,我有個個人的前提,就是,假設你不知道那位作家、哲學家和他們的著作,在閱讀這篇小說的時候應不受大的影響,那些旁加的豐富是“意外”,就像寫作現實小說閱讀者愿意給予的注入一樣。我不對它依賴。
孫昱瑩:在吸取西方經驗和寫作中國故事的問題上,您是怎么考慮的?
李浩:我是個“拿來主義”者,我愿意把一切的好、一切可為我所利用的東西全部地拿來,無論它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我不會因為地域而排斥任何一種有效知識,也不會因為地域性而對它高看。我寫下的一切都是中國故事,更為逼仄一點,我所寫下的都是“我”的故事,哪怕小說中的“我”是父親、小丑、皇帝或銀行職員。
當然現實生活的給予在小說中是很重的支點,這一點,我們無法回避。而且,有一句片面深刻的話,它說“所謂個性,本質上就是地域性”——我部分地認同這話的合理,中國是我的寫作建立個性、建立陌生感的一個重要路徑,我當然要好好地利用、使用。沒有陌生感的小說是平庸的。而地域性、民族性差異是在人類共通情感和命運的基礎上保留陌生感最多的地方,我可不能在這點上輕言放棄。《失敗之書》,我寫下的那種失敗感的零余人全世界都有,這有它的普遍性,但把失敗歸罪他者,向家人施虐讓家人承擔更多卻多少是“民族性”的,沒有它,我的這篇小說可能不寫。《被噩夢追趕的人》,我寫下的是怯懦的愧疚,它也有某種共通性,而為了減弱自我愧疚的“救贖之路”卻有民族不同。我說,“救贖”,大約是一個舶來的詞匯,我試著讓它在我的小說中落地生根,看它在我們的國民性中會有怎樣的特質和異質:首先,它來自于內力、外力的被迫而非宗教感的自愿,假如不是自己的內心難以安撫,噩夢連連,肖德宇未必會讓自己走向什么救贖之路;其二,避重就輕、自我麻痹始終伴隨著整個救贖的過程,它甚至會在救贖中產生崇高感;其三,個人的救贖并不是完全由個人承擔的,其中的“代價”時常會轉嫁與分攤,他有意無意中減少自己應有的責任——在最后,肖德宇的救贖變成了對弟媳趙寧生活和自由的干涉,留住趙寧成為他救贖的一個部分,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我所見的人與事中,這種轉嫁型救贖相當普遍,他們和我(我不認為我有特別的豁免權,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分子)有時會道貌岸然、義正詞嚴地將個人的救贖代價轉嫁出去,做得相當心安……這段話,是我的創作談里的,你也許讀到過。我希望我的小說,使用著全世界最有效、最有趣味和美感的技巧,呼應或回答全世界最普遍最核心的生存問題,而它,又具備強烈的民族異質——中國故事。
孫昱瑩:您寫下了那么多的父親形象,這些父親各有不同,我想問的是,小說中的“父親”和您生活中的父親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李浩:我說過“父親”是一件制服,它更多是象征性的,它象征著“父權”,是我們生活中最先出現的那個男人,象征歷史、政治、權威、力量、責任,象征經驗,象征面對生活的態度和可能的態度,象征我們生活中需要正視也必須正視的堅固存在。它也象征懲罰和懲罰的可能,象征權力和它的欲望,象征它能夠達到的和無能……我幾乎把我所想到的象征都塞給了這個“父親”,偶爾他會化身為兄長,或者其他的什么人。
這個“父親”,當然部分地來自于我的父親,但不會全然是他,我覺得我塞入的“我”會更多一些。那些令人羞愧的、不愿啟齒和面對的部分我都讓“父親”來承擔了,這多少會讓我下筆的時候“手不軟”,更心安理得一些。小說中的“父親”還有部分來自我的姥爺,《那支長槍》里姥爺的成分和“我”的成分更重。此外,還來自我的四叔、我的弟弟、我身邊的朋友和親戚……小說,從來是混雜的結合體,它的取自也從來不是單一向度。
孫昱瑩:《那支長槍》是您較早的作品,里面的“父親”為什么一次次地“鬧”自殺?他的死,在小說的設置中是他繼續的“鬧”還是真的想要死了?
李浩:是的,是我早期的作品,它的存在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感謝你注意到“鬧”這個詞,父親的自殺是“鬧”,是他喚起別人注意、憐憫進而體諒的一種方式,是弱者的稻草,關涉他的尊嚴和隱秘的渴望。在小說中,我也借他的口說出他怕死。他不愿意死,雖然生所能給予他的實在是少,而且越來越少。但他還是怕。最后,他把自己吊在樹上——這依然是“鬧”,不過很不幸的是這次的“鬧”導致了他真正的死。其實,這篇小說的寫作,其原點在這兒:很早之前,我讀到一家地攤上的舊報紙,上面用嘲弄的口氣寫下一則奇聞,說一個在村上很怪的人,總是捉弄人,總是鬧自殺,結果最后他真的自殺了,他把自己吊死在樹上,腳底下是一面銅鑼——他其實是想,把自己吊起來然后敲鑼,把村里的人召喚過來救他,可是等他踢倒了凳子卻再沒氣力敲鑼了。于是,有了那樣的后果。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也跟著發出嘲笑,只把它當成是一則奇聞,天下之大當然無奇不有……直到我在病中,直到我感覺自己“離死亡不遠”了,作為一個庸碌無為的小職員,一個不被注意的小人物實在有所不甘。于是,一個去買早餐的早晨,我望著在路邊樹上掛著的黑色塑料袋忽然想起這個舊報紙上的故事,于是有了《那支長槍》。父親的那些心態,是我的,我也猜度是我姥爺的,是我們這些人這類人的。
孫昱瑩:是不是可以將此闡釋為您對“文學的”和“生活的”不同理解?
李浩:當然。生活提供素材,提供可能,但小說是寫出來的不是生活生出來的,從生活到小說需要經歷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變動。納博科夫說:“我們可以這樣看待一個作家:他是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師。一個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師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為大作家,得力于此。”我極為認可這一點。他還有一句有些苛刻的話:“文學是創造。小說是虛構。說某一篇小說是真人真事,這簡直侮辱了藝術,也侮辱了真實。”我也認可這句話。
孫昱瑩:我注意到,2016年,您在不同的刊物發表了數篇《會飛的父親》,有四篇,五篇?您已經寫了幾篇?打算一直寫下去?它們的同和不同在哪兒,為什么這樣去寫?
李浩:2016年,我發表了四篇《會飛的父親》,2017年3月可能還會發表一篇,之后,我還會寫數篇,爭取出一本小說集,全部收錄我的這些《會飛的父親》。它是游戲,也是自我考驗,我看我就這個有限制的題目還有多少想說,能說,我還能不能找到新可能。他們當然有不同的負載,我讓每一篇《會飛的父親》承擔不同的“問題追問”。第一篇,父親的飛走屬于想象,他缺位于生活,因此讓兒子通過記憶和來自于生活的證詞“幻想”了父親的飛走,這份想象里有避與諱,有高大化、偉岸化,而部分地忽視真實與合理——我們的歷史書寫往往是如此的,我們愿意塑造一個“那樣的父親”,“那樣的歷史存在”,而不愿意“看到”確切和真相。第二篇,父親的飛走同樣是不存在的,而且這一次,我更將他按入沉實的生活中,讓他沉入到泥漿里——他的走,無論是飛還是別的,都不過是想辦法“透口氣”,他還要落實于生活,但沒有這個透口氣的飛走和離開,生活的無望和無力會讓他悶壞的。我愿意指認,我們的生活日常需要這樣的“出口”,即使是那些卑微者。第三篇,我干脆把“飛走”的愿望壓得更實,更不可能(父親因車禍,坐在了輪椅上),那這一愿望也就變得更為強烈了。開始,我想讓父親走向陽臺或一個高坡,但后來否決了:它會落入到俗套,不能如此。于是,我讓愿望只是愿望,成為一種含在父親心中的“泡沫”,它甚至不易顯現。第四篇,是一篇元小說,是我對第三篇《會飛的父親》構思的經過,包括先想到的什么,改變了什么,故事的走向在什么地點發生了改變,我想塞入的寓意又是如何一波三折地變動的。第五篇,我改寫的是希臘古典神話中一個著名的故事。匠人代達羅斯和他的兒子被困在國王的迷宮里,父親帶著兒子穿越迷宮,他們飛向高處,大約是出于傲慢和好奇,兒子忘記了父親的警告而朝太陽飛去,結果熾熱的陽光烤化了粘著羽毛的蠟,兒子伊卡洛斯掉入了海洋……既然是改寫,我就必須注入不同和新意,在這里,在舊有的神話故事里,我加重了父親代達羅斯的妒忌和其他,在繼續保留他工匠身份的同時又為他注入“怯懦”、“麻木”、“酒徒”、“缺乏道德感的人”、“施虐者的幫兇”和一些其他的“壞品質”。我也加重了對國王彌諾斯的筆墨,他的暴虐、無情、殘酷、傲慢、孤獨,甚至弱小……進一步,我取消了神話中那頭著名的魔獸,它是不存在的,是國王彌諾斯一種虛張的恐嚇,他所建的迷宮不是為了存放兇狠的魔獸,而是存放自己,包括自己的孤獨和恐懼。依靠暴虐統治的國王們都可以說是恐懼癥的受害者,彌諾斯當然也是。他只能在誰也進不來出不去的迷宮里才能獲得短暫的安全感。接下來,我也置換掉兒子伊卡洛斯掉入海洋的原因,在這里,他不再是傲慢和好奇,而是對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新生活”的厭惡與恐懼。離開迷宮和國王彌諾斯,會有新的彌諾斯在等待他們,而這個父親也依然是舊父親……他朝向太陽的飛翔其實是一種自殺行為,是擺脫。我還準備繼續寫后面的《會飛的父親》,前提是,它們必須和前面的言說有巨大不同,有新意和另外的敞開。我愿意將它變成“嚴肅的游戲”。
孫昱瑩:2012年在成都,我們在《作家》雜志的文學活動上第一次見面,我還記得那時您跟我說過“復眼式寫作”,當時這個概念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直到閱讀了您的作品,才明白您說的“蜻蜓式的復眼”。當然,我希望在此聽您詳細闡釋一下這一理論,因為我確是希望將來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出現這一詞條。
李浩:是的,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談論薩爾曼·拉什迪。我冒昧地給出了“復眼式”寫作這一命名。這一命名源自于我對君特·格拉斯的小說、對拉什迪小說的閱讀。在我看來,他們是有復眼的作家,那種饒舌卻趣味盎然、無限豐富的寫作讓我著迷。他們的寫作有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繁雜、多意,每一處都是有光的,甚至會讓故事的前行變得緩慢。我認為,這種“復眼式”使得現代史詩成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