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玨《飛行的土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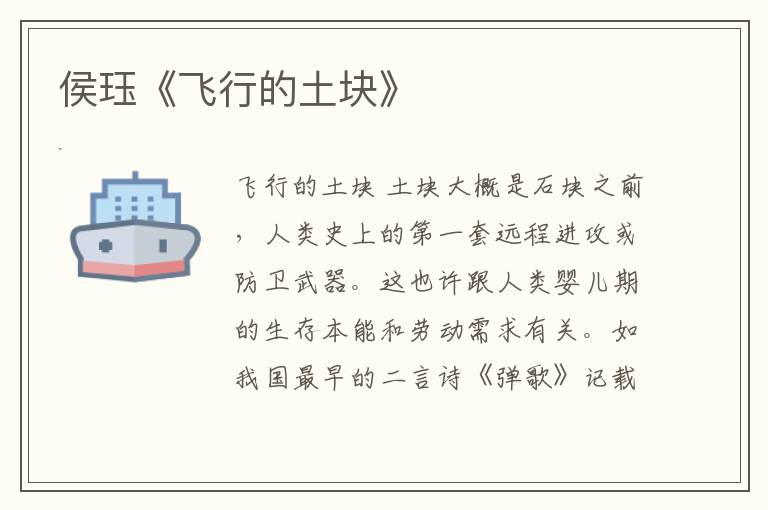
土塊大概是石塊之前,人類史上的第一套遠程進攻或防衛(wèi)武器。這也許跟人類嬰兒期的生存本能和勞動需求有關(guān)。如我國最早的二言詩《彈歌》記載:“斷竹、續(xù)竹,飛土、逐肉”。遠古時期的人們,使用竹枝或竹竿制作標槍,來捕獵禽獸;利用結(jié)硬的土塊或粘土捏成的泥團,驅(qū)逐那些偷食的鳥雀與碩鼠。鳥雀與碩鼠,目標小,動作極快,非使用土塊實施遠程射擊不可。
后來武器進步了,土塊就退出歷史舞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說,“夫飛土逐肉,兒戲之常。”可見在古代社會,在刀光劍影和大型投擲器械之外,人們用泥巴丸子攻擊小動物,仍然是一種很常見的活動。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遠古人拋擲土塊抵抗自然入侵,到紀曉嵐所生活的時代,已經(jīng)變成孩童游戲。
孩童游戲的行為模式,既是成人社會活動的投影,同時也一定攜帶著歷史深處的訊息。鄉(xiāng)野孩子玩過家家,尿尿淋濕泥土,然后捏成團,壓成片,塑成拇指大的小碗、湯勺、小人兒之類,便是原始社會人們制作陶器的第一道工序步奏,也符合女蝸摶土造人這一類神話傳說的審美心理。至于大一點的頑皮男孩,喜歡隨地撿起土塊互擲對方,俗稱打泥巴仗,所反映的歷史內(nèi)容,或許應(yīng)該是數(shù)千上萬年前原始部落間攻伐戰(zhàn)爭的圖景吧。
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城里還是鄉(xiāng)下,對于水和泥土的熱愛,是孩子們天生就有的心理和感情。他們不在乎雨水淋濕衣服身子,不在乎鞋子是否需要保持干燥,總喜歡跑進雨中體驗被淋濕的愉悅,喜歡踩進水洼尋找樂趣。當然,他們也不在乎大人洗衣服的辛苦,不在乎雙手是否會感染細菌,只要遇見沙堆或者裸土,就會情不自禁地蹦扎過去,玩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遺憾的是,我們成人往往不知其天性,經(jīng)常使用言語恐嚇,甚至棍棒伺候,硬要剝奪孩子們的天性本真。難道我們和孩子之間,真是文明與野蠻、開化與蒙昧的對立面嗎?
其實每個孩子的內(nèi)心,都居住著一個神靈。自從第一聲啼哭起,他們就可以感知萬物,與萬物通靈,只不過他們尚未掌握言語表達罷了。
神,總是沉默的。因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無名才是萬物之始。而我們往往出于世俗的目的,過早剝奪了孩子們珍貴的神性。
人的生命從土地汲取能量,最終又要回到土地中。土地的神奇,在于她所呈現(xiàn)的豐富生命體,所謂厚德載物。現(xiàn)在看來,在農(nóng)村度過童年時期的一代人,是多么的幸福,而這無關(guān)貧富,無關(guān)疾苦,只關(guān)乎想象力的發(fā)育和自然心智的成長——因為,這是土地直接給予我們的禮物。
我慶幸自己生于鄉(xiāng)村,長于鄉(xiāng)村,在山鄉(xiāng)生活了十五年,那可是一段金子般閃爍的歲月。
我的家鄉(xiāng)在黔湘桂三省交界的丘陵山區(qū),那里泥土的數(shù)量僅次于空氣。人們與土地的關(guān)系十分直接、自然、親密,并不像大城市里,土地被鋼筋水泥包裹,山地在郊外,路途遙遠,孩子們難得一聞?wù)嬲哪嗤练枷恪E紶柸セB市場買個盆栽,塑料盆裝好的一撮土壤,還放滿了花肥,根本看不到蚯蚓的勞作。超市賣給孩子玩的橡皮泥,徒有泥字,卻早已失去泥土的本質(zhì)屬性和趣味。
四季分明,相時而動,我們童年時代的游戲,是跟隨著季節(jié)的變幻而變化的。春天來了,萬物萌動,草長鶯飛,我們這群野孩子,自然也不會浪費片刻光陰,只要有機會玩鬧,就不會讓自己消停。
“布谷,布谷”,當村莊四周山谷草叢里傳來布谷鳥的叫聲,所有人的腦海里立即浮現(xiàn)出一副畫面:光滑筆直的金竹筍破土而出,山坡上的蕨菜紛紛張開毛茸茸的小拳頭,身體像卷尺似的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往地面提拉起來。沒出幾天,走在村里的石板巷道上,就可以聞到竹筍炒臘肉或者蕨菜炒臘肉的香味。
“轟隆隆,轟隆隆”,春雷在天庭滾動,把沉睡在泥土中的娃神和蛇神給吵醒了。蟄伏了一個冬天的村民,鼓足了勁,聽從雷公的召喚,扛著打磨得鋒利無比的農(nóng)具,紛紛牽牛出門春耕。大人們用鋤頭或者鐵犁,把稻田里封凍僵硬的泥土,一寸寸翻松,一畦畦犁開,放眼望去,仿佛大魚背上的鱗片全都豎了起來。大地再一次張開了無數(shù)個小嘴巴,等待農(nóng)人播撒種子與禾苗。在谷雨來臨之前,人們還沒有放水耙田,翻耕好的新鮮泥土,一團團裸露在空氣中。那可是我們?nèi)≈槐M的武器和玩具。
林溪河從東北方向的山地流下來,到文大村附近拐成一個S形,在上下游兩岸形成兩處河灣臺地,那是人們世代耕種水稻的沃野。有一條沿河公路蜿蜒穿越山區(qū),向北伸向湖南省邊境。公路兩旁坐落幾個自然屯,好比一根藤蔓上幾張對稱的葉片。文大中心小學是掛在葉片之間的果實,與我們文塅屯隔河相望,相距大約兩公里。
每天傍晚,我們一群野孩子從學校放學回家,總不喜歡走尋常路,放著順溜的公路不走,偏偏要踩過一壟又一壟翻耕過的田野,把鞋子踩臟了,被毒蛇驚嚇了,也在所不惜——大家都是為了能夠打一場酣暢淋漓的泥巴仗。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十幾個同學,一般分成兩個陣營,按村頭寨尾的原則迅速組合。有時也插入外村的陣營,形成三方面作戰(zhàn)格局,不過那比較少見,因為回家的路途不一致。隊伍分配好之后,隨便哪個伙伴都可以發(fā)出作戰(zhàn)信號:開始啦!一瞬間,所有人一哄而散,尋找有利地形準備發(fā)起攻擊。動作神速的同學,早已抓起一塊土疙瘩,向敵方目標最明顯的人飛射出去。只聽見啊的一聲慘叫,我們就知道有人中彈了,自己也下意識舉手作防衛(wèi)腦部的動作。
戰(zhàn)斗的激情往往需要一方強烈反攻,才能充分燃燒起來。人們的智慧在敵我的劇烈沖突里爆發(fā)。那時我們年紀尚小,也就是小學二三年級的樣子,卻很快學會了聲東擊西、左右兼顧、以攻為守、趁火打劫、圍魏救趙之類計謀。
打泥巴仗游戲有兩種形式,其一為陣地戰(zhàn),另外是游擊戰(zhàn)。陣地戰(zhàn)一般是兩邊人馬約定好,選擇兩塊足夠大的相鄰稻田,各自占據(jù)其中一塊,以橫在中間的田埂為界限,互相扔泥巴砸往對方,其格局與乒乓球臺相似。雙方做好準備以后,也沒個帶頭的人發(fā)號施令,冷不丁從角落里飛來流彈,有人應(yīng)聲破口大罵,戰(zhàn)斗即打響。
如果選擇陣地戰(zhàn),兩邊人員是不能逃開各自陣地邊界的,也沒有規(guī)定的時間限制,想要結(jié)束戰(zhàn)斗,非得等一方主動表示投降為止。這種正面強硬對抗的游戲,考驗的是手臂力量、身體躲閃外來攻擊的靈活度以及強大的心理耐力。
被翻耕過的稻田,坑坑洼洼的,我們一方面要時刻注視對方的陣型變化、攻擊方向,一方面要后退、彎腰、雙手撿拾土塊、起身前進、瞄準目標、掩護隊友、連續(xù)射擊、迅速躲閃……稍微不慎,就會被腳下的坑洼絆倒,或者與隊友沖撞,乃至被對方飛來的“炮彈”擊中。
投擲土塊的姿態(tài),與士兵扔手榴彈的動作十分相似。有時候我們這一方忽然喊口號,大家齊刷刷地,瞄準對方某個人或某個危險逼近的射擊點實施飽和打擊。頓時萬土齊發(fā),泥土如雨,聲勢兇猛,給對方以極大震懾,有時我們也受到對方的集中火力阻截,躲不過,逃不掉,疼得哇哇叫。這種飽和打擊的方式,主要看速度與配合,一般是每個人雙手拿兩塊泥巴,擲出去一塊,接著再擲一塊,多個人連續(xù)集中轟炸一個戰(zhàn)術(shù)點。那樣的話,敵方最兇狠或最衰弱的一個人,逃也逃不掉。有時也根據(jù)對方火力發(fā)射的規(guī)律,不講集體配合,靈活反擊,各自盯住對方某個人,讓對方戰(zhàn)士背后受敵,淬不及防。
在防御方面,首先要看你彎腰和躲閃的速度,因為自己手上的土塊打完之后,馬上要取新的上來,不然在彎腰那一瞬間,對方的飛彈就會趁虛而入了。其次,要看己方人員互相掩護的默契度,當你在彎腰裝彈時,戰(zhàn)友需要立即補上,用火力掩護,防止對方背后打冷槍。然而這一切的配合,都不需要言語溝通,因為經(jīng)過長期的訓練,大家已經(jīng)心照不宣。
一些力氣大的孩子,可以抓起比較大塊的泥土,像西瓜那么大的一坨,作為超級重型武器轟炸對方。這是我們最快樂的場景之一。那個能夠掌控重型炸彈伙伴,會得到大家的熱烈歡呼。歡呼聲中,對方誰要是被砸中了,所有人都會笑到肚子抽筋,他則痛到家了,捂著滿頭碎泥或者被砸淤血的脖子,自認倒霉。重型炸彈的缺點是,射程比較短。而想要瞄準對方火力比較活躍、躲得比較遠的人,則可以拿雞蛋大點的硬土,進行遠程射擊,實現(xiàn)精準摧毀目標。
陣地戰(zhàn)是一種傳統(tǒng)的戰(zhàn)術(shù),參與戰(zhàn)斗的孩子極易體驗到正面武力對抗的樂趣。不過,有時候大人卻很討厭我們搞陣地戰(zhàn),不僅因為我們作戰(zhàn)時跑來跑去,必將大人辛苦翻耕好的田地踐踏回原形。還因為我們長時間互相拋擲土塊,擾亂了稻田的泥土構(gòu)成。比如說,甲方所在陣地,是東家的田地,東家媳婦很勤快,經(jīng)常挑一擔擔牛糞來倒進田里,日積月累,她家稻田的泥土就變得黝黑肥沃,稻谷產(chǎn)量很高;而乙方所在陣地,是西家田地,西家人管理無方,稻田的基土干巴巴,顏色灰白,比較貧瘠。我們這群野孩子才不管這些,開戰(zhàn)時,把東家田地的大量泥土甚至牛糞一股腦拋擲到乙方的陣地,乙方則用西家田地比較貧瘠的泥土悉數(shù)折騰過來,一來二去,東家媳婦等于無形中為西家干活,西家人平白無故占了便宜。這樣的結(jié)局,大人們肯定不愿意看到。
游擊戰(zhàn)方面,是甲乙雙方兩個縱隊流動作戰(zhàn),有時候我們一方集中防御,集中打擊,有時候分散包抄,趁勝追擊。這種戰(zhàn)術(shù)既考驗個人能力,也考驗集體的戰(zhàn)略。一些不夠沉著冷靜的小伙伴,往往會被敵方打的很慘,措手不及之間已經(jīng)遭受對方伏擊小隊泥石流伺候。
由于沒有場地界限的限制,我們有時候可以跑出戰(zhàn)斗地點很遠,讓對方打不到自己,然后趁對方不注意又去發(fā)動奇襲和偷襲。游擊戰(zhàn)也是運動戰(zhàn),大家一邊跑回家,一邊攻城掠地襲擊對方。從學校一路打到家,往往粘上一身泥土。好在清澈的林溪河從我們村口流過,我們結(jié)束戰(zhàn)斗之后,一伙人沖進河里,一邊清洗衣服和書包,一邊繼續(xù)打水仗。
有的同學頭發(fā)全部被搞臟了,有的同學鞋子也跑爛了。那時候農(nóng)村普遍比較貧困,爛了鞋子,不容易換新的,所以不少家長反對我們這群野孩子打泥巴仗。他們心底里是出于經(jīng)濟上的考慮,至于孩子是否受傷,他們并不在意——“摔摔打打,快長快大”,是一句古訓。
當然,我們小伙伴隊伍中,也有一些不太老實家伙,在打泥巴仗過程中違規(guī)使用石頭。這是最為恐怖的事情,有時人被打中要害,如太陽穴被擊中,就會暈了過去,甚至被送去醫(yī)院。血流滿面的情況也有,這樣的話麻煩就大了,會驚動到家長,誤了農(nóng)活,嚴重的話還會引發(fā)家長參與,發(fā)生家庭和家族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們在打仗前,一般會商量好規(guī)矩,諸如不能用石頭、牛糞,不能跑進菜園之類,如果誰率先破壞了規(guī)矩,那么下次玩游戲時就不會要他參加。這也是我們?yōu)槭裁匆话悴粴g迎外村孩子參與游戲的原因,因為隊員不太熟悉,戰(zhàn)斗就不太保險。
拋擲土塊的歷史非常古老,它源于人類最初跟大自然打交道的經(jīng)驗。那些土塊,延長了人類手臂的功能。人們?yōu)榱松妫坏貌荒闷鹞淦鞴ぞ撸舢愵惖娜肭帧M翂K作為武器,其實還殘留著遠古部族戰(zhàn)爭的影子。戰(zhàn)爭可以促進武器的發(fā)展,卻改變不了其基本動作和模式——發(fā)射彈藥和攻擊目標。比如古代很多拋擲石頭的吊裝武器,山寨、城堡防御戰(zhàn)中的滾石戰(zhàn)術(shù),懸崖山道伏擊戰(zhàn)中的居高臨下阻擊,乃至后來的手榴彈,火箭彈、巡航導彈等等。
人類活動空間的拓展,與動力系統(tǒng)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動力系統(tǒng)的改進,讓人類在物理世界獲得了巨大的自由。從拋擲土塊,到發(fā)射弓箭,子彈導彈,火箭和衛(wèi)星,宇宙飛船……相比而言,我們少年時代打的泥巴仗,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兒科了。
不過從本質(zhì)上看,兒戲之中確有大學問。至少通過打泥巴仗這項游戲,我們農(nóng)村娃親密接觸了泥土,對土地產(chǎn)生了深厚的情感,同時也學會了團結(jié)協(xié)作的族群生活精神。可以說,我們在幼年階段的手部腿部力量以及肺活量,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打泥巴仗鍛煉出來的。反觀現(xiàn)在的兒童,整體體質(zhì)已大不如前,家長們很難放手讓孩子去參加稍有身體對抗性的游戲或體育運動。雖然我們的經(jīng)濟條件在增強,但是孩子們的野性和血性卻日益消退。
因此,每當我驅(qū)車行駛在城郊鄉(xiāng)野道路上,看著一望無垠的田野,連綿起伏的群山,便會情不自禁地懷念起少年時代,那些自由飛行的土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