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客來(外一篇)》宋靈慧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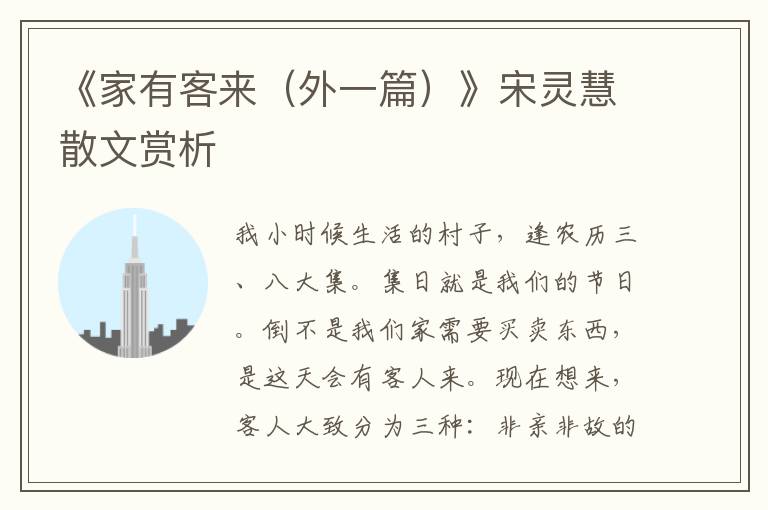
我小時候生活的村子,逢農歷三、八大集。集日就是我們的節日。倒不是我們家需要買賣東西,是這天會有客人來。現在想來,客人大致分為三種:非親非故的客人、遠近的表親和父親場上的朋友。
我家門前是一條不算寬的土路,一頭是集市,一頭樹杈一樣,通往遠近的村子。門口一個光滑锃亮的石墩子,方便過往的行人歇腳。每逢集日,天還不亮,賣東西的就大大小小出開了攤子。炸馃子的、蒸包子的,不時騰起的熱氣,一波一波地散開,香味彌漫了街巷。
早飯后,路上便是轔轔行行的車馬行人,自行車居多。不遠處有幾個“存車處”,婦女或體弱年老的男人,早早地手里把著一大嘟嚕竹棍做的牌子,站在路邊招呼生意。
我家不存車,院子里卻很快放滿了車子,這是第一類客人到了,他們循著那石墩子,就認得我家。跟母親說一聲,自己是張家王家的老少姑太太的什么人,把車子放下,他們就去趕集了。他們舍不得存車的五分錢:三分錢一斤韭菜,七分錢一斤醋,八分錢打一封信,男勞力一天工分才一毛六啊。車子大多是大水管,俗稱鐵驢,沒有車撐,一截半米長的木棍從后輪前別過去,很占地方,有的側面還拴一個柳條筐子。晌午前,他們陸陸續續回來,把買的東西裝進筐里,綁到車后架,掛到車把上,打個招呼,就順著土路,消失在枝枝叉叉的盡頭。暮春仲夏,口渴了,他們就到院子西南角水甕邊,掀開蓋簾,摘下掛在甕沿兒的銅舀子,舀半下子涼水,咕咚咕咚灌一氣。
對于這些客人,出身大戶的小腳奶奶很反感。倒了的車子砸壞了喂雞的瓦盆,破筐里的豬崽拉了一地屎,五天一個集耽誤很多活計,一年還要喝了幾挑子水……母親笑而不答,只要不農忙,頭天傍黑掃凈了院子,再去遠處洋井挑來甜水,擦拭干凈甕蓋和那只銅舀子。
遠近的表親一般沒事不會來的。有時賣完豬、羊、牲畜過了飯時,他們才會馱著空筐子、拎著韁繩來,往往還會帶一個浸了油的草紙包,里面是包子或馃子。按理,這包子馃子足夠他們飽餐的,但是,要是街頭有親戚在外面吃飯,會被以為死門活相,不光彩。把香噴噴的紙包一放,炕頭上一坐,他們實實落落地稀的干的,商商勻勻地吃了,兩全其美。因而,我家集日的午飯總是晚做,不然哪家親戚來了,飯不夠,尷尬。
客來了,母親把刷了的碗再刷一遍,斟滿熱水,放在炕上,然后遞上旱煙簸籮。簸籮里裝滿了摻了苘葉的、新搓的旱煙,綿壯程度恰好;卷煙紙是我們寫過字的廢本裁的,兩個火柴盒大小。快速地給客人卷一只喇叭形狀的煙卷,遞過去,點上,母親便去忙飯了。細糧少,搟一劑面條,蔥花兒熗鍋,切幾刀臘肉,做一鍋糨乎乎的熱湯面,炒一大盤子雞蛋,一碗腌蘿卜條淋上香油,再把客人拎來的包子馃子熥一下,端上去。父親和客人盤著腿坐到炕頭里面,母親半邊身子坐在炕沿上,佯裝陪吃,伺候盛飯。我們小孩子是不能上桌的,在另一個屋子里貓著,不許亂竄。
終于客人走了,鍋臺上,撤下來的盤子、箅子,我們一掃而光。母親邊收拾邊吃一些剩剩落落的。
父親場上的朋友來了,我們是最不自在的。首先,不能隨意去待客的屋子,撩著門簾扒頭兒也不行,站有站相,坐是坐相,不許叫嚷追逐。其次,作為長女,我要燒火。炒下酒菜,這火一燒就是好長時間,火弱了旺了還很拿捏。弟弟們最受拘束。眼饞著客人嶄新的自行車,不能手欠:擰腳蹬子不行,摸織著穗頭花邊的把套兒不行,掏車兜子更不行。唯一可以滿足的只有一個節目——被父親叫進屋里,向客人匯報考試分數,我們姐弟很少不考第一的!
母親從迎門櫥子里,炫耀似的端出那套茶具,仔仔細細地洗,準備沏茶。茶具是父親出外買回來的,冰青色壺身畫著一叢墨色蘭草,壺蓋上寫著“吃水不忘挖井人”;茶碗兒冰青色鑲黑邊,小巧的把兒,一共六個。這套家什可不簡單,半截街有相媳婦啊重要客人都來借。沏茶的開水不能大柴鍋燒,母親說這水有味兒,要提著暖水瓶去村東頭“劉家茶館”倒(買水),三分錢一壺。那水是從煤灶上燒開的,煤灶長形,一米多,并排著五六個鐵壺,一個大風箱“古達古達”地拉著。待客的煙是煙卷,從躺柜里拿出的,父親舍不得抽的,帶過濾嘴兒的。灰盒的大境門、恒大,綠盒的荷花、粉盒的墨菊、或者是紅盒的山茶花。酒是一定要有。除非客人帶來,父親支派我去聯社(供銷社)買“吳川”的酒。父親說,朋友們喜歡這個麯味。菜呢,母親去集上割點肉,從供銷社食堂“回”(買半成品)點豬雜碎、花生米,再把西屋醬黑色壇子里的咸鴨蛋掏出來,洗去厚厚的鹽泥巴。炒、切、煮、燉,我和母親一頓忙活。偶爾,我以端菜倒茶的名義進到屋里。煙氣、酒味繚繞著大小的碟子盤子和父親、客人,他們噼噼啪啪扒拉著算盤子。母親說他們在核賬,那時候,像父親在社辦廠里當會計,是我向往的職業,“核賬”是一個神秘而高貴的事情。
上了初中,學習緊張了,就愿意放學回家就馬上吃飯,一度我很反感集日。一天,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去質問母親,為什么費時費力照應那么多客人。母親指著門前的路:門敞開了,路才能越走越寬。你忘了你去鄰村看電影迷了路,是在咱家放車子的“老棒”黑燈瞎火把你送回來的?他認得你,認得咱家門口的石墩子!還有,你奶奶開刀,咱家沒錢,不就是多虧了親戚朋友你三十、他五十地幫襯?
再后來,我家搬離了那個村子,房子賣給了遠房本家。除了門前那條路和石墩子,其他的我似乎都模糊了。這些年,母親時常念叨,聽說那條路修寬了,鋪上油漆了,那石墩子,讓人偷了,說是老輩子的上馬石,不知道趕集的人還去不去院子里放車子。除此之外,母親就是非議我們的待客方式。客人來了,往飯店里領,能吃出家里的味道么?不把客人讓到熱炕頭上,那叫什么待客的禮數?甚至連臥室的門都不讓人進,這是什么規矩?
我不敢說母親老了。我私下里也擔心,匆忙行路中會不會丟了不該丟的東西。
窗外,合歡一片安靜
盛夏的午后,像一團線,冗冗長長的,又像一條隧道,沒有車輛駛過,張著嘴巴,只呆呆地等著。沒有風,一絲也沒有。沒有蟬鳴,一絲也沒有。連鳥和孩子們以及遠處的汽車聲,也商量好了似的,統統躲藏了起來。晴而不響的太陽,烈又幾分混沌地潑灑著,有力度,沒聲響。樓下,合歡們,不搖,不動,很像一張毯子,鋪展在這座樓和那座樓之間。
遠望,毯子濃碧如玉。細細品味,未來得及凋謝的花朵,星星點點,粉艷不再;剛剛成型的莢,被簇簇的羽葉舉著,通透著豆豆微微的凸。有了殘花和嫩莢點綴,這毯更像玉了——有紋理而非純冰種的玉,不價值連城,素常親民的玉。假如雕成飾件,不是擺放在皇宮或被貴族們拍來拍去的珍品,而是戴在鄰家女人腕上的一枚鐲子,點綴著主人稍稍有點精致的生活。
如果這是一塊玉,她歷經了多少年的地下沉積、巖漿侵入,而后火山噴發、期后熱液,重新結晶?風塵給予了她怎樣的囑托?歲月委派這位使者,以這種形式,暗示我們一個怎樣的讖語呢?
曾經,她是花簪滿髻的。那花,是粉紅的,就像戰馬額前的櫻子,紅得爍爍,粉得晃人眼睛。那瓣,不是瓣,瓣太粗疏了,她用精細的梳子把自己梳理成絨絨的絲線,用細膩心思把自己化成無數對觸角。在這個世界面前,她溫柔而又敏感地綻放著。花們,團團簇簇,天降的小傘似的,一落就是一樹。整棵樹像極了從宋詞里走出來的少婦,發髻簪滿的不是花,是溫婉,是妖嬈。千年百年一路走來,那步履里溢著優雅,眸子里淌出執念。
昨夜,星月斑斕。眾星于碧空漫撒著,疏疏密密的。脈脈的星輝,一如合歡花那細細的絨線和觸角。滿天的星,就是開在天上的花。滿樹的花,就是落在樹上的星。月亮不甚明皓,她似乎樂意在這如花的星輝和沾滿了星輝的花影里游移,浸染這份最現實的浪漫。月,實在不愿意攪擾合歡的夢,比花更讓自己心疼的是那葉。夜的帷幔還沒有完全遮掩,葉們便迫不及待地開始了纏綿。對視,擁吻,然后忘我地繾綣。合歡葉子是世界上最多情的,如果生命魂魄存在輪回,她一定是修行了千年,又經歷了幾生幾世,如今才落地合歡的!
風雨交加的日子,狂風如笞,暴雨如鞭,天地要被凌遲,萬物都在顫栗,一瞬間變成了寒蟬。除了風雨雷電,這個世界誰都沒有了話語權。在這千萬般的虐里,合歡卻能夠嬌弱地花顏永葆,翌日的陽光下,她又聳起了并不威武但柔韌如水的雙肩。秋至,羽葉化作了枯蝶,先是一只只,后是一群群,飄下。在西風中,被席子卷著一般,它們凌亂了昔日的夢。冬來,朔風變成了刀,率性恣情地狂砍,褐如后土的豆莢子們,一簇簇地舉著,就在枝頭。風刀過后,一曲恢弘的搖鈴大曲輪番奏起。
……
其實,此刻只是一個縫隙。不春不秋,不風不雨,這不是合歡的常態。時光的河,長袖一揮,總善于撥風弄浪,把生命的小船顛簸得歪歪斜斜。這個午后只不過是一個窄窄的縫隙吧,合歡就抓住這個縫隙,盡享這片安靜。趁著下棋的老人們還躲在空調屋子里,趁著閑適的人們還犯著慵懶,趁著嚶嚶嗡嗡紛紛翻飛的蟲兒們還在眠棲,暫且讓我安靜一下吧,不睡,不醉,也不醒,不拘眼睛的開合和心靈的馳止。
聽到了合歡的心語了,我,在一個長長的午后。
把目光從窗子放牧出去,我觸摸到了一塊玉積淀歲月的足跡。玉絕不像鋼鐵,用火煉,用水淬,僅在水與火的外力對撞里完成靈魂的升華。玉,不是。玉是有生命、有呼吸的。她的生命是潤的,她的呼吸是溫的——玉才是生命的王者。
窗外,樓下的合歡該算是一塊待璞的玉吧。她就在我觸手可及、舉首可見的咫尺。我愿與合歡一起靜坐一個盛夏的午后,讓她陪著我走過朝夕冬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