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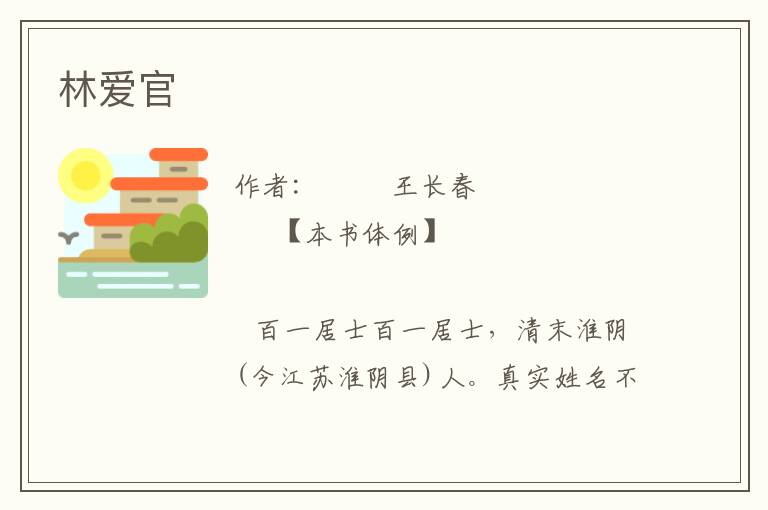
作者: 王長春 【本書體例】
百一居士
百一居士,清末淮陰(今江蘇淮陰縣)人。真實姓名不詳,白田吏隱在《壺天綠后序》中說他:“志氣磊落,博極群書,屢躓場屋,每郁郁不得志。”著有《壺天錄》,書前有光緒十一年(1885)自序。所錄多為“時勢興感,忠孝節義,感應昭昭”之異聞軼事。
林愛官,白門良家女也。幼失怙恃,入青樓。年及笄,溫重寡言,不喜裝飾,綽有大家風范。居恒以流落為感。既與長安雍生遇,兩相浹洽,遂訂白頭約。顧雍一翩翩書記耳,囊橐蕭條,荏苒數年,不能出其籍,林也自矢不他。會雍友陳生,悅林色,求通燕好。林不可,強以鴇母命,辭不獲。比入帷,林扃戶,出白劍,膝跽前,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茍延有待者,以身隸煙花,尚復貞一。君家擁花圍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挾制言歡,欲污吾身,請先污吾劍。”言訖,以刃剝(zì自)立妝臺。陳驚曰:“余固知爾鐘情雍生久矣。如力不滿何?”曰:“不滿,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為者?”陳性固伉爽,不吝施與,乃慨然曰:“爾識雍,余豈不識雍哉?予為若成之。”啟戶遽出,覓雍挾至,出金條二枚,付鴇母曰:“林不爾問矣,舍女取金,爾之見機也。不從吾言,盍觀此刃。”,鴇母惶懼無言。竟歸雍。同人撰聯句頌其義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真個為人作嫁,千金聲價贖青樓。”始則以白刃相仇,繼則以白刃受恩。此林之所夢想不及者也。世有此人,當鑄金事之。
(選自《壺天錄》)
林愛官是南京的良家女子。年幼時失去父母,流落入青樓妓院。年齡到了成年,性情溫柔穩重,不愛說話,不喜好裝飾,很有大家小姐的風度。在妓院時間長了,很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悲痛,不久與長安的雍生相遇,兩人相處非常和睦,就訂立下白頭到老的婚約。但雍生是一個英俊瀟灑的書牘記錄的小官罷了,口袋里沒有錢,光陰荏苒,轉眼數年過去,也沒能把林愛官贖出妓院。但林愛官仍矢志不移,決不再交接他人。恰好雍生的朋友陳生,喜愛林愛官的姿色,要求與她結交求歡。林愛官不同意,以鴇母的命令強迫她,她仍拒絕,但沒有獲準。等到陳生進入帷帳之中,林愛官關上房門,掏出利劍,挺身以膝跪地,請求說:“我本是薄命之人,生死都不足輕重。之所以茍延殘喘還有所等待,是因為雖身陷煙花,卻還又忠貞于一個人。你家里擁花圍柳,妻妾成群,何處不能遇到佳麗美人?假如一定要挾迫言歡,想沾污我的身體,請先沾污我的劍!”說完,將利劍插在梳妝臺上。陳生吃驚地說:“我本來就知道你鐘情于雍生很久了。但假若他無力辦這件事怎么辦?”林愛官說:“辦不到,就去死。不然的話,我揣著這把利劍干什么呢?”陳生性情本來就很豪爽,不吝嗇給別人幫助,于是情緒激昂地說:“你認識雍生,我難道不認識雍生嗎?我替你成全此事。”開門急速出去,尋找到雍生并將他強拉到妓院,拿出二枚金條,交給鴇母說:“林愛官不再屬于你了,丟了這女子而得到金子,你看勢辦吧!不聽我的話,何不看看此劍!”鴇母驚慌害怕得無言以對,終于將林愛官嫁給雍生。同事朋友撰寫對聯贊頌這件事說:“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真個為人作嫁,千金聲價贖青樓”。開始是以利劍相仇恨,繼而是因利劍受到恩惠,這是林愛官所夢想不到的。世上有陳生這樣的人,應當鑄銅像紀念他。
本篇全文雖只有四百余字,但結構完整,語言生動,塑造的兩個人物形象豐滿生動,栩栩如生。
林愛官雖然身陷煙花巷,但其重諾守信,忠于感情,與雍生“兩相浹洽,遂訂白頭約”之后,即使雍生阮囊羞澀,不能贖其身,也“矢志不他”。甚至不惜違背鴇母之命,拒絕接客,為雍生守身如玉。當陳生想要強逼她時,林愛官以身倚劍,慷慨陳述與雍生的情誼,并理直氣壯闡明自己崇尚忠貞、不畏強暴的立場,令人敬佩。也由此感動陳生解囊相助而“出其籍”。在封建時代里,林愛官那種無所畏懼,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勇于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勇氣,那種“出污泥而不染”,雖身居青樓而“尚復貞一”的精神,實屬難能可貴。
再說陳生。陳生也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無他,則林雍之姻緣終成夢想。他開始企圖與林嫖宿,在遭林拒絕后仍強行“入帷”,給人印象是一個好色之徒。但林愛官仗劍陳辭,不惜以死相拒之后,陳生竟大行俠義之舉,慷慨贈金,助林愛官與雍生美夢成真。陳生形象之前后看似矛盾,但仔細一想又合情合理,非常符合生活的真實。現實生活中確實大量存在陳生這一類型的人。他們時有輕浮浪蕩之舉,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卻仍然沒有泯滅一個普通人應有的正義感和惻隱同情之心。矛盾的統一構成了人物的真實。而從塑造人物怎樣才能達到真實豐滿這個角度講,《林愛官》這篇小說確實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