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和《桃花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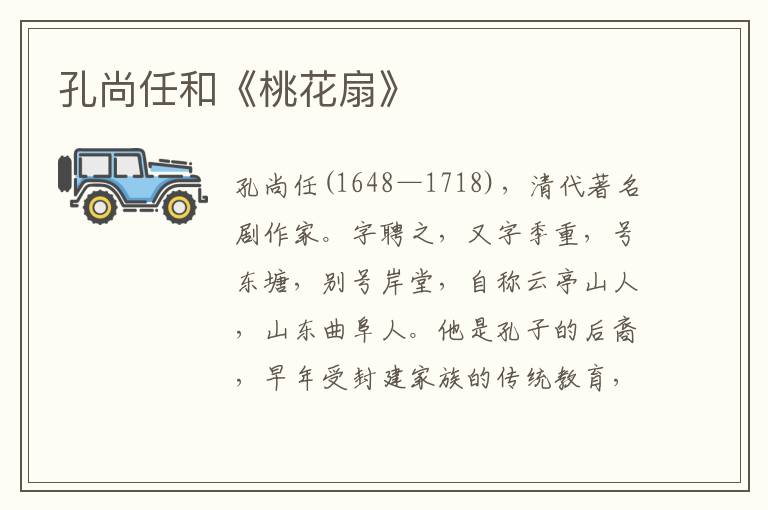
孔尚任(1648—1718),清代著名劇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稱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他是孔子的后裔,早年受封建家族的傳統教育,雅好詩文,精通音律,閉門讀書,“養親不仕”。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歸時到曲阜祭孔,孔尚任為之導游,并在御前講解《論語》,受到康熙皇帝的褒獎,被任為國子監博士。他對此感激涕零,曾作《出山異數記》表達自己的心情。不久,他被派往淮陽,督浚黃河海口,接觸了廣大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發生變化,認識到現實的黑暗和吏治的腐敗;同時游歷揚州、南京一帶,憑吊前朝歷史遺跡,結識一些明代遺老,增加了不少有關南明興亡的實際知識和感受,產生了遷官羈臣之感,這為《桃花扇》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回京后,他決意完成構思已久的《桃花扇》的創作,從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年間“三易稿而書成”(《桃花扇本末》)。《桃花扇》的演出引起巨大震動,一些“故臣遺老”為之“掩袂獨坐”,“唏噓而散”。第二年,他即因文字之禍的牽連被罷官。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返歸曲阜,重度平淡生活。晚年景況蕭條。孔尚任除作傳奇《桃花扇》外,還與顧彩合撰傳奇《小忽雷》。此外還有詩文集《湖海集》、《岸堂稿》、《長留集》等。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線索反映南明王朝興亡歷史的歷史劇。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的目的是想借南明王朝興亡的歷史總結明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他在《桃花扇小引》中說:“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為了總結歷史教訓,《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通過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悲歡離合的故事線索,概括反映了明崇禎十六年(1643)明朝滅亡前夕至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南明王朝滅亡期間,發生在以南京為中心的政治舞臺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全面反映了南明興亡的歷史。孔尚任沒有從階級矛盾的角度來反映這一時期的歷史,也回避了民族矛盾,而從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角度來總結歷史的教訓。《桃花扇》無情地揭露了南明王朝的腐敗,猛烈抨擊了南明王朝昏君行亡國之政、權奸迫害忠良、武將爭位內訌以至斷送大好河山的罪行,揭穿了福王、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同惡相濟、禍國殃民的罪惡;同時,《桃花扇》又以極大的愛國熱情歌頌了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抗擊清兵的斗爭,對愛憎分明、忠于愛情、具有堅定節操的歌妓李香君以及富于民族氣節的柳敬亭、蘇昆生等下層人民表示了由衷的贊美,這使整個作品表現出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作品中描寫男主人公侯朝宗政治上動搖,但有一定正義感,忠于愛情,國破家亡之后最后歸隱。這種描寫雖與史實有出入,但卻概括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和生活道路。《桃花扇》通過眾多的歷史人物的言行和命運說明明王朝因為重用閹黨,排斥東林而至于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所推翻;南明王朝也因重用權奸,排擠忠良,重用閹黨余孽,打擊復社成員而導致敗亡。這就從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角度總結了明王朝和南明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反映了孔尚任的興亡之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曲折體現了孔尚任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情緒。在思想文化統治極為嚴酷的康熙年間,《桃花扇》表現了鮮明的政治傾向,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桃花扇》的出現使文學史上通過男女離合悲歡,串演一代興亡歷史的傳奇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桃花扇》不僅在反映南明興亡歷史方面表現了相當的廣度和深度,而且在藝術方面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它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戲劇的優秀傳統和成功經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是對《梧桐雨》、《浣紗記》、《長生殿》等優秀作品借男女之情串演興亡歷史的表現方法的繼承和發展;“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于兒女鐘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這種忠于歷史的嚴謹的創作態度和注意歷史劇的特點而適當進行藝術虛構的作法,顯然是借鑒了《漢宮秋》、《梧桐雨》、《鳴鳳記》、《清忠譜》等優秀作品處理虛實關系的經驗。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總結歷史興亡教訓的自覺意識更強烈,他創作《桃花扇》不僅要在感情上使觀眾受感動,更重要的是要使人們吸取歷史教訓,寓意之深是以往歷史劇中所罕見的。孔尚任除作《桃花扇》劇本之外,還作了《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小識》、《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凡例》、《桃花扇考據》和《桃花扇綱領》等論文和說明,全面詳細說明了自己創作的動機目的、藝術構思、創作源起、結構安排、材料出處和角色安排等。這些材料不僅體現了孔尚任創作《桃花扇》嚴密而完整的總體構思,而且也表現了他的戲劇理論觀點。他不僅以劇作家的手段來寫劇,更以戲劇理論家的頭腦指導自己的創作。正因為如此,《桃花扇》人物形象的設置做到了精而不雜,各種角色的安排實現了綱目分明;人物性格的刻畫虛實處理也很得當;情節設計、結構安排更加考究,不僅做到了“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又巧妙地將“南朝興亡,遂系之扇底”;關目轉換靈活,造成“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的特點;至于語言運用,注重曲詞和賓白的配合,上下場詩“創為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等等,均可見出孔尚任用心之深細。
《桃花扇》高度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使其在脫稿之時便轟動一時,獲“紙貴之譽”,引得故臣遺老的故國之思。《桃花扇》和《長生殿》的創作成功使處于衰落的傳奇創作為之一振,標志著中國古代傳奇創作的現實主義又達到了新高度,孔尚任也因而得與洪昇齊名,得“南洪北孔”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