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伍蠡甫藝術美學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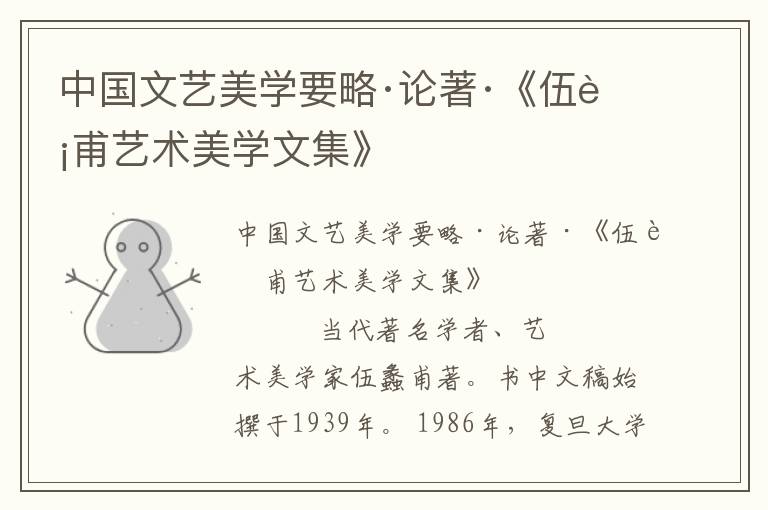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伍蠡甫藝術美學文集》
當代著名學者、藝術美學家伍蠡甫著。書中文稿始撰于1939年。 198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將作者四十多年來寫過的關于繪畫藝術和繪畫美學的文章,選了三十七篇,由作者加以修改,收入這本文集。全書內容大致分為:繪畫藝術的本質與藝術想象;藝術想象的途徑與表現(xiàn)——表現(xiàn)媒介與藝術形式美;繪畫美學中自然、藝術或物、我關系與藝術形式美,上述諸方面如何體現(xiàn)在繪畫專科、繪畫理論發(fā)展、代表性畫家及其藝術與風格中。中國的繪畫美學占了全書較大比重,其次,是西方繪畫及其美學。此外,環(huán)繞藝術想象與藝術形式美等問題,作了中西雙方的比較研究。
作者在文集中較多地論述了藝術形式美。認為這是藝術美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形式美是“構成藝術形象時所憑的方式,它不等于藝術形象本身”;它的構成因素為“線條、顏色、面塊、體積等”;它具有“比例、平衡、對稱、虛實、奇正、節(jié)奏、多樣統(tǒng)一、不齊之齊等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本身并不含有階級性;它具有相對獨立性,但考察某一具體作品的藝術形式美時,還必須聯(lián)系作品的主題,內容以及作家的審美觀點、藝術風格。作者把中西畫理的“真”與“假”的辯證觀點,提高到美學高度,指出: “在藝術家眼里,藝術形象是真,自然形象是假;他所產(chǎn)生的是藝術形象,而非自然形象,是美的事物,而非物,是霧的藝術形象,而非必倫敦之霧。”在進行中西繪畫美學的比較時,認為唯美主義也好,現(xiàn)代主義也好,中國古典美學的審美范疇也好,都只能作為我們創(chuàng)造新的藝術形式美的借鑒,藝術家要真正把藝術形象的真、善、美關系處理好,不能不研究這透徹明朗,然而又耐人尋味的藝術美學。
書中對藝術的想象與抽象有非常深刻的論述。作者把詩與畫并列或對照,認為詩、畫相通,但各有特征、各有界限;詩勝過畫或畫勝過詩等諸方面,都有共同之處。 “一言以蔽之,畫中求‘詩’包括了生活實踐——感情激發(fā)——藝術構思——創(chuàng)作實踐的全部過程,并且是繪畫創(chuàng)作的終的。”在藝術抽象的研究方面,認為從客觀事物和形象的感受,到藝術概括,運用藝術形式美,以塑造藝術形象、藝術典型,并表達藝術家的情思意境、審美個性與風格,這是任何藝術創(chuàng)造所必經(jīng)之途。西方抽象藝術,則是從陰暗的“我”,或內在音響,將不反映客觀事物的點、線、面、體布置于“虛幻的空間”,以滿足“內在需要”,所以,我們在研究他們所產(chǎn)生的抽象藝術時,既要注意其藝術形式美方面的可供借鑒的方面,也要研究造成這種特殊藝術的社會背景和審美文化心理。在研究抽象藝術時,尤其應當注意我國書法藝術的特征,認識到它脫胎于象形,而發(fā)展為抽象表情、抽象表質的藝術。作者以為,倘若熟悉我國書法藝術的抽象功能,再看現(xiàn)代西方抽象派藝術,就不會對“抽象”這一審美概念感到陌生。又指出,我國書法所表之情與質,可以是渾樸、瀟灑、肅穆、剛毅、奔放、沉酣、奇倔等,這種精神狀態(tài),和西方抽象畫派畫家的審美心理相比,有其積極與消極、正常與失常的差異。作者主張,應當吸取西方抽象藝術的合理內容和形式,發(fā)展我國積極、正常的民族抽象藝術。該書還對于中國繪畫的自然美與藝術美、中國繪畫的人與藝術、中國繪畫美學史的幾個新發(fā)展,如宋元以來文人畫的審美范疇和藝術風格等問題,作了詳細的探討,提出嶄新的見解。
本書對于畫論的研究,特別注意在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分析中國畫論的概念范疇,在思想上追本溯源,在實踐中看其發(fā)展衍變,因此作者雖以現(xiàn)代眼光論析古代美學思想,但結果是對古代畫論的科學總結,不是以現(xiàn)代思想強加古人,而古代美學的為今所用起點也正在這里。書中在分析“氣韻”時,以謝赫“六法”為畫論觀點的起始,以荊浩對“氣韻”的解釋說明其意義,得出明確的認識:創(chuàng)作中的力是氣,取得的藝術效果是韻,有“氣”則“取象不惑”,得“韻”須“隱跡立形”。為了說明“氣韻”中“韻”的價值,作者又進一步從司空圖詩論中的“韻味”,以及蘇軾、黃庭堅、范溫、姜夔的有關理論見解加以論證,這就使畫論中的“氣韻”問題得到透徹明晰的論證。本書中對于類似的問題,如“形與意”。以及“簡”、 “拙”等,都有同樣的史論結合的深入分析。
書中的畫論研究是以作者豐富的創(chuàng)作和鑒賞經(jīng)驗為基礎的,因此闡發(fā)的理論準確深刻,評析的現(xiàn)象更富有審美引發(fā)性。在書中不論是概論問題,還是就具體現(xiàn)象進行分析,都收有這樣效果。如對于畫中的簡約表現(xiàn),作者從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儒家“尚儉”、道家“抱一”,說到陸云、劉勰、南宋禪學的簡約觀點,再具體進入藝術實踐的品評,找出宋元時代繪畫中的尚簡實績,證明了簡的特殊藝術表現(xiàn)力。再如對于孔子講的“繪事后素”,作者從實際繪畫經(jīng)驗指明,繪是涂顏色,畫指描線條,顏色涂成的面,須用白色線條界畫清楚,顯出“后素”之功。若不是有經(jīng)驗的畫家是很難說得這樣清楚的。
作者學貫中西,善于從實際到理論進行全面分析比較,所以本書非同一般藝術美學論著,而是在概括了中西藝術美學的共有規(guī)律之后,在更有超越的意義上講著美學原則,因而理論令人信服,也啟發(fā)人開闊思想視野。如對于線條的分析,作者從柏拉圖、荷加茲、席勒等人的著名觀點,分析到唐人的“一筆畫”,清代石濤的“一畫”指出中國畫論中的線條概念, “已遠遠超越了藝術媒介的范圍,一方面體現(xiàn)意境發(fā)展和藝術構思的綿延,另方面連貫起藝術構思和運筆造形,匯成一種動力以及動力所含的趨向。所謂‘線條’意味著,形而上的‘道’或表現(xiàn)途徑,自始至終綴合意、筆,學、理、心、物,統(tǒng)一主觀與客觀,從而概括出藝術形象。”這是非比較方法不能明鑒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