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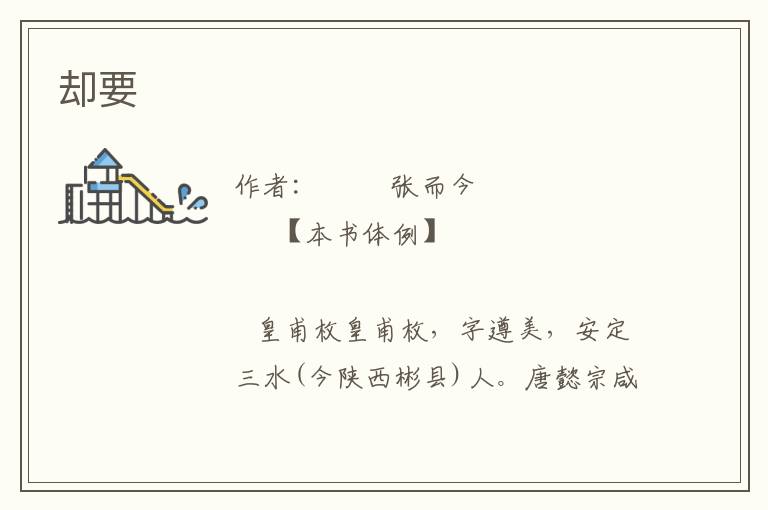
作者: 張而今 【本書體例】
皇甫枚
皇甫枚,字遵美,安定三水(今陜西彬縣)人。唐懿宗咸通(860——874)末年,曾為汝州魯山(今河南魯山)縣令。僖宗(874——888)時赴調(diào)梁州(治所在今陜西南鄭縣東)行在。唐亡后旅食汾晉(在今山西),追記咸通中事,著《三水小牘》,多記仙靈怪異,亦有人間故事。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于親姻家,惟卻要主之,李侍婢數(shù)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
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卻要而不能也。
嘗遇清明節(jié),時纖月絹絹,庭花爛發(fā),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卻要遇大郎于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東南隅,佇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dāng)至。”大郎即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diào)之。卻要復(fù)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來之,卻要復(fù)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著,握手不可解。卻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
延禧于庭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fā)。少頃,卻要突然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卻要復(fù)從而咍(hāi咳)之。
自是諸子懷慚,不敢失敬。
(選自《三水小牘》)
湖南觀察使李庾的女奴,叫卻要。容貌美麗,舉止端莊,并善于辭令。初一、十五與親戚家通禮問候,都由卻要主持,李家侍女奴婢幾十人,沒有能和她相比的。而且乖巧可愛,才思敏捷,會察言觀色,相機行事,親戚們也大多喜歡她。
李家四個兒子:大的叫延禧,二的叫延范,老三叫延祚,為人們所稱呼的大郎以下又排到五郎。個個年少狂放,都想占卻要的便宜但做不到。
有一回趕上清明節(jié),新月如眉,庭院里鮮花盛開,正堂掛著刺繡的簾幕,里面點著銀燈。卻要在櫻桃樹的花影下遇上了大郎,大郎就拉住她求愛。卻要拿坐墊給他,說:“可以在大廳東南角,站著等我;等到前屋人都睡著了,就來。”大郎離去后,到了廊下,又遇上二郎調(diào)戲她。卻要又拿坐墊給他,說:“可以在大廳的東北角等我。”二郎離去后,又遇上三郎抱住她,卻要仍拿坐墊給他,說:“可以在大廳西南角等我。”三郎離去后,又有五郎遇著她,握住手脫不開。卻要也拿坐墊給他,說:“可以在大廳西北角等我。”四位公子都離去了。
延禧在廳角,抑制住呼吸等待。大廳的門斜關(guān)著,看見他的三個弟弟陸續(xù)而來,各奔一個角落。他心里雖然對此驚訝,但不敢出聲。一會兒,卻要忽然點起火炬,急速地奔向大廳,敞開兩扇門往里照,對延禧兄弟們說:“這些個窮小子,怎么敢到這里找睡覺的地方?”哥四個都扔下所帶的東西,捂著臉跑開了。卻要又趁機譏笑他們。
從此各位公子感到羞愧,對她不敢無禮了。
本篇塑造了一個美麗端莊而聰明干練的女性形象——卻要。
作者采用概括介紹和集中表現(xiàn)相結(jié)合的手法,首先敘述她“美容止,善辭令”,又“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在外交場合應(yīng)付裕如。接著集中筆墨寫她教訓(xùn)主人家都想染指于她的四位公子的故事。一個清明節(jié)的晚上,卻要在庭院先后分別遇上了大郎、二郎、三郎和五郎,他們都想調(diào)戲她。卻要略施小計,讓他們分別在大廳的四個角落等待,之后燃亮火炬,往里照射,說道:“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羞得兄弟四人“掩面而走”。這一情節(jié),突出地表現(xiàn)了卻要的“巧媚才捷”,可見作者善于在矛盾沖突中展示人物性格。
讀者在發(fā)笑之后,稍加思索便會感到這實質(zhì)上是一篇思想嚴肅的作品。卻要這樣一個聰明干練、美麗賢良的女子,竟“身為下賤”,給人作奴,而愚蠢、荒淫的延禧兄弟卻是人上人,多么不公平的世界!在讀者心中激起的已不是暢快,而是惋惜,是憤慨了。所以,它堪稱一篇“寓教于樂”的作品,輕松的故事里蘊含著重大主題。
本篇風(fēng)格謔而不虐。李家四位公子雖然當(dāng)場出丑,但并非“當(dāng)眾”;而且用語委婉,說他們是“覓宿處”,聽起來似乎在那里做游戲。就這樣在有分寸的耍鬧中懲罰了他們,因此顯得風(fēng)趣橫生。卻要及李家公子,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唐伯虎“三笑”故事中秋香及華家少爺大呆、二呆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