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xué)要略·人物·王若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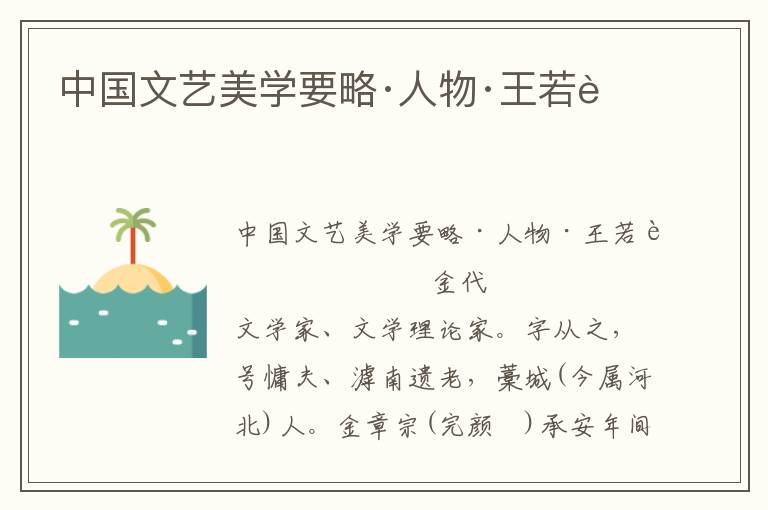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xué)要略·人物·王若虛
金代文學(xué)家、文學(xué)理論家。字從之,號(hào)慵夫、滹南遺老,藁城(今屬河北)人。金章宗(完顏璟)承安年間進(jìn)士,曾任金翰杯直學(xué)士,金亡不仕。有《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他的美學(xué)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文辨》和《詩話》中。王若虛推崇程朱理學(xué),重視文藝的思想內(nèi)容,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了他的美學(xué)思想,在詩文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guān)系上,他強(qiáng)調(diào)“以意為主”,即內(nèi)容起決定性的作用。他曾征引其舅父周昂的話說: “吾舅嘗論詩云: ‘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主強(qiáng)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他對(duì)內(nèi)容的要求是“真”與“似”,即應(yīng)當(dāng)有真實(shí)的思想感情和符合于社會(huì)實(shí)際的真實(shí)。《詩話》說: “哀樂之真,發(fā)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他還抨擊邵公濟(jì)的“遷史杜詩,意不在似”論,說:“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夢(mèng)中語乎?”
他還就蘇軾所提“形似”問題以及“形似”和“神似”的關(guān)系予以闡發(fā),反對(duì)那種片面強(qiáng)調(diào)“神似”、 “氣象”而脫離生活真實(shí)的傾向。他認(rèn)為“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即應(yīng)在形似的基礎(chǔ)之上求神似,否則便失之空靈。他舉例說:“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煙杳靄,謂之氣象”,他認(rèn)為這是不可取的。
王若虛提出的“妙在形似之外”,已經(jīng)涉及生活真實(shí)與藝術(shù)真實(shí)的辯證關(guān)系問題。從對(duì)內(nèi)容與形式、形似與神似這樣的根本問題的認(rèn)識(shí)出發(fā),他反對(duì)江西詩派因襲模擬古人和險(xiǎn)怪奧僻的詩文風(fēng)氣。 《文辨》說: “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為哉?”《論詩詩》說:“文章自得方為貴,衣缽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fù)何人?”這些都是就江西詩派“奪胎換骨”、 “點(diǎn)鐵成金”的觀點(diǎn)而發(fā)的,因而,他又說: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diǎn)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因而他十分反對(duì)片面追求形式奇險(xiǎn)和文辭浮華的風(fēng)氣,他批評(píng): “凡文章須是典實(shí)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xiǎn),始為知本末。”他還反對(duì)一味茍簡,提倡“唯適其宜”,即宜繁則繁,宜簡則簡。要“辭順理達(dá)”,要適當(dāng)?shù)刂v究句法和工巧。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基于這種美學(xué)觀點(diǎn),他最為推崇杜甫、白居易和蘇軾。他認(rèn)為白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dú)庀噘啊薄qg斥了所謂“郊寒白俗”的說法。他贊美蘇詩“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袞袞筆頭傾。”并指出蘇黃的極大區(qū)別: “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并從“詩詞只是一理”出發(fā),批駁了宋正統(tǒng)詞派和婉約詞派認(rèn)為詞與詩的內(nèi)容不同,詞應(yīng)當(dāng)以男女艷情為主的觀點(diǎn),同時(shí)駁斥了他們對(duì)蘇軾“一洗綺羅香羅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zhuǎn)之度”豪放風(fēng)格的挑剔,認(rèn)為蘇詩的“情”在“風(fēng)韻”、“雅趣”,在驚濤駭浪、渾然天成,而非“纖艷淫媟”之情。對(duì)詩文的法度, 《文辨》說:“定體則無,大體須有”,看到了文體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王若虛文藝美學(xué)思想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和一些精辟見解對(duì)后世有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