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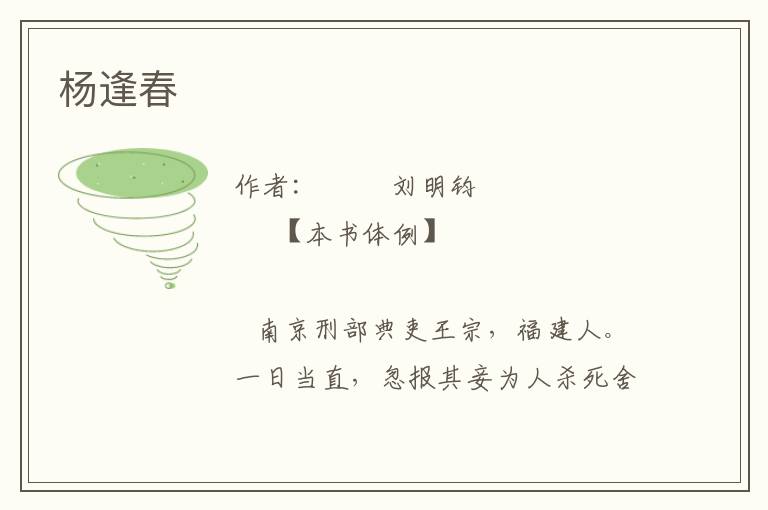
作者: 劉明鈞 【本書體例】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為人殺死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云:“聞報而歸,眾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為殺之?”拷掠累日,終無異詞。
既數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時后鞫(jǖ居)王宗獄。
如期鞫之,猝命隸云:“門外有覘(chān)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法而釋宗。
楊曰:“若日間則觀者眾矣,何由蹤跡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來瞰乎?”由是舉稱神明,一時聲震都下。
(選自《說聽》)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是福建人。一天,他正在官署辦公事,忽然,有人報告說他的小妾被殺。王宗匆忙回去,隨即跑來報案。尚書周公把這個案件交給河南司官員審理。辦案人員懷疑兇手是王宗。王宗說:“我聽說這件事以后才回去,眾人都看見了。再說,這個女子并沒有外遇,我們相處很和睦,我為什么要殺她呢?”一連幾天拷打王宗,他還是以上那種說法。
幾個月以后,都察院會審這個案件,發文調浙江道御史楊逢春共同審理。楊示意定于某夜二更天后審訊王宗一案。
按約期審訊王宗,楊逢春突然命令衙役道:“門外有窺視的人,抓過來。”果然抓到了兩個人。一問,甲說:“他拉著我和他作伴,也不知道什么事。”于是把甲放了。對乙用刑拷問,乙全部招認。說:“我和王宗館人的妻子私通,被他的妾看見了,就殺人滅口。”隨即把乙依法制裁,釋放了王宗。
楊逢春說:“如果白天審理此案,看的人一定很多,怎能尋找這個人呢?如果不關自己的事,誰肯深夜來看呢?”由于這件事,大家稱贊楊逢春辦事精明干練,一時間名滿京城。
這是一篇公案題材的小說,通篇看來,案情并不驚險,情節也不復雜,是一個一般性的兇殺案件。但作者寫來,卻一波三折,耐人尋味。前后兩次不同的偵破手段,抓到前后兩個不同的兇犯。一假一真,作者寫得抑揚曲折,褒貶之意明顯。
作者生活在明朝后期,當時吏治是非常腐敗的,司法官員“卒臆斷獄,任情用刑”(《錯斬崔寧》),多少無辜的生靈喪命于捶楚之下,這是十分可氣可恨的事。小說中的“河南司”的官員正是采取這種審案方法。他們稀里糊涂地把王宗抓了起來,“欲坐宗罪”,便非常殘酷地對王宗“拷掠累日”,王宗不服,理直氣壯地爭辯:“聞報而歸,眾所共見;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為殺之?”而河南司的地方官對王宗卻一味的嚴刑拷問,使王宗大吃苦頭。結果是“終無異詞。”使此案走入了死胡同。身為南京刑部典使的王宗,事涉獄訟,尚且遭受如此的拷掠,那么,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庶民百姓遇到這類的官司,就更是吃盡苦頭,九死一生了。作者在這里對明代的司法吏治進行了無情的嘲弄譏諷。
楊逢春這個人物的出現,使擱淺了數月之久的疑案又柳暗花明。楊相信王宗的爭辯是有道理的,用今天的話說,王宗沒有殺人的主觀動機,也不存在殺人的時間和條件,所以,他排除了王宗殺人的可能性。那么真兇是誰?他現在干什么?楊逢春展開了心理分折和邏輯推理:因為此案還沒有結案,兇手一定十分關心此案的進展,在這期間,他內心肯定忐忑不安。白天審案,看客眾多,在看客中很難查到誰是兇手。于是事先放出風聲:“某夜二更時后鞫宗獄。”而楊在審案時卻密切注意門外,出奇不意命手下人:“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一下子便抓住了這個案件的真兇,楊逢春真可謂是精明干練。
作者采取了對比的手法來塑造人物,使人物的形象更突出。河南司的官員不問青紅皂白,一味的嚴刑拷打,而楊逢春卻是冷靜思考,細致分折,運用聰明的機智進行推理判斷,然后采用一定的手段破獲了此案。在結案時,楊說;“人非切己事者,肯深夜來瞰乎?”一語道破其中奧妙,入情入理,令人心服口服,兩相比照,更顯得河南司官吏的昏憒無能。
這篇小說正如我國古代此類題材的小說戲劇一樣,具有作者的理想色彩,作者所稱頌的清官,在當時社會里是極少見的。正如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十五貫》中的況鐘,這些人代表了廣大人民渴望清官的善良愿望,正如本篇小說中的楊逢春,即令有生活的原型但也有作者的附會,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