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藝美學(xué)要略·人物·尤奈斯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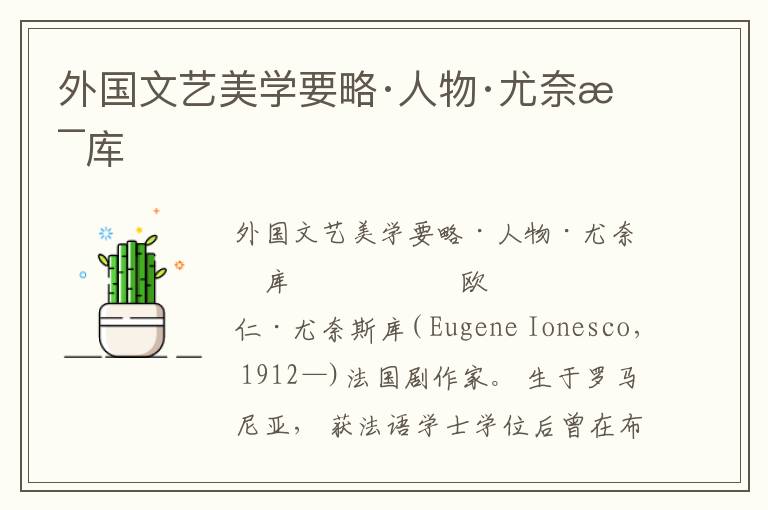
外國文藝美學(xué)要略·人物·尤奈斯庫
歐仁·尤奈斯庫( Eugene Ionesco, 1912—)法國劇作家。 生于羅馬尼亞, 獲法語學(xué)士學(xué)位后曾在布加勒斯特任教。1938年始在法國定居,后在巴黎出版界工作。尤奈斯庫是一位多產(chǎn)的劇作家。他在學(xué)習(xí)英語時發(fā)現(xiàn)人物對話中那些陳詞濫調(diào)全是以固定的方式、莊嚴(yán)的聲調(diào)發(fā)出來的,不禁大笑。于是他把這種平庸的日常用語極度夸張,達(dá)到荒謬程度,寫出了他的第一部“反劇本” 《禿頭歌女》 (1950)。以后,他在三十年里寫下40多部劇作,著名的有《椅子》 (1950)、 《阿梅黛或脫身術(shù)》 (1954)、 《不為錢的殺人犯》(1958)、 《犀牛》(1959 ) 、 《國王正在死去》(1963)等。在法國,他的戲劇同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存在主義等文學(xué)思潮一樣,有著極大的影響。他的許多劇本被譯成近三十種文字,并在許多國家上演。他同時寫有不少論述他的戲劇主張的論文,大多收集在《意見與反意見》(1965)、《與克洛德·波納弗的會談》和《散記》中。
尤奈斯庫認(rèn)為,他的戲劇創(chuàng)作的根源是“一種情緒”、 “一種沖動”,是為了“滿足內(nèi)心的一種需要”,而戲劇則是“內(nèi)心斗爭在舞臺上的一幅投影”。對作為創(chuàng)作根源的“精神狀態(tài)”,他分為兩種:一種是在一瞬間感覺到人生有如夢幻一般,仿佛能看穿一切,以為人生和世界都“無足輕重,毫無意義”,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消逝”感、“虛無”感。這時,就會由苦惱導(dǎo)致欣喜,進(jìn)而化為解脫,看到在充滿幻覺和虛假的世界里,人類的一切行為也都表現(xiàn)得荒誕無稽,從而獲得徹底的創(chuàng)作自由。再一種是感覺“物質(zhì)充塞每個角落,占據(jù)一切空間,它的勢力扼殺一切自由”, “人間變得壓抑不堪”的“壓抑”感、 “窒息”感。在這種憂慮的處境中,把幽默注入苦惱,是又一種歡樂,又一種解脫。這同前一種比較是更占據(jù)優(yōu)勢的創(chuàng)作根源。同時他認(rèn)為這些作為創(chuàng)作根源的情緒和沖動,還會以其“嚴(yán)密的一致性” “使處于原始狀態(tài)的感情具有正規(guī)結(jié)構(gòu)”,不須去“適應(yīng)外界強(qiáng)加的某種結(jié)構(gòu)程序的邏輯”。總之,他認(rèn)為世界和人生都是荒誕不經(jīng)的,對人生的一切探索和追求都是徒勞無益的,因此,只有“感覺荒誕,感覺到不可能有日常經(jīng)驗(yàn),也不可能有人與人之間溝通思想的嘗試”,才會進(jìn)入創(chuàng)作的“一個更深的階段”。由此,他主張戲劇只提供見證,避免說教,無須連貫的情節(jié),喜劇性作為“表達(dá)異常事物的一種方式”,只有使“最平淡無奇的日常工作、最乏味的言語被應(yīng)用得超過限度時”,才會實(shí)現(xiàn)。
在他的作品中,人物被抽象化,沒有個性,喪失自我,有意地出現(xiàn)不符合邏輯的推理、夢魘和奇異的變形,甚至以無生命、非人性的或腐朽的物體逐漸擴(kuò)展,排擠在物質(zhì)世界殘存的人,用物體、道具取代語言、思想等。這些都體現(xiàn)了他的基本觀點(diǎn)和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