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葉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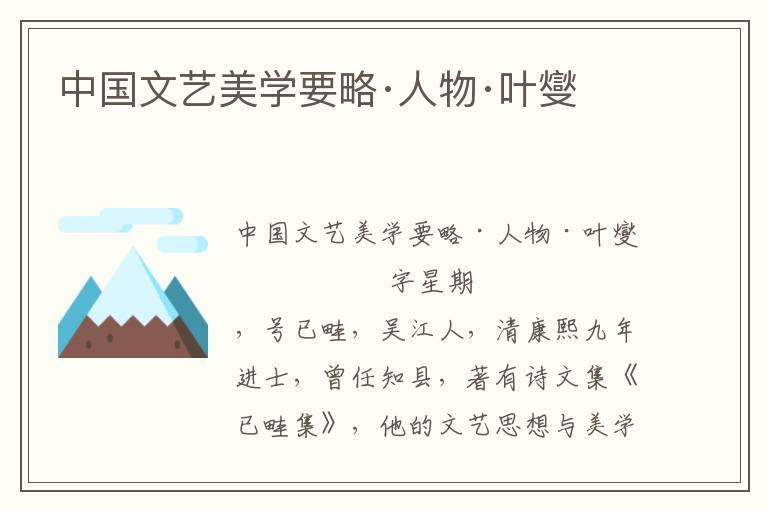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葉燮
字星期,號已畦,吳江人,清康熙九年進士,曾任知縣,著有詩文集《已畦集》,他的文藝思想與美學觀點集中表現(xiàn)在他的理論專著《原詩》中。
葉燮是中國古代美學史上具有較完備的美學體系的理論家。他堅持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吸收儒、道、禪宗等各家的美學思想精華入論,并在表現(xiàn)方式上打破傳統(tǒng)的詩話體的評點方式,在藝術美學領域中“探奇撥霧”,驚壓時賢,自成一家體系。
葉燮看到廣泛存在于天地之間的美,是具有客觀屬性的具體存在。他說: “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本乎天”是說美的底蘊具有客觀性,不是由人任意而定的。他的美本乎天的客觀屬性論是在他具體分析了美的事物的構成之后得出的。他認為美離不開“理、事、情”三種因素。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 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這里說的“理”是事物的內(nèi)部規(guī)律性, “事”是事物得以實現(xiàn)的過程, “情”是事物千姿萬態(tài)的情狀。葉燮又進一步推究,這三者在“自然流行”的“氣”的動力因作用之下,也就是生生不已的運動變化之中,形成一體,構成為美;又在人的“神明才慧”作用之下,實現(xiàn)為美。也就是美的現(xiàn)實的實現(xiàn)離不開人。這是葉燮美學獨到之處。在他看來不僅社會美、藝術美是如此,就是自然美也是如此。他說自然美是“生而美者”之類,如五岳的性情氣象,但是對這些如果沒有游山人的“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 “默契神會”, “天地亦不能自剖其妙”。這就是說五岳之美具有客觀的底蘊性,與人結合之后,其美妙“始泄”。
葉燮看到了美的存在形式上的“對待”與轉(zhuǎn)化關系。他說“凡物之義不孤行,必有其偶為對待”。他例舉陳、熟、生、新等等,說明無事無物不在對比之中顯現(xiàn)。他還從發(fā)展變化的角度提出,美與丑的地位有時隨條件的轉(zhuǎn)化而發(fā)生轉(zhuǎn)化: “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偏于一者也。”他例舉生死、貴賤、貧富、香臭這些對待之兩端,習慣中被認為是美的,有時變化為丑的, “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 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為惡。”他發(fā)現(xiàn)的規(guī)律是存在的,盡管有時舉例不當。
葉燮的美學觀中創(chuàng)作主體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認為藝術創(chuàng)造是一種源于物而攄于意的自由創(chuàng)造,這種創(chuàng)造活動不應受到本身規(guī)律以外的任何人為的桎梏的束縛。“文章一道,本攄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為此他反對對古人的“字剽句竊”,反對對輿論的附合,反對對名利的競逐。他認為這些都是實現(xiàn)審美創(chuàng)作主體“筆墨自由”的障礙。
在葉燮的主體論中,“才、膽、識、力”是實現(xiàn)主體價值的條件,他認為只有有了這四個條件,才能對于普遍存在的理、事、情三者,加以反映表現(xiàn),創(chuàng)造為藝術品。這個主體的價值是實踐的價值,條件是實踐的條件。他說: “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于此而為之發(fā)宣昭著。此舉在我而為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為作者之文章。”葉燮所標舉的“才、膽、識、力”,并不是平列的。他認為四者的核心是才與識,而識又“居乎才之先,識為體而才為用”。這說明識是才的內(nèi)聚力,才是識的外現(xiàn)力;識還是膽的智慧之宰,也是力的引導。
在葉燮的審美創(chuàng)作論中,藝術對于生活的“踵事增華”是統(tǒng)一的,而藝術的價值更在于“增華”。實現(xiàn)的途徑在于改造事端,游于象外,所寫不必“一一征之實事”,可以“想象以為事”,這樣藝術就不僅是表現(xiàn)常事、常理,更要表現(xiàn)難述之事、難言之理。由于葉燮的藝術美學的目標在于超越性的創(chuàng)造,所以他在分析才華與法式的關系時,就自然要強調(diào)“以才御法”,不要“斂才就法”;要善于創(chuàng)造變化的藝術,而不要總是“井然秩序”的老一套。他把藝術美的基本點放在了適度與變化的和諧統(tǒng)一之上,為中國古典美學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