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與《草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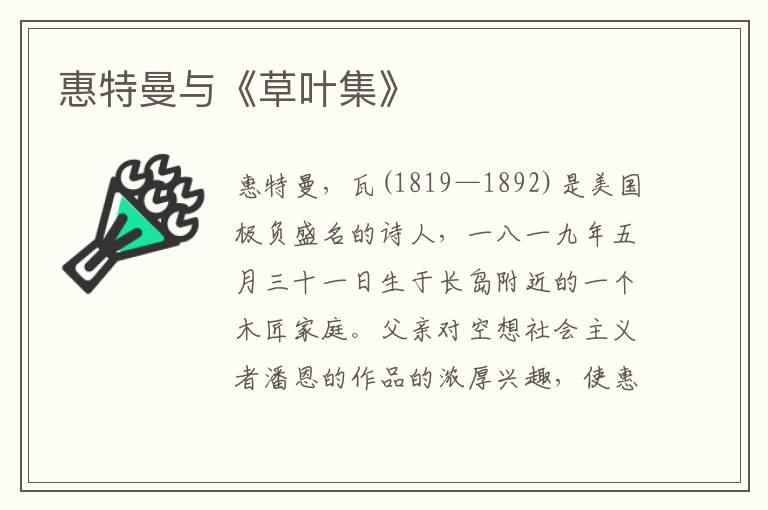
惠特曼,瓦(1819—1892)是美國極負(fù)盛名的詩人,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生于長島附近的一個木匠家庭。父親對空想社會主義者潘恩的作品的濃厚興趣,使惠特曼深受影響。一八三〇年,惠特曼結(jié)束初等教育,邁入社會,先后做過信差、藝徒、排字工、小學(xué)教師、記者、編輯、木工等。一八四六年擔(dān)任紐約《布魯克林之鷹報(bào)》的編輯,因?qū)懳恼路磳π钆贫唤夤椭螅_始到美國南方漫游,同勞動者廣交朋友,思想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開始了民主主義者的新生活。南北戰(zhàn)爭期間,他堅(jiān)定站在林肯領(lǐng)導(dǎo)的革命軍方面,多次到醫(yī)院做志愿看護(hù)人員,戰(zhàn)地生活之間隙,積極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戰(zhàn)后,惠特曼屢遭生活的不幸和疾病折磨,一八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逝。惠特曼的整個創(chuàng)作大致分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從五十年代始,至南北戰(zhàn)爭前夕,作品中蕩漾著浪漫主義的激情,他歌頌蓬勃發(fā)展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民主、自由的時代特征,情感奔放、真摯,筆力剛健、明快,語言雄渾、流暢;后期創(chuàng)作從南北戰(zhàn)爭期間至詩人逝世,面對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尖銳矛盾,詩人減弱了浪漫主義情調(diào),增強(qiáng)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批判精神,成為實(shí)現(xiàn)美國文學(xué)從浪漫主義向現(xiàn)實(shí)主義轉(zhuǎn)化的先驅(qū)人物。惠特曼一生的詩作都編入《草葉集》(1855-1892)。詩集第一版問世時,僅收詩十二首,以后歷經(jīng)再版,不斷增編和補(bǔ)充,最后第九版問世時,已成了包容三百八十三首詩的巨作。其中最長的一首,后來被稱為《自己之歌》,其內(nèi)容幾乎包括了詩人畢生的主要思想,是他最重要的詩作之一。詩中多次提到“草葉”,它代表了一切平凡、普通的東西和平凡的普通人,是詩集靈魂的象征。詩人在編印各版《草葉集》時,經(jīng)常變動詩篇的前后次序,其原則不是按詩篇寫作時間的先后,而是按照它們的主題分類。詩人謳歌民主與自由:他在《大路之歌》、《為你,啊,民主喲!》詩篇中呼喚,“走呀!帶著力量,自由,大地,暴風(fēng)雨,健康,勇敢,快樂,自尊,好奇;走呀!從一切的法規(guī)中走出來!”詩人真摯地表示,“為你,啊,民主喲,我以這些為你服務(wù),”“為你,為你,我顫聲唱著這些歌。”在《從巴門諾開始》中,詩人寫道:“啊,這樣的主題——平等!這神圣平凡的名詞!”表達(dá)了渴望人類平等的理想。歌頌人、自然和勞動,是《草葉集》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詩人十分重視“人”的精神和肉體的力量,欣賞“人”的活力,宣稱“我是肉體的詩人,也是靈魂的詩人”,他通過“自我”,禮贊極為自然的人性。詩人尤其把對人的藝術(shù)描寫的主要鏡頭,對準(zhǔn)了開發(fā)新大陸、建設(shè)新生活的普通勞動者,在《職業(yè)之歌》、《闊斧之歌》中,斧頭和它所創(chuàng)造的形象,成為勞動者創(chuàng)造力的象征。題名為《我聽見美洲在歌唱》的著名短詩,以普通人們的勞動和歌聲,組接成同時作用于讀者視覺和聽覺的動人畫面。惠特曼的民主理想是和反對蓄奴制密不可分的,《草葉集》也體現(xiàn)了詩人這種鮮明的政治傾向。在《敲呀!敲呀!鼓啊!》、《致政府》等詩中,他大聲疾呼地號召一切人參加戰(zhàn)斗,投入廢奴戰(zhàn)爭。南北戰(zhàn)爭以后,詩人對美國社會現(xiàn)實(shí)的丑惡面加深了認(rèn)識,在《不,今天別向我提到那重大恥辱》等詩中,揭露了美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虛偽和國家機(jī)構(gòu)的腐化。惠特曼是全力為建立美國式的、民主的文學(xué)而奮斗的地道的美國詩人,同時又是一個熱情的國際主義者,《草葉集》中也洋溢著詩人支持和贊頌歐洲革命的激情。綜觀而言,《草葉集》是惠特曼對美國整整一個時代的總結(jié),概括了極其豐富的生活內(nèi)容和思想意義。雖然它也表現(xiàn)出惠特曼世界觀中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因素,但其基本部分屬于美國文學(xué)和世界文學(xué)中民主性的精華。《草葉集》在詩歌的藝術(shù)形式上體現(xiàn)了詩人的大膽創(chuàng)新精神。他采用民間口語,打破了長期以來美國詩歌因襲的格律,創(chuàng)造出一種以思想、形象和用詞、造句上的平行法為顯著特點(diǎn)的新詩體。這種后來被稱作“滾滾波濤”的自由體,大量采用疊句,長句,平行句和夸張的形象語言,廣泛運(yùn)用象征、比喻手法,增強(qiáng)了詩歌表現(xiàn)力,對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我國“五四”以來的新詩從中受益不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