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崖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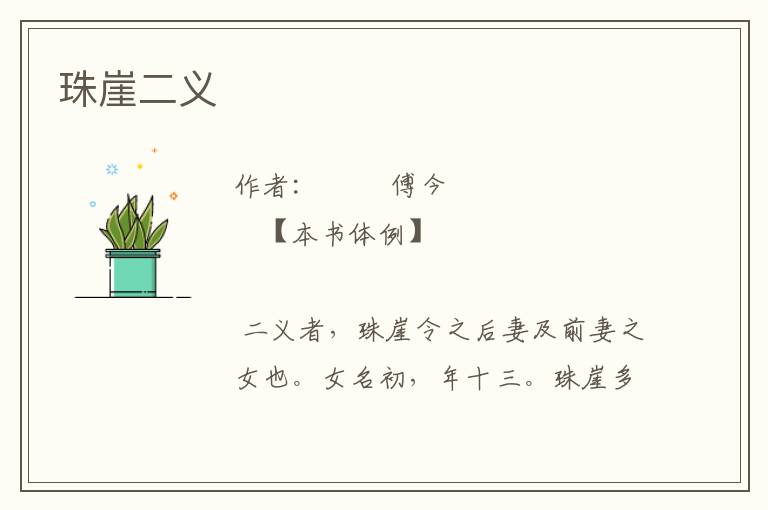
作者: 傅今 【本書體例】
二義者,珠崖令之后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系臂,及令死,當送葬。法納珠入于關者死,繼母棄其系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知之,遂奉喪歸。至海關,關侯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系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愿且待罪,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系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旁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侯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旁人,可謂直矣。
(選自《列女偉》)
兩位有義氣的人,是珠崖令的后妻和他前妻的女兒。女兒名叫初,十三歲。珠崖這地方盛產珍珠,繼母把大珠子串成珠鐲,帶在臂上。珠崖令死后,將遺體送回故鄉安葬。當時的法律規定,帶珍珠進關內,應判死罪,所以繼母把她臂上的珠鐲扔了,她的男孩當時九歲,因喜好而把珠子又拾回來,放在母親的梳妝匣里,誰也不知道,于是就護靈柩朝故鄉走去。到了海關,官吏從繼母的鏡匣中搜出十枚珍珠。關侯說:“哎,觸犯了法律,沒有辦法,誰該負罪?”初在一旁,由于擔心母親說是她自己放在鏡匣里,就說:“我應當負罪。”關侯說:“那具體情節如何?”初答:“父親不幸去逝,夫人從臂上解下珠子扔了,我覺得可惜,便拾回放在夫人的鏡匣里,對此夫人并不知道。”繼母聽了,忙過來問初。初說:“夫人把珠扔了,我又拾回來,放在夫人的鏡匣內。我應當負罪。”繼母認為初說得是實情,因憐愛她,便對關侯說:“我愿負罪,不要懲辦孩子,孩子確實不知。這些珠子是我的臂鐲。丈夫不幸去逝,我解下來放在鏡匣里,急著奉喪,道路遙遠,與弱小同行,恍惚中忘了,我應當負罪。”初固執地說:“實在是我拿的。”繼母又說:“孩子只是推讓罷了,實在是我拿的。”因此哭得制止不住。女兒也說,夫人可憐我成了孤兒,硬想讓我能活下來,夫人實在是不知道啊。”又因此哭泣,淚交互流在了頸脖上。送葬的人都哭了,十分悲傷,旁邊的人都痛哭流涕,關吏拿筆書寫罪狀,竟不能寫一個字;關侯低著頭流淚,一整天不忍心判決。于是說:“母親和孩子這樣有情有義,我寧愿自己抵罪,也不忍心判決。而且又互相推讓,怎么知道哪個是呢?”于是就把珠子扔了,讓她們回去。回去以后,才知道是男孩獨自拾的。君子稱這兩位有義氣的人慈、孝。《論語》說:“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在中間了。”繼母和女兒推讓著爭死,悲哀感動旁人,可以說是正直了。
這是劉向《列女傳》中的一個名篇,它生動地描繪了幼女初與繼母,在法律面前,為了保護對方,爭著承擔罪責的高尚品德。
本篇在藝術上的特色是,作者很會使用小道具。本篇的道具是珍珠。珍珠的丟棄與存在,推動著故事情節的向前發展。珍珠把一些互不相聯的事件,緊緊地連接在一起,使作品有完整的結構,清晰的脈絡。
全篇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系臂”(“系臂”,就是手鐲),表現出繼母與一切女人一樣,富有愛美之心。第二部分,是“繼母棄其系臂珠,其子男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知之。”繼母棄珠,是因為法律有規定:“納珠入于關者死”。珍珠在產地,好象不值錢,人們可以任意使用。但是,私人帶入關內,就是違法,而且要處死。繼母知道這條法規,所以,珠崖令死后,她將“臂鐲”棄之不用,以免引起麻煩。但是,她九歲的兒子不懂事,喜歡這些珠子,拾回來放在母親的鏡奩內,于是引出了這篇動人的故事。第三部分,是故事的高潮。他們奉喪回老家途徑海關,“關侯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繼母鏡奩中。”真是禍由天降。人贓俱在,他們只有認罪。但是,判誰的罪?女兒初與繼母兩人,表現出了無私無畏的品德。由于母女的高風亮節,感動了海關的官吏,他們下決心“吾寧坐之,不忍加文”。官吏也表現出同情,不忍心讓這母女抵罪。三個部分,始終離不開“珠子”,恰似獅子滾球,本只是一個球,卻教獅子放出通身解數,一時滿棚人看獅子,眼都看花了,獅子卻是并沒交涉,人眼自射獅子,獅子眼自射球。滾者是獅子,而獅子之所以如此滾,實都是為了球。(金圣嘆:《讀第六才子書法》)《珠崖二義》的作者象耍獅子者,一串珠子,牽動所有人的心。這就是本篇的藝術特色。
這篇小故事很有意義,本身也不含說教。但是,作品結尾的贊語,作者塞進《論語》的一段話,卻含濃厚的封建倫理道德的成分。引文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說:子若有過,父為隱之,叫做慈;父親如果有過,子為隱之,叫做孝。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所謂“直”,就是正直、無私。這種所謂的無私之愛,其內涵是對錯誤互相隱瞞。這不僅不是“直”,而且是極其自私的行為,是不可取的。這是作者的局限,時代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