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國亡詩·花蕊夫人》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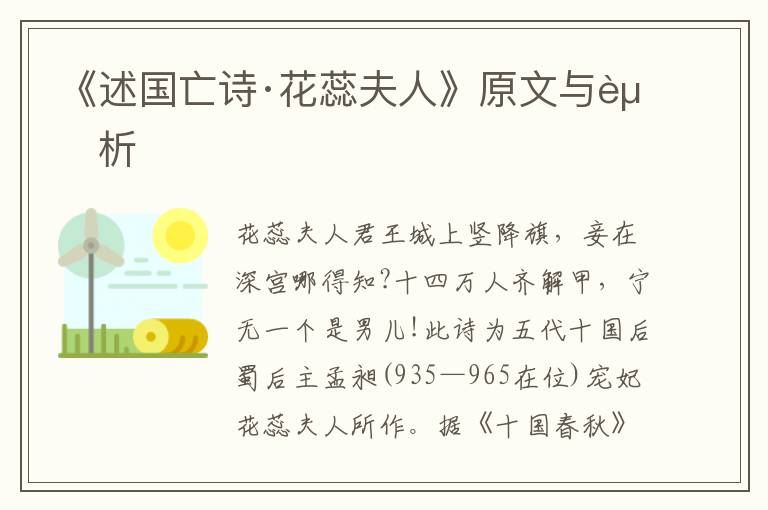
花蕊夫人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此詩為五代十國后蜀后主孟昶(935—965在位)寵妃花蕊夫人所作。據《十國春秋》卷五十:“慧妃徐氏,青城(今屬四川灌縣)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于后主,后主嬖之,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又升號慧妃。”她長于寫詩,曾仿效唐代詩人王建,作《宮詞》百余首,富獨創性。歷代宮詞作者不少,但大多為外臣,常有失實之處。徐氏以宮中人寫宮中事,皆成信史,且語言工麗,清婉可掬,出于王建而勝于王建,如“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將宮女內心的孤寞、羞怯、對自由生活的向往,描摹得細致入微, 自具風格。
后蜀亡國后,花蕊夫人同孟昶一起成了宋朝部隊的俘虜,被押至汴京。花蕊夫人充入后宮,受到宋太祖趙匡胤的寵愛。孟昶不久也就莫名其妙地死去。“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后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十國春秋》)終因不忘故國,以罪賜死。
據《十國春秋》載,太祖聽說花蕊夫人的詩寫得好,有一次要她寫詩,詩應說清蜀國亡國的原因。“其詩有‘十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同上,第二冊,七四八頁)此詩有的本子題為《口占答宋太祖》,第四行第一字作“更”或“可”,當以“寧”字在意思上更為妥貼。全詩潑辣而不失委婉,言下之意,尚不甘心,于感嘆中含有譴責,在羞愧中蘊藏力量,很是得體,從題材到風格,跟她以往的宮詞大大不同,堪稱絕唱。歷代文人都激賞此詩,魯迅在雜文《女人未必多說謊》中,也曾加以引用。
“君王城上豎降旗”,指投降宋朝是后主孟昶一個人決策的,它概括著豐富的內容。原來后蜀君臣極端奢侈淫靡,如孟昶“溺器皆以七寶裝之”,以至后來“宋太祖見寶裝溺器,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等到宋朝軍隊到來,昶“大懼,問計于左右;老將石頵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帝嘆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未幾……赍表請降。”就這樣毫無抵抗地“豎降旗”,可謂昏庸失國、懦弱無用。因此,宋朝部隊從出發到滅蜀,只花了六十六天,稱得上是一路順風了。這一句含蓄地揭露了這一事實。
“妾在深宮哪得知?”意為蜀降之事,與自己毫無關系。這就耐人尋味了。質言之,如果由我決策,恐怕就不是這個局面了。這平淡的回話,卻蘊含著巨大的力量,也包容著無限的悔恨與不盡的血淚。自古以來,人們都說女人是禍水,把商紂王的垮臺歸罪于妲己,將周幽王的被殺歸罪于褒姒,拿吳王夫差的失敗歸罪于西施……花蕊夫人以親身體驗進行申辯。不過話又說回來,在婦女毫無地位的宮中,即使她事先知道打算投降的事,并且提出反對,蜀主會聽進一個字嗎?所以,花蕊夫人的悲劇是由她所處的那個時代決定的。仔細品味此句,花蕊夫人對投降一事是感到臉紅的,比起那些毫無廉恥之心的王侯將相來,不啻有天壤之別,可謂裙釵勝須眉了。
“十四萬人齊解甲”,據《十國春秋·后蜀志》,當時宋太祖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萬人,分路進師”伐后蜀。《宋史紀事本末》云:“將步騎六萬。”總之,宋軍只有五、六萬人。而后蜀經過四十一年的經營,軍事力量是可觀的,花蕊夫人說“十四萬人”,決非虛言。從后蜀方面說,只要組織應戰,是決不會很快亡國的。可笑的是孟昶一聲嘆息、一說投降,“十四萬人齊解甲”,沒有一個愿為國捐軀的,沒有一個有大丈夫氣概的, 因此,宋軍兩個多月,就“得州四十五,府一,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不戰而降,花蕊夫人感到可恥、可悲!
“寧無一個是男兒?”她悲憤地責問:怎么“十四萬人”的蜀軍官兵中,竟沒有一個人是有血性的男子漢?她以夸張手法,進發出憤怒的吼聲,催人猛省, 發人深思!
全詩以充沛的激情表達了亡國之痛與對誤國者的怨恨。抒情主人公,一個血氣方剛的女性栩栩如生地出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一個有鮮明個性的、千百年來激勵著無數讀者的愛國志士的形象,這一形象給人以勇氣和力量。
花蕊夫人敢于在不可一世的趙匡胤面前,直陳己見,不僅有羞恥之心,而且毫不示弱,表現出非凡的膽識,后來終因懷念故國而慘遭殺害,這史實的本身就令讀者熱淚滾滾了。
這首絕句在藝術上也很成功。與她的膽識相適應,全詩回答宋太祖的提問,從容不迫,平靜自然,卻沉著有力,深含哀怨。在唐五代絕句中獨具一格。另外,兩個反問句,前者表面上是回答趙匡胤的,實際上是一種反抗;后者卻在前者鋪墊的基礎上,向古今一切無血性、不戰而降的男兒發出了責問,如狂飚乍起,似夏雷震響,尖銳潑辣,韻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