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新郎·辛棄疾》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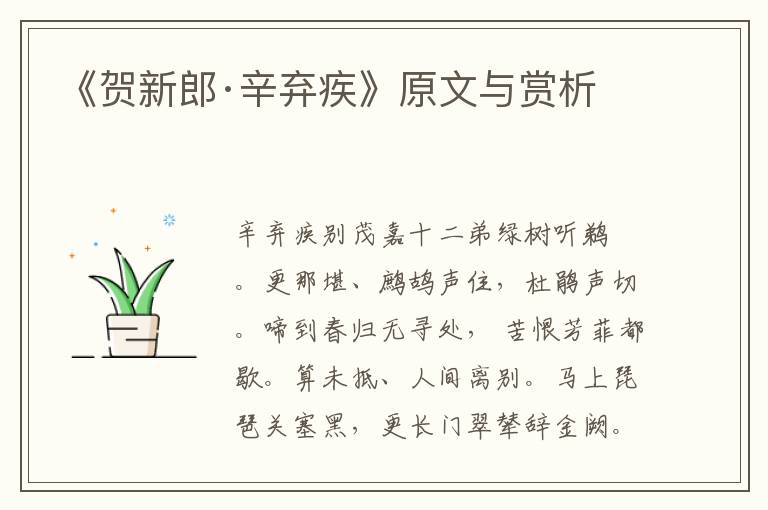
辛棄疾
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鵜鴂。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 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 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 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居士,齊州歷城人。孝宗時,以大理少卿出為湖南安撫,治軍有聲,雄鎮一方。官至龍圖閣待制。生性豪爽,尚氣節。工于詞,才氣縱橫,與蘇軾齊名,世號“蘇辛”。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等。
辛棄疾這首詞寫得很奇特,開頭一氣舉了三種鳥的叫聲,接著羅列五個典故,都與“別弟”的題意不甚相關。是在“掉書袋”,曬腹中五車書嗎?好象又不是。看,這三、五之中縱綰著“算未抵、人間離別”,“誰共我,醉明月?”別是一番氣度,別是一番格局。
那三種鳥呢?;第一種是“鵜鴂”,“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離騷》),那么第一句就明含時機蹉跎,眾芳衰歇之意了。第二種是“鷓鴣”,它“多對啼,志常南向,不思北徂”(《埤雅》),“啼到曉,惟能愁北人。”(白居易《山鷓鴣》)“畫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未穩,數聲相應在前村。”(張詠《聞鷓鴣》)那么鷓鴣聲聲,對于詞人這位南來的北人,當然“不是傷情即斷魂”了。第三種是杜鵑,相傳乃古蜀國望帝之魂所化,又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向也。”(《禽經》)鳴聲都是“不如歸去”。
“恨別鳥驚心”,詞人當年金戈鐵馬過江來,滿指望南宋朝廷一鼓作氣,討還河山,誰知徽欽二帝失國為囚,喪命于異域五國城中,中原淪喪,故鄉久違;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和戰紛紜,國事莫定,積弱難振。詞人是一腔熱血,報國無門,感觸紛至沓來。是這暮春的鳥聲觸動了他的感情,以鳥聲起興,一聲聲都是驚心慘目的血淚,一聲聲都是滿腔激越的憤懣。鳥聲奠定了全篇感情的基調。
詞人此時雖隱居瓢泉,但并沒有脫離現實,也不可能脫離現實,于是必然地使他直逼社會人事,然而對于現實他不能也不愿直說,現實的感受就很自然地和爛熟在胸中的讀破萬卷之書交相醞釀,融貫生發,以表達他心頭不吐不快的“難言之隱”、“獨喻之忱”。因而五個典故就一瀉而出了。
王昭君離宮出塞,陳皇后失寵長門,莊姜送歸妾戴媯,李陵絕域別蘇武,燕丹易水泣荊軻,如滾珠落盤,也就顧不得什么章法,什么過片提起的尋常格律了。
但詞人用典決非無的放矢,一樁樁一件件無不是現實圖景的折影。“上半闋北都舊恨,下半闋南渡新恨”(《宋四家詞選》),上半闋三件事,從后妃被逐契入,影射北宋失國,二帝蒙塵。王昭君“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詠懷古跡》),尚為和親,比之國破罄宮后妃嬪娥被虜北去,其情如何?陳皇后失寵, 比之身為天子而無力庇護后妃,一齊淪為俘囚,其情又如何?莊姜送歸妾,尚“瞻望勿及,泣涕如雨”(《詩經·邶風·燕燕》),而徽欽二帝自哀不及,其情又將如何?二帝被辱,后妃被奸淫虜掠,豈不比這些歷史更為慘痛,更為酸心刺骨。此為國之奇恥大辱。愛國之臣, 隱痛難言。
下半闋李陵、蘇武之事,正是“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杰率陷沒殊域,與草木俱腐”(劉克莊《辛稼軒集序》),從對李陵的慨嘆中表達了對淪陷北方的義軍戰友深切懷念之情。易水荊軻,則影射宋金通使事,高宗趙構以臣禮事金,至孝宗進而要以叔侄之禮事金,使者在金人面前不僅山呼舞蹈,還要折沖樽俎,種種屈辱凡有民族意識者怎能容忍,除非賣國賊,使臣無不以必死之心前去。這兩個故事,何其切合宋朝的恥辱史!
因而詞人以悲抑凄愴的語調道出“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鳥本無情尚有“如許恨”,何況人呢!何況一腔報國熱情,“壯懷激烈”的志士呢!流血終宵自不待言了,這一句呼應開篇,力貫全詞,直透紙背,刻骨銘心。
全詞到此,似題旨已明,然而上半闋“算未抵、人間離別”尚無著落,而與“送弟”亦不搭界。詞人在洋洋灑灑鋪陳之后,力挽千鈞,猛然收縮,跌出“誰共我,醉明月?”茂嘉對于詞人不僅是兄弟,而且是同心知己,憂國心碎,滿腔悲憤,只有茂嘉情同此心。如今茂嘉一去,更無知音。即此臨行之際,痛泄為快。此后天各一方,赤膽忠心,唯日月共鑒。突然而起,戛然而止,然余音裊裊,情意綿延。
本詞于豪放之中,更多的是遒勁、蒼郁、悲涼,這是有挽狂瀾之力而不用,淚眼看山河其悲憤者,有難言之隱、然不吐不快而形成的獨特風格,開別愁之另一生面。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評道:“稼軒詞,自以《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一篇為冠,沉郁蒼涼,跳躍動蕩,古今無此筆力。”確是的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