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詩·王粲》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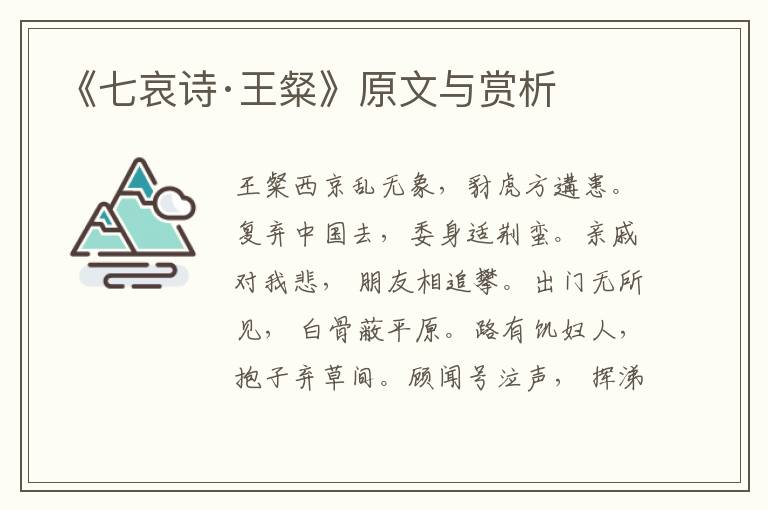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 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 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 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 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少年時就有才名,是“建安七子”中的代表人物。漢獻帝三年(192)時因董卓部將李傕、郭汜在長安作亂,他避難到荊州去,依附劉表,但未受重用。到建安十三年(208),他歸附曹操,位居列侯,官至侍中。他經歷了戰亂, 目睹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百姓遭殃的慘象,所以作品多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有《王侍中集》。
《七哀詩》共三首,不是一時之作,歷來公認是王粲的杰作。這里選的是第一首。“七哀”表示哀思之多。這首詩是他離開長安往荊州避難時所作,寫途中看到的離亂景象和自己的悲痛心情。
在詩中作者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寫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是一篇真實反映當時社會情況的詩。要更好地理解這首詩,須先了解當時軍閥混戰的情況和人民所受的苦難。東漢末年已是軍閥連年混戰的局面。一九○年大軍閥董卓進占洛陽后,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屠殺反對派,并且驅趕洛陽地區的百姓遷往長安,沿途死人無數。洛陽內外二百里地面所有公私房屋全被燒毀。一九二年董卓被殺,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人大殺官員并屠戮長安城,老少不留。這群豺虎又互相混戰,長安被燒為空城,關中數十萬戶居民,死亡殆盡,附近幾百里內不見人跡。加上這批野獸搶掠糧食,人民大批餓死,在殺死和餓死的同時,連年戰爭帶來了疫病流行。漢靈帝時就有大疫五次,漢獻帝時更加嚴重。屠殺、搶掠、疫病三種大災使得人民流離轉徙、饑餓死亡,其悲慘情景達到無法形容的程度。連曹操這個參加殺人的人也說:“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詩一開頭就展示出軍閥混戰,屠戮長安城的社會背景,并且憤怒斥責那批禍國殃民的軍閥是毫無人性的“豺虎”,指出這場災患就是他們制造的。接著用一“復”字,表明自己因戰亂頻繁,已經歷過一再的播遷(王粲原來隨父親住在洛陽,被迫遷往長安,這次避難離開長安, 已是第二次流離了,當時他年僅十六歲)。“委身”一詞更透露出去國離親,遠遷異邦、托身于人的內心悲涼。“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親戚的悲痛,朋友們的攀車追隨不忍分別,表現出離亂年代親朋間生離死別的哀傷。這兩句從親友方面的神態來反映別情的凄愴,雖沒直抒己意,但同樣映襯出自己內心的悲痛。這種襯托的表現方法,在描寫雙方感情共鳴的情景時,特別顯得真切生動而且含蓄精致。王粲出身世家,所遭戰禍已這樣可悲,由此可想見平民百姓的災難當更加悲慘了。
中間八句寫路上所見的慘象。“出門無所見, 白骨蔽平原”,這是剛出長安城所見。昔日繁華的京畿,現在是一片廢墟,真是“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這兩句具體地概括了當年關中平原上的慘景。接著,饑婦人的特寫場面更加令人怵目驚心,慘不忍聞。“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顧”字寫出饑婦人棄而不舍的傷痛心理;“獨不還”更表現出她最后橫下心來不忍回頭的內心摧折。“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這是一位被饑餓所迫而棄子的母親,在不能兩完的情況下所選擇的唯一可以僥幸保全兒子的辦法。但是在任何人也無法生存下去的時候,她的兒子又怎能獨存呢!短短十個字,包含著人民的多少血淚!這些觸人魂魄的詩句,又寄托著詩人對人民多么深切的同情!
最后,詩人登上霸陵(漢文帝陵墓,文帝史稱西漢賢君)高處,回望長安。撫今追昔,領悟到《詩經·下泉》作者那種急切思治的心情,不禁痛心時事,為憤世憂民而喟然長嘆了。
這首詩在藝術表現上也有著明顯的特點:
一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它取材于現實生活,本質地反映了社會矛盾,通過高度的概括,以“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這一典型事件,深刻揭露了漢末幾十年間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現了人民遭受戰爭破壞的苦難生活,并且表示了同情人民的深厚感情。詩以個人的途中經歷為線索,把自己的感情和人民的痛苦聯系在一起。這種感情又是逐步發展的,從個人流徙產生的哀怨,擴大到對人民苦難的同情,最后發展成為對國難民瘼的憂嘆,表現出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
二是白描筆法。全詩不論敘事、抒情都是直陳白描,不事渲染,不加夸飾。娓娓道來,卻是曲折盡意,增加了真實樸素的感覺。詩人藝術技巧的成熟精妙由此可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