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車·劉叉》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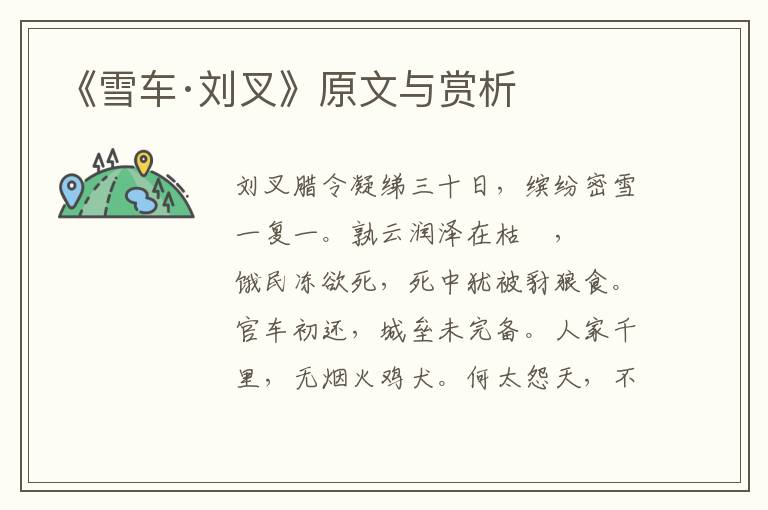
劉叉
臘令凝綈三十日,繽紛密雪一復一。孰云潤澤在枯荄,阛阓餓民凍欲死,死中猶被豺狼食。官車初還,城壘未完備。人家千里,無煙火雞犬。何太怨天,不恤吾氓?如何連夜瑤花亂?皎潔既同君子節,沾濡多著小人面。寒鎖侯門見客稀,色迷塞路行商斷。小小細細如塵間,輕輕緩緩成樸簌。
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御炎酷。徒能自衛九重間。豈信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刀兵殘喪后,滿野誰為載白骨?遠戍久乏糧,太倉誰為運紅粟?戎夫尚逆命,扁箱鹿角誰為敵?士夫困征討, 買花載酒誰為適?
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依違用事佞上方, 猶驅餓民運造化防暑阨。吾聞躬耕南畝舜之圣,為民吞蝗唐之德。未聞孽苦蒼生,相群相黨上下為蟊賊。廟堂食祿不自慚,我為斯民嘆息還嘆息。
盧仝以《月蝕詩》稱怪,劉叉以《冰柱》、《雪車》二詩怪稱。《冰柱》詩《唐詩鑒賞辭典》已選,故本書選《雪車》詩,可兩不相犯。宋代葛立方的《韻語陽秋》說:“劉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于正也……《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御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其實,《雪車》詩除了有些散文化的傾向有的句子顯得有些生硬拗口外,無論從形象、意境、構思到造句都并不怎么怪。倒是作者劉叉的為人頗有些怪異。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五說:“叉,節士也。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俯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孟右。樊宗師見,獨為拜。后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這首詩把矛頭直接指向天子,批判他只知道自己享受,絲毫不關心老百姓的死活,既不用比興手法指東說西,也不吞吐隱約其辭,而是毫不掩飾地直陳其辭,直接指著帝王的鼻子痛訴。要說此詩怪,恐怕主要怪在這一點上。
全詩分三段。
第一段寫連綿不斷的大雪,使許多城市貧民凍餓而死,又遭官車趁火打劫,造成千里無人煙的蕭條景象。開篇四句寫大雪景象:這一年,臘神命令鋪上厚氈天地縞素帶孝三十日,因此繽紛大雪下了一天又一天;誰說“瑞雪兆豐年”,雪水能滋潤莊稼的枯根呢?市區居民都將被凍死了!“綈”,本指一種粗厚光滑的絲織品;但《急就章》上有“綈絡縑練素帛蟬”的話,因此詩中“凝綈”為活用,極為形象地寫出大雪紛紛揚揚下個不停的景象。一開始雖為寫景,但與饑民的生活緊緊聯系在一起,飽含同情心,給全詩定下了基調。接著七句,話題轉換,說饑民“死中猶被豺狼食”。是四腳豺狼,還是兩腳豺狼?觀下文即明。官車剛從戰場上開回來,由于城墻尚未修筑完備,官兵趁機遛出城市,下鄉打劫,造成千里無人煙雞犬的蕭條破敗景象,又何必過分埋怨蒼天不同情愛撫人民呢?先描述天災,轉而描述人禍,過渡極其自然,語言又極其尖刻。而中華書局排印本《全唐詩》將這幾句斷為“官車初還城壘未完備。人家千里無煙火。雞犬何太怨。天不恤吾氓。”這樣斷句不僅造成“雞犬何太怨”一句文義不通,還把罪責完全歸之于天時,這與詩人原意也完全不合,因此我們認為是完全斷錯了的。最后七句繼續寫大雪景象。先以“如何連夜瑤花亂?”一問句承上啟下,天該怨,因為大雪畢竟凍死了大量饑民;天不必太怨,因為人禍危害更烈。詩人用詞極有分寸。“皎潔既同君子節,沾濡多著小人面”兩句含義很深:上層社會的人物只注意雪的潔白的顏色,將其與君子的節操聯系起來,把它看得很神圣;下層社會的人物關心的則是雪帶來嚴寒,沾在臉上鉆筋刺骨,威脅著他們的生命。所以一個把它看作是福音,一個則把它看作是災星。“寒鎖侯門見客稀”,侯門之內正好擁火宴飲作樂;“色迷塞路行商斷”,旅途之上行商必然挨凍發愁。小雪細細屑屑猶如塵粉,大雪輕輕緩緩堆成小樹。詩人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把雪寫足了,但重點仍在雪給貧民帶來災難。
第二段寫官車載雪供宮中享用,不載白骨,不載軍糧,真太不象話了。官家根本不了解人民在挨餓受凍,滿路上盡是裝載象玉屑一樣白雪的牛車。原來是為了“秘藏深宮,以御炎酷”的。寫到這里,詩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憤怒地責問天子:“徒能自衛九重間, 豈信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 ”你們只知在深宮享樂,自顧自地講究養生之道,你們可相信,車轍中的點點血跡,都是農夫哭出來的!接著,詩人又情不可遏地、連珠炮似地發出—連串的責問:戰爭和天災過后,滿野白骨你們為什么不去裝載?遠戍士兵急需軍糧,太倉紅粟你們為什么還不運了去?藩鎮抗命叛逆,靠誰去排除障礙、沖鋒陷陣?將軍與士兵都困于征討,官車上買花載酒又供誰享用?這些責問如利箭似的射中了封建統治者的要害,他們是無法回答的。雖說在唐代文禁比較松弛,但象這樣直接指著帝王鼻子責問,還是需要極大膽量的。詩人曾在《自問》詩中自豪地宣稱“酒腸寬似海,詩膽大于天”!他又曾在《答孟東野》詩中表示“百篇非所長,憂來豁窮悲。唯有剛腸鐵,百煉不柔虧”!看來,劉叉確是一位具有俠骨剛腸的硬漢子,他是說到便能做到的!
第三段通過議論,進一步批判朝廷君臣“相群相黨上下為蟊賊”。詩人激憤地說,天子端然高坐,絕少聽取下面的意見。而他的股肱大臣和左右耳目又都是些奸邪小人,常常隱瞞住事實真相。他們依違用事諂媚上級,在如此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情況下還要去運雪防暑。我聽說舜親自跟人民一起耕種才能成為圣人,為民吞蝗是我大唐王朝先帝的美德,從來沒有聽說作孽苦害蒼生、上上下下勾結起來當蟊賊的!那些坐在朝廷上享受食祿的官員們難道不覺得慚愧嗎?我真要為老百姓嘆息了再嘆息!這一段干脆利落,俱是針針見血之論。詩人“野夫怒見不平處,磨盡心中萬古刀”(《偶書》)的性格得到了異常真切的表現。
總之,我們認為這是一首關心民生疾苦、為民請命的好詩,它的價值,是并不在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之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