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慢·姜夔》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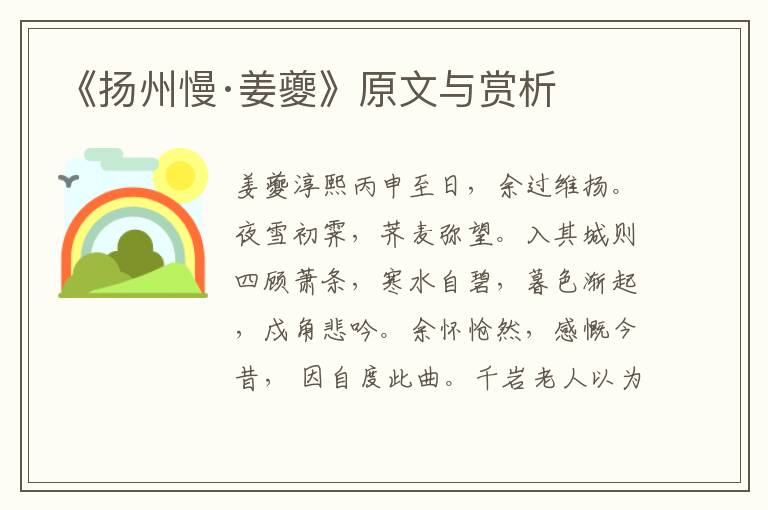
姜夔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余懷愴然,感慨今昔, 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 竹西佳處, 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 盡薺麥青青。 自胡馬窺江去后, 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 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 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 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姜夔(約1155—約1221),字堯章,南宋饒州(今江西鄱陽縣)人。父噩,宋高宗趙構紹興三十年進士,任漢陽知縣。“夔孩幼隨宦,往來沔鄂幾二十年。”(姜虬綠《白石道人詩詞年譜、世系表》)孝宗趙眘乾道四年十四歲時,他父親離世。淳熙三年,他二十二歲,“至日過維揚,作《揚州慢》”(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此后十年,他來往于今贛、皖、蘇間,作名公巨卿的清客,政治上很不得志。淳熙十三年,至長沙依著名詩人蕭德藻,“德藻自謂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周密《齊東野語》),“以其兄之子妻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后隨蕭德藻調任而寓湖州,結交了楊萬里、范成大等文壇巨擘。光宗趙惇紹熙元年,“卜居白石洞下”,人稱之“白石道人”。此后仍到處依人作客, 以布衣終身。
姜夔一生寄人籬下,內心抑郁,視野不廣。但是,他對南宋小朝廷的茍且偷安、向金國的一再讓步,時有不滿。這說明他并未忘懷國事。他跟著名愛國文學家辛棄疾亦有交游,受到一定的影響。
姜夔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詩、詞、書法、音樂皆有名于時,而詞的成就尤為卓著。從內容看,有關懷國事的悲苦之作,這是最有價值的,雖然數量不多, 而詞中大多為自傷身世、應酬倡和、懷念情人、詠物寫景之作。從藝術上說,姜詞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他的詞集中有十七首自度曲,每首注有旁譜,是現存的詞和樂譜的合集。姜詞風格清剛,情韻綿邈,用字造句,刻意精心。他想以清剛來救治婉約派軟媚之病,以綿邈來避開豪放派粗獷之弊。因此,他的詞讀起來,確是“別有一股滋味”,清新剛健,感情深沉,耐人尋味,音樂感強。這種風格對后代影響深遠。
《揚州慢》描繪了揚州在金人多次入侵后的殘破荒涼景象,抒發了作者對國事興衰的無限感慨。
揚州自古繁華,從唐代以來即為國內外商業貿易的要地。可是南宋小朝廷建立后,這里卻成了宋金雙方激烈爭奪的戰場。宋高宗趙構建炎元年(1128)秋天,金兵在宗弼(兀術)率領下南進,次年侵占揚州,焚掠一空。紹興四年(1134)韓世忠大敗金兵于揚州。紹興十一年(1141)“紹興和議”成立,劃定東起淮水,西至大散關一線為宋金分界線。揚州再次暴露于金人眼前。紹興三十一年(1161)秋天,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渡過淮河,侵入揚州,飲馬長江,揚州城再次遭到浩劫,元氣大喪。隆興二年(1164)“隆興和議”后,七月,南宋撤兩淮邊備及海、泗、唐、鄧州之戊,金人又乘機侵占揚州,燒殺搶掠,無所不為, 自此元氣不能恢復了。
十五年后即宋孝宗趙眘(慎)淳熙三年(1176),姜夔從湖北順江東下,經過揚州,看到這座名城一片破敗景象而自制《揚州慢》詞。作者的小序交代了寫作動機,他說,這年冬至日,我經過此城。他所說的“維揚”即揚州,《尚書·禹貢》:“淮海維揚州。”后代遂借來作地名。這天夜里下雪,剛剛轉晴。在郊外看到的全是薺菜與野麥。進城后四顧,一派衰敗荒涼景象,冰冷的河水在白雪映襯下綠得發黑,清冷至極。天色漸漸暗淡下來,駐軍號角悲壯地響起,使這座荒城更顯得空曠凄涼。我萬般感慨,十分悲傷,創制《揚州慢》曲調并填了詞,抒發胸臆。叔丈、大詩人蕭德藻吟誦后,認為此詞和《詩經·王風·黍離》一樣,表達了國家衰亡、都城荒廢的悲哀之情。這短序是一首優美的散文詩,意境有致,寄托遙深,心情酸楚。它形象地告訴我們,他是為追懷傷亂,感慨今昔而創制此詞的。它曲折地表達了作者對金國入侵的憎惡,對南宋畏葸讓步的不滿,抒發了愛國之情。
詞的上片寫景。開手破題,從揚州說起。“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淮左”,淮河東部,從行政區域看,宋代淮河南岸設淮南東路與淮南西路,“淮左”即淮南東路。揚州是該路治所,著名都市。“竹西”,指城東北禪智寺畔的竹西亭,此處竹林蔭翳,幽靜迷人,是揚州景色最佳之處。唐代杜牧曾在《題揚州禪智寺》中以“斜陽竹西路,歌吹是揚州”之句,描寫了這兒的優美景色與游人之盛。這歷史名城,這竹西風光,作者向往已久,今日到來,情不自禁地“解鞍少駐初程”,在改為長途陸行的開始階段,稍事休整。這幾行極寫對美麗揚州的心馳神往。揚州位于長江下游北岸,大運河與大江交會處。城建于二千四百多年前吳王夫差時期。至隋唐時期,大量中外商品在此集散,這里就成為東南最大的商業城市與外貿港口,繁榮興旺,名聞中外。揚州城是我國人民的驕傲,祖國繁榮昌盛的象征。歷代文人過此,都留下了優美詩章。可是作者今日到此,卻十分失望,所見為一片荒涼景象,“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十里揚州路上,春風輕輕吹過,再也見不到往昔“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樓上看神仙”(唐代張祜《縱游淮南》),“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杜牧《贈別》)的盛況了,到處是薺菜、野麥,真是山河破碎,草木叢生啊!這兩行跟前三行強烈對比,蘊含著作者失望與痛苦之情。這兩行的轉折使前三行看似平板的句子含蓄深沉了。
下面寫造成巨變的原因,“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金人的多次入侵,使揚州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連那廢棄了的池苑與兵火后幸存的老樹,也怕談起戰亂,更何況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呢!作者以意為主,在寫景中寄托了沉重的“黍離”之悲與國破之痛。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再正面直寫揚州城的破敗情景,“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漸近黃昏的時候,號角聲帶來更深的寒意,凄涼蕭索,籠罩孤城。作者極力渲染這一氛圍,旨在表達對邊防空虛的無限憂慮。上片寫所見,四層三轉折,“寫兵燹后,情景逼真”(《白雨齋詞話》)。
下片寫所感。換頭處回到杜牧身上:“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杜牧即使有勝賞的本領,料想他今日至此見到這殘破景象也會大吃一驚。再深入一層:“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縱然他有寫“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贈別》)的才華,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遣懷》)的感受,也難以表達我現在懷念故國的“深情”了。質言之,面對今日揚州,他再也不過冶游生活,不寫小兒女的柔情了。他一定會陷入巨大的創痛中,寫出《黍離》式的名篇來的。這是為杜牧設想,借以表達自己憫亂傷時的感情,虛擬頓挫,更耐人尋味。
第三層又回到現實:“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二十四橋”仍然在城西郊,可是昔日“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的繁華消失了,爾今月夜依舊,橋下寒波蕩漾,一彎冷月無聲地在波心微微顫動著,空曠、寂寥而又凄清。這就加深了讀者對亂后揚州的認識與感受。景中含情,畫中有意,可以想見作者在慘白的月色中失聲慟哭的情景,體會到對南宋小朝廷茍且偷安,“西湖歌舞幾時休”腐朽生活的強烈不滿。先遷甫在《詞潔》中贊揚“蕩”字,說是“一字得力,通首光彩。”唐圭璋亦云:“‘二十四橋’兩句, 以現景寓情,字煉句烹,振動全篇。”
末層為揭拍:“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可憐橋邊的紅芍藥花,年年花開花落, 自生自滅,昔日賞花之人俱已被戰爭奪去生命;那末這嬌艷的花朵今日為誰而開?以名花無人欣賞作結,悲嘆“名都”已成“空城”的不幸,含哀無限。劉永濟在《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中說:“曰‘知為誰生’者,傷‘俊賞’無人也。言外更有舉國無人,危亡可懼之意,不但感一時之盛衰也。”其言甚善,可知該詞結尾加深了全詞主旨。下片寫感抒情,也是四層三轉折,詩人通過“橋”、“月”、“水”等今昔巨大變化,突出了內心的悲惻愴傷。
據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這詞作于隆興戰敗之后”,描寫了揚州城的荒蕪黯淡景象,揭露金國統治者的暴行,抒發對中原淪陷的哀思,寄寓對南宋小朝廷軟弱讓步的不滿。這首詞在姜夔“淺斟低唱”的作品中堪稱上乘之作。
這首詞布局嚴密,情景交融。上片寫所見,景中有情, 下片寫感觸,情寓景中,把淪喪之痛,黍離之悲,深刻地表達出來。作者寫景,用駐、看、聞、念為線索,步步寫來。而又翻騰折進,極盡變化之妙。情隨景移,逐層加深。沈祥龍《論詞隨筆》云:“詞之妙在透過,在翻轉,在折進……三者不外用意深而用筆曲。”這首詞達到這一藝術要求。作者觀察細致,體物入微,讀者在一幅幅畫面中看到“薺麥”的綠色,聽到“清角”的凄惻嗚咽,嗅到“紅藥”的清香……達到“詞之為物,色香味宜無所不具”的境地(劉熙載《詞概》)。作者寫景還善于將動態與靜境結合,虛寫與實描相配,橋邊月夜,死一般寂靜,然著一“蕩”字,立使“冷月”顫動起來。凄楚的清角,使“空城”更顯得寂寥曠遠……作者多次化用杜牧詠揚州詩意,極力寫揚州昔日的紛華,從而實描出今日之殘破頹敗。可謂“以樂景寫哀,倍增其哀”(王夫之《姜齋詩話》)。
音韻諧婉,辭句精美。姜夔追求精當的音律,所以作品的音樂感忒強。此詞一韻到底,按戈載的《詞林正韻》,是“平聲庚青蒸”,屬較強級,與全詞沉痛、激忿、不滿情緒合拍,與“南渡以后,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于詞中寄慨”協調(《白雨齋詞話》)。領字短促有力,過、自、漸、算、縱、念皆為去聲,從而使每一層的聲音由低到高,從促而緩,增添了令人回味的音樂美。作者煉字烹句,十分刻苦。小序與詞配合默契,一散一韻,對于感情的抒發,相得益彰。南宋張炎在《詞源》中說,白石“句法挺異……能持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姜夔用詞遣句都著意追求清空的風格。沈祥龍說:“清者,不染塵埃之謂;空者,不著色相之謂。清則麗,空則靈。”劉永濟《詞論》卷下:“清空云者,詞意深脫超妙,看似平淡,而義蘊無盡,不可指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味,這首詞意不淺露,語不窮盡,句有余味,篇有余意,詞境深靜,寄托深遠,故王國維《人間詞話》云:“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