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哀公篇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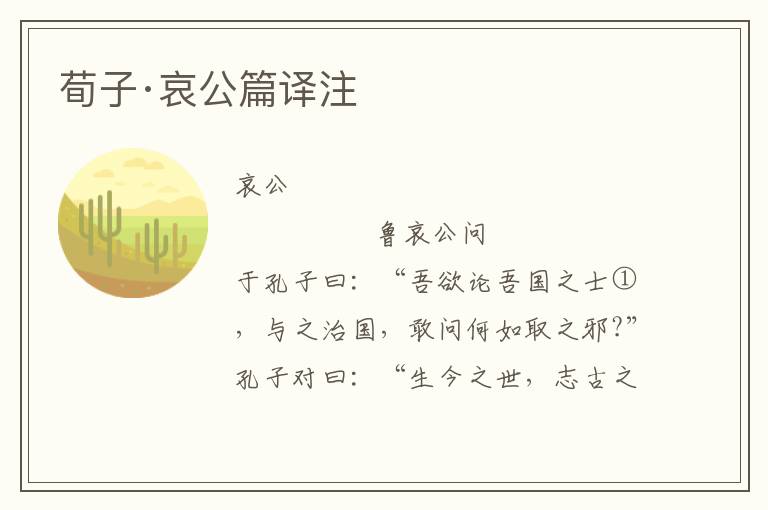
哀公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①,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②,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③,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 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④,志不在于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⑤,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注釋] ①論:選擇。 ②舍:處。 ③章甫:商代的一種帽子。絇(qú渠)屨:帶有絇飾的鞋。絇,古代鞋頭上的裝飾,用于穿系鞋帶。“紳”下當脫一“帶”字。搢(jìn晉):插。④端衣:祭祀時穿的禮服。玄裳:祭祀時穿的黑色的裙。路:大車。⑤斬衰:古代最重的一種喪服,用粗布制成,不緝邊。菅屨:草鞋。啜(chuò綽):吃。
孔子曰:“人有五儀①: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圣。”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②;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③,止交不知所定④;日選擇于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正⑤,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遍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⑥,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大圣矣?”孔子對曰:“所謂大圣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⑦。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⑧,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于風雨,繆繆肫肫⑨。其事不可循⑩,若天之嗣(11);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12)。若此,則可謂大圣矣。”哀公曰:“善!”
[注釋] ①儀:等級。②色色:當為“邑邑”,憂郁的樣子。③勤:當為“動”字。④交:當為“立”字。⑤五鑿:五情。⑥怨:通“蘊”,積蓄,蘊藏。⑦不:通“否”,然不,然否,是非、對錯。⑧辨:通“遍”,遍及。⑨繆繆:通“穆穆”,和美的樣子。肫肫:通“純純”,精密的樣子。⑩循:通“揗”,模仿。(11)嗣:通“司”,主宰。(12)鄰:連接。
魯哀公問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①,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注釋] ①務:通“冒”,便帽。拘領:曲領,用以繞頸。拘,通“句”,彎曲。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圣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①,仰視榱棟②,俛見幾筵③,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④?君昧爽而櫛冠⑤,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⑥,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⑦,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注釋] ①胙階:東階,主人迎接賓客的臺階。胙(zuò作),通“阼”,臺階。②榱(cuī崔):椽子。③俛:同“俯”,低頭。④而:能。⑤昧爽:黎明。櫛(zhì質)冠:梳頭戴帽。⑥昃(zè仄):太陽偏西。⑦虛:同“墟”,廢墟。數蓋:數處。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①?”孔子蹴然曰②:“君號然也③! 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④,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⑤,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注釋] ①委:周代的一種黑色絲織禮帽。②蹴然:變色的樣子。③號當為“胡”字。④黼(fǔ府)衣、黻裳:均為祭服。⑤肆:市場。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①,無取詌②,無取口啍③。 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 故弓調而后求勁焉,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愨而后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爾也④。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⑤,暗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則亡。”
[注釋] ①健:指爭強好勝的人。 ②詌:通“鉗”,指用武力脅制人。 ③哼(zhūn諄):同“諄”,能說會道。④爾:通“邇”,近。⑤怒:此處泛指恩怨、感情。
定公問于顏淵曰①:“東野子之善馭乎②?”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③。”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④,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⑤,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⑥!”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⑦,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 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注釋] ①定公:魯國國君,名宋。②東野子:魯定公時善于馴馬駕車的人,姓東野,名畢。“子”是對人的尊稱。馭:駕馭車馬。③失:通“逸”,逃奔。④校:負責養馬的官。⑤驂(cān參):古時用四馬拉車,兩旁的馬稱“驂”,中間的馬稱“服”。列:同“裂”。⑥趨:通“促”,督促。⑦是:后當脫一“以”字。
【鑒賞】 荀子著文,多以論述中心為其題目,而此篇《哀公》乃以一國君為題,所述多為魯哀公與孔子的對話,頗有拼湊之嫌。然而聽其徐徐道來,胸臆間亦不免漸生興亡之悲。
從歷史上來看,魯哀公可稱是一個昏庸的諸侯。其在位時,正是春秋末年吳越爭霸之際。當時的魯國,內有權臣季氏當道,外有齊國屢次莫名的討伐,又曾遭到吳國的侵犯,然而哀公卻如同一個無知的孩童,將自己的眼光只界定于觸手可及的宮墻之內,甚至為自己不曾了解哀傷、憂愁、勞苦、恐懼、危險而焦躁不安。面對這樣不知世事的君主,連孔圣人也啼笑皆非:“君之所問,圣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然而,孔子在自嘲之后還是不得不一步步地啟發:您看到宗廟里的玉器是先王留下的,然而物在人亡,不是會感到哀傷嗎?您每天處理國家大小事務,但如果有一件沒辦好,可能就會帶來災禍,難道這不是令人發愁的事嗎? ……不過夫子的滔滔大論顯然沒有打動哀公,他所感興趣的也無非是古代的禮服、禮帽之類。
面對這樣一位昏庸的君主,孔子顯然是非常痛苦的。然而,即使自己曾經說過“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的話,即使內心對于“不可雕也”(《論語·公冶長》)的“朽木”有著極強的排斥感,但為了魯國的興盛,夫子仍然是“不俟駕行”(《論語·鄉黨》)地努力向哀公進諫。偶爾哀公興致所至,也隨口說起如何選擇人才的話題,夫子便率爾而對:“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在夫子看來,今世之所以禮崩樂壞,乃是在于古代的文化傳統失落了。雖然圣人的衣冠仍舊為人們津津樂道,但不過是懷舊的時尚而已。上古的風范、圣人的美德這些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卻為人們所遺忘了。“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圣人的光輝并不是來自華麗的衣著,而是來自他們奉行仁義的美德。所以即使是衣冠樸拙,也同樣受到天下的尊崇。“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論語·陽貨》)相比于追求小道的快樂,君王應關注的難道不是大道的安定嗎?而對于如何治國,孔子則提出一方面要實行仁道,另一方面則須選取人才,罷黜爭強好勝、好用武力、巧言令色之徒,拔擢士人、君子、賢人,尤其是大圣。因為圣人乃是智慧的化身,“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了解事物的一切發展規律,自然能夠通古今之變,輔佐君王完成天下大治。雖然這其中有一廂情愿的想象,但對于統治一個國家來說,選拔人才的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然而悲哀的是,夫子面對的正是這么一個“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的庸人,雖然他不會像某些暴君那樣,做出驚天動地的惡行,但同樣會造成生靈涂炭、國滅身亡的后果。雖然時時把“善”字掛在口頭,但勸諫之言就仿佛一陣清風,絲毫不曾被采納。據《史記》記載,哀公的晚年在三桓的追殺之下,奔亡于衛、鄒、越國之間,雖然最終回國而又卒亡。設想其在奔亡之際,倘若想起早年夫子的諄諄教誨“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也許會感到一絲諷刺罷。
雖然后世學者多有考證,認定《哀公》篇乃偽托圣人之言,然而當我們誦讀此篇的種種哲言,來對照魯哀公的生平事跡,尤其是其最后的奔亡之事,仿佛間又聽到了歷史的警鐘鳴響。掩卷之際,當哀而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