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太史公自序》譯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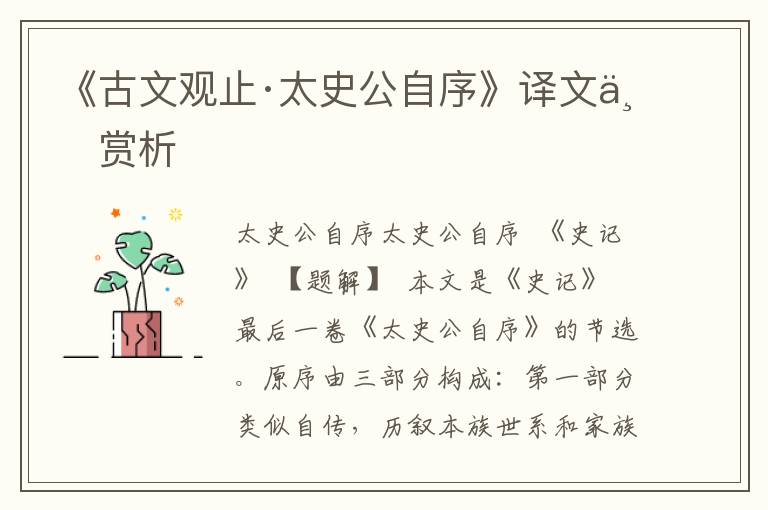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史記》
【題解】
本文是《史記》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的節(jié)選。原序由三部分構(gòu)成:第一部分類(lèi)似自傳,歷敘本族世系和家族的淵源,并概括敘述了作者的前半生的經(jīng)歷。第二部分即本文,利用對(duì)話的形式,敘寫(xiě)編撰《史記》的目的和作者的一系列遭遇,揭示作者忍辱負(fù)重的博大胸襟和強(qiáng)烈的歷史使命感,抒發(fā)了郁結(jié)于胸的悲憤不平之氣。第三部分是《史記》一百三十篇的小序。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31],正《易傳》,繼《春秋》,本《詩(shī)》、《書(shū)》、《禮》、《樂(lè)》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注釋】
[31]紹明世:紹,繼續(xù)。明世:太平盛世。
【譯文】
太史公說(shuō):“先父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自周公死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已經(jīng)有五百年了,應(yīng)該是到繼承圣明世代的事業(yè),修正《周易》,續(xù)寫(xiě)《春秋》,探求《詩(shī)經(jīng)》、《尚書(shū)》、《禮》、《樂(lè)》的本原的時(shí)候了。’他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啊!他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啊!我怎么敢推辭呢?”
【原文】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dá)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jiàn)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譯文】
上大夫壺遂說(shuō):“以前孔子為什么要寫(xiě)《春秋》呢?”太史公說(shuō):“我聽(tīng)董仲舒說(shuō):‘周王朝衰敗,孔子出任魯國(guó)的司寇,諸侯們忌恨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huì)被采用,政治主張也不可能被推行,因而評(píng)定了二百四十二年歷史的功過(guò)是非,作為天下行事的標(biāo)準(zhǔn),褒貶天子,斥責(zé)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shuō):‘我與其空泛地記載我的主張,不如用歷史事實(shí)來(lái)體現(xiàn)更為深刻、明顯。’
【原文】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32],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guó),繼絕世,補(bǔ)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yáng)、四時(shí)、五行,故長(zhǎng)于變;《禮》經(jīng)紀(jì)人倫,故長(zhǎng)于行;《書(shū)》記先王之事,故長(zhǎng)于政;《詩(shī)》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zhǎng)于風(fēng);《樂(lè)》樂(lè)所以立,故長(zhǎng)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zhǎng)于治人。
【注釋】
[32]紀(jì):綱紀(jì),倫理綱常。
【譯文】
《春秋》這部書(shū),對(duì)上則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治世之道,對(duì)下則辨明了為人處世的倫理綱常,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確定了猶豫難定的事,褒揚(yáng)了善良,貶斥了邪惡,尊敬了賢人,鄙薄了不肖,保存了亡國(guó),延續(xù)了絕世,修補(bǔ)了弊端,振興了衰廢,這都是王道的重要內(nèi)容。《易》昭示天地、陰陽(yáng)、四季、五行,所以長(zhǎng)于變化;《禮》調(diào)整了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所以長(zhǎng)于指導(dǎo);《尚書(shū)》記載古代帝王的事跡,所以長(zhǎng)于政事;《詩(shī)》記述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的狀況,所以長(zhǎng)于教化;《樂(lè)》使人樂(lè)在其中,所以長(zhǎng)于調(diào)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zhǎng)于治理百姓。
【原文】
是故《禮》以節(jié)人,《樂(lè)》以發(fā)和,《書(shū)》以道事,《詩(shī)》以達(dá)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shù)萬(wàn),其指[33]數(shù)千。萬(wàn)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guó)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注釋】
[33]指:同“旨”,要旨。
【譯文】
因此,《禮》是用來(lái)節(jié)制人的行動(dòng)的,《樂(lè)》是用來(lái)調(diào)和人的性情的,《尚書(shū)》是用來(lái)指導(dǎo)政事的,《詩(shī)》是用來(lái)表達(dá)內(nèi)心情意的,《易》是用來(lái)闡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lái)說(shuō)明天下正義的。把一個(gè)混亂的社會(huì)引導(dǎo)到正確的軌道上,沒(méi)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shū)有數(shù)萬(wàn)字,所闡明的要旨也數(shù)千,萬(wàn)事萬(wàn)物的成敗、聚散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書(shū)中,記載臣?xì)?guó)君的有三十六起,滅國(guó)的有五十二個(gè),諸侯四處逃奔仍不能保全其國(guó)家社稷的數(shù)不勝數(shù)。觀察他們之所以如此,都是因?yàn)槭チ送醯乐尽K浴兑住飞险f(shu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原文】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guó)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jiàn),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jīng)事[34]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quán)[35]。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shí)[36]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注釋】
[34]經(jīng)事:日常的事情。經(jīng),正常,日常。
[35]權(quán):變通。
[36]實(shí):實(shí)心,本意。
【譯文】
所以說(shuō):‘臣子殺死君王,兒子殺死父親,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zhǎng)時(shí)間逐漸形成的。’因此,為君者不可以不知曉《春秋》,否則當(dāng)面有小人進(jìn)獻(xiàn)讒言而自己卻看不出;背后有竊國(guó)之賊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則處理日常事務(wù)就不知道如何采取適宜的辦法,遇到出乎意料的事也不會(huì)用變通的權(quán)宜之計(jì)去對(duì)付。身為國(guó)君或身為人父,如果不知曉《春秋》的要旨,一定會(huì)蒙受罪魁禍?zhǔn)椎膼好W鳛槌枷潞蛢鹤拥模绻恢獣浴洞呵铩返拇罅x,必定會(huì)陷入篡位殺父的法網(wǎng)中,得到該死的罪名。其實(shí)他們都以為自己在干好事,只是因?yàn)椴欢Y義,受到別人毫無(wú)根據(jù)的譴責(zé)也不敢反駁。
【原文】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wú)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guò)也。以天下之大過(guò)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jiàn),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譯文】
由于不知曉禮義的要旨,以至于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君不像君大臣就會(huì)犯上作亂,臣不像臣就會(huì)遭到殺身之禍,父不像父就是沒(méi)有倫理道德,子不像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是天下的大過(guò)錯(cuò)。如果把天下最大的過(guò)錯(cuò)加給他們,他們也只有接受而不敢推辭。所以《春秋》這本書(shū),是禮義的根本宗旨。禮的作用是在壞事發(fā)生前就加以禁止,法的作用是在壞事發(fā)生后加以處置。法的作用顯而易見(jiàn),而禮的作用就很難被人們所理解。”
【原文】
壺遂曰:“孔子之時(shí),上無(wú)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dāng)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wàn)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shū)》載之,禮樂(lè)作焉。湯、武之隆,詩(shī)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dú)刺譏而已也。’
【譯文】
壺遂說(shuō):“孔子的時(shí)代,國(guó)家沒(méi)有英明的國(guó)君,下層的賢才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作《春秋》,依靠文章來(lái)判明什么是禮儀,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xiàn)在您上有英明的君主,下有恪守本職的臣子,萬(wàn)事已經(jīng)具備,各項(xiàng)事情也都按照秩序進(jìn)行著,您現(xiàn)在論述這些,是要說(shuō)明什么道理呢?”太史公說(shuō):“對(duì),對(duì),您說(shuō)得對(duì),不過(guò),不過(guò),我不是這個(gè)意思。我聽(tīng)先父說(shuō)過(guò):‘伏羲時(shí)極其純樸厚道,創(chuàng)作了《易》的八卦;唐堯、虞舜時(shí)代的昌盛,《尚書(shū)》上也有記載,禮、樂(lè)就是那時(shí)作的;商湯、周武王時(shí)代的興隆,古代的詩(shī)人對(duì)此加以歌頌。《春秋》抑善揚(yáng)惡,推崇三代的功德,頌揚(yáng)周王朝,并非全是抨擊和諷刺。’
【原文】
漢興以來(lái),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37],易服色[38],受命于穆清[39],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40],請(qǐng)來(lái)獻(xiàn)見(jiàn)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guó)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guò)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41]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注釋】
[37]改正朔:指使用新歷法。
[38]易服色:改變車(chē)馬、祭牲的顏色。
[39]穆清:肅穆清和,指天。
[40]款塞:叩開(kāi)邊塞的門(mén)。塞,同“叩”。
[41]墮:丟棄。
【譯文】
漢朝建立以來(lái),直至當(dāng)今的圣明之君,得到了上天的祥瑞,舉行封禪,使用了新歷法,改變了車(chē)馬、祭牲的顏色,受命于上天,恩澤遍及遠(yuǎn)方,海外風(fēng)俗不同的國(guó)家,輾轉(zhuǎn)幾重翻譯到中國(guó)邊關(guān)來(lái),請(qǐng)求前來(lái)進(jìn)獻(xiàn)物品、拜見(jiàn)天子的多得數(shù)不勝數(shù)。文武百官極力頌揚(yáng)圣上的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重用,這是國(guó)君的恥辱;皇上英明而其德政沒(méi)被廣為流傳,這是官吏的過(guò)錯(cuò)。何況我曾擔(dān)任過(guò)太史令,廢棄皇上英明的德政不去記載,埋沒(méi)功臣、諸侯、賢大夫的功績(jī)而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囑托,這個(gè)罪過(guò)就太大了。我所說(shuō)的記述過(guò)去的事,只是整理一下他們的世系傳記,并不是所謂的創(chuàng)作,而您將它與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論,這就錯(cuò)了。”
【原文】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42]。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shī)》、《書(shū)》隱約者[43],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guó)語(yǔ)》;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shuō)難》、《孤憤》;《詩(shī)》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lái)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lái),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注釋】
[42]縲紲:捆綁犯人的繩索,這里借指監(jiān)獄。
[43]隱約:意旨隱晦,文辭簡(jiǎn)約。
【譯文】
于是,我將有關(guān)資料加以編排,整理成文。寫(xiě)了七年之后,太史公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囚禁在監(jiān)獄中。于是喟然長(zhǎng)嘆:“這是我的罪過(guò)啊!這是我的罪過(guò)啊!身體已經(jīng)殘廢,沒(méi)有什么用了。”事后又進(jìn)一步深思道:“《詩(shī)》和《書(shū)》,意旨隱晦,文辭簡(jiǎn)約,這都是作者想要表達(dá)他們內(nèi)心的思想。從西伯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被困于陳國(guó)和蔡國(guó)后,寫(xiě)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創(chuàng)作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后來(lái)才撰寫(xiě)了《國(guó)語(yǔ)》;孫臏遭受了臏刑后,論述了兵法;呂不韋被貶蜀地,世上才能夠流傳他的《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guó),因而寫(xiě)出了《說(shuō)難》、《孤憤》。《詩(shī)》三百余篇,大多都是圣賢之人為了抒發(fā)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chuàng)作的,這些人都是心中懷有憂愁郁結(jié)之情,不能得到發(fā)泄,所以追述往事,寄希望于后人。”這樣我終于編寫(xiě)出從唐堯以來(lái)的歷史,止于獵獲白麟的那一年,而從黃帝開(kāi)始。
【評(píng)析】
文章以對(duì)話形式展開(kāi),主要寫(xiě)了作者與壺遂之間的對(duì)答。在對(duì)答中,我們知道作者編撰《史記》有兩個(gè)目的:一是為了完成父親臨死前命他繼續(xù)寫(xiě)史書(shū)的遺囑,極力贊頌了《春秋》的巨大社會(huì)作用和思想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從側(cè)面闡述了自己寫(xiě)作《史記》的宗旨。二是抒發(fā)自己心中所積郁的種種不快。說(shuō)明自己在寫(xiě)作過(guò)程中,遭受宮刑奇恥大辱之后,曾一度灰心,但最終決心忍辱負(fù)重,發(fā)奮寫(xiě)作,實(shí)現(xiàn)自己終生的誓愿,終于寫(xiě)作了《史記》這部巨著。
本文氣勢(shì)軒昂,以說(shuō)理為主,以另一種方式向人們傳達(dá)了一種精神: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事,世界上沒(méi)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文中列舉了眾多學(xué)者,他們歷經(jīng)艱辛,最終取得了成功。文章寓意深刻,值得我們細(xì)細(xì)研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