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流芳《游虎丘小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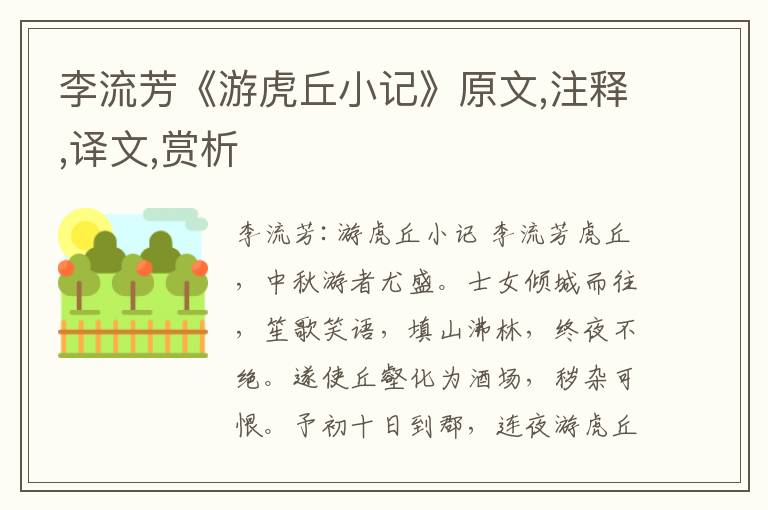
李流芳:游虎丘小記
李流芳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
予初十日到郡,連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
又今年春中,與無際舍侄偕訪仲和于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
生平過虎丘才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游。”真知言哉!
這則小記僅有二百余字,記敘了兩次游覽蘇州虎丘的情景,容量較大,而文字極簡,行文容與疏淡,毫無散漫局促之感。全篇都貫穿著一個“靜”之。
作者兩游虎丘,一次是在秋天,中秋前夕,也是作記之時。此次“連夜游虎丘”,記中僅提到兩夜。一夜,“月色甚美,游人尚稀”,有“紅粉笙歌”點綴于“風亭月榭”之間,對今夕之游作者感到“亦復不惡”。“尚”字,“亦復”,極有分寸,說明此游尚可,但還有缺憾。因為畢竟還有其他一些游客,加之笙歌聒耳,已覺不靜。又一夜,天黑無月,無游客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寫景簡淡之極,但意境深遠。耳聞近處檐間鈴鐸在風中搖振的叮叮當當的聲音,目見遠方林中佛寺忽隱忽現的燈光,唯夜深人靜,始能獲覽其境。在記兩夜游覽虎丘的中間,插入“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的議論,以作過渡。這“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八字,非等閑之語,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自然審美觀。如果把全篇比作一盞燈籠,疏落簡淡的景物描寫好比燈籠周圍所繪的花紋圖案,那么這八字就好像燈籠中心的燭光了,通篇文字都映射出它的光輝。
第二次游虎丘,是往日之事,時在春日。是夜,有月,無人,唯有作者與其侄盤膝石上,如僧人默然“趺坐”,“不復飲酒,亦不復談”。此時作者已經忘懷一切,精神完全專注、溶化在自然景色之中,達到物我兩忘,悠然“與清景俱往”的境界,進入審美意境的最佳狀態。此節豐富了文章的內容,深化了文章的主題,寫的是往事,卻不可缺少。
小記結尾部分,總括兩度游覽虎丘,見到了虎丘“本色”,并引友人詩句,說明欲見自然美“本色”,須在“歲寒”或“夜半”,仍然歸到一個“靜”字。
晚明文人觀賞自然美,特重“本色”,或曰“性情”,也就是自然山川的真面目。自然山川在什么情況下才暴露其真面?觀賞者怎樣才能領略到自然山川的“性情”?對于前一個問題的看法,作者取山空、人靜、歲寒、夜半,質言之,環境必須清靜。對于后一個問題的看法,作者取“靜意”,觀賞者的情緒心境必須安靜。總之,審美客體與審美主體都要“靜”,唯靜才能窺見自然美的本色,領略自然美的性情。反之,環境嘈雜喧鬧,心神煩躁不定,都會破壞美感,不能真正領略山川自然之美。他在《江南臥游冊題詞·虎丘》一文中說:“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于游人雜沓之時”,又指出一般游者愛好趕熱鬧,“附羶逐臭”,“非知登覽之趣者也”。在本文第一節,作者對虎丘中秋之夜,士女雜沓,“笙歌笑語”,“填山沸林”,致令“丘壑化為酒場”的景象,覺得“穢雜可恨”。這從反面托出靜之于美是十分要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