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翱《登西臺慟哭記》抒情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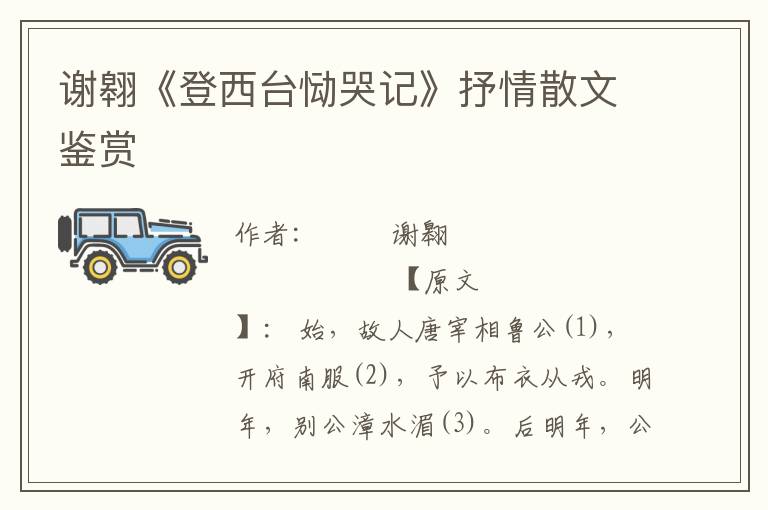
作者: 謝翱
【原文】: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1),開府南服(2),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3)。后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4),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5)。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予恨死無以籍手見公(6),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云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7),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臺(8)。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9)。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10),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11)。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12),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13)。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14),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15),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云從西南來,渰浥浡郁,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16)。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17)?”歌闋(18),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嗜。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19),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后,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后濟。即濟,疑有神陰相(20),以著茲游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21),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游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
予嘗欲仿太史公(22),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后之人必有知予者。于此宜得書(23),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后。時,先君登臺后二十六年也(24)。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作者簡介】:
謝翱(1249——1295),字皋羽,自號晞發子,原籍長溪(今福建省霞浦縣),后遷居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試進士不中,落魄閑居于漳、泉二州(今福建省漳州市及泉州市),倜儻有大節。元軍南下時,他曾參文天祥戎幕,任諮議參軍。宋亡不仕,漫游兩浙山水而逝。所作詩沉郁悲憤,為南宋一家。文章風格接近柳宗元,長于記敘,有《晞發集》。
【鑒賞】:
西臺,在浙江省桐廬縣西富春山,與東臺相峙,相傳為漢隱士嚴光釣魚處,亦稱釣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謝翱為悼念故丞相文天祥殉國而作《登西臺慟哭記》。張丁《登西臺慟哭記注》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當時為了避免元朝統治者的文網,故文章詞多隱晦。
文章開頭,就以“故人唐宰相魯公”來隱指文天祥,并寫“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以唐代張巡與顏杲卿抗擊胡軍(安史叛軍當時主要是胡人)的舊事來隱指文天祥抗擊元軍的事跡,“悲歌慷慨”四字寫得既沉抑哀痛又慷慨飛揚,仿佛又回到往昔抗擊元軍的日子里,表現出一種熱血澎湃的激情。
“予恨……”一段寫對文天祥深切的悼念之情:“每一動念,即于夢中尋之”寫得哀郁凄涼,于是昔時曾經的一草一木都仿佛成了追憶的故事,觸景生情,卻又“徘徊顧盼,悲不敢泣”,高壓的殘酷更顯出這種思念的真切與沉痛。此后姑蘇一哭,越臺一哭,至今西臺又一哭,一路寫來,如一路哭來,哀悼懷念的心情顯得十分沉郁而強烈。
隨后一段寫雨中登岸謁拜,寫祠旁僧舍是“毀垣枯甃,如入墟墓”,仿佛無意中的描寫極寫出元軍南下對南方經濟與人民生活的殘酷破壞,從另一個角度極力地歌頌著文天祥抗元的功勛。“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一片破敗荒涼的環境中,祭拜文天祥,情景相融,顯出一種沉重荒涼的情緒。隨后寫到“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一種國家淪亡,復興無望,人物俱去,雄心盡滅的失望和悲涼強烈地籠罩著文章的氣氛,作者的情緒落到了最低點。于是有云從西南來“若相助以悲者”。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最后是“竹石俱碎”。真是風云為之變色,山水為之含悲。痛慟之后,感情漸趨于平靜,而“適有邏舟之過”的驚險既表現出當時元代統治者的殘酷高壓政策,又反映出作者對“先朝”的忠誠和對元統治者的蔑視。寫到“薄暮,雪作風凜”,將那種凄涼迷惘的情緒渲染得濃郁深沉。最后寫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正是痛慟之后的微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