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送孟東野序》文章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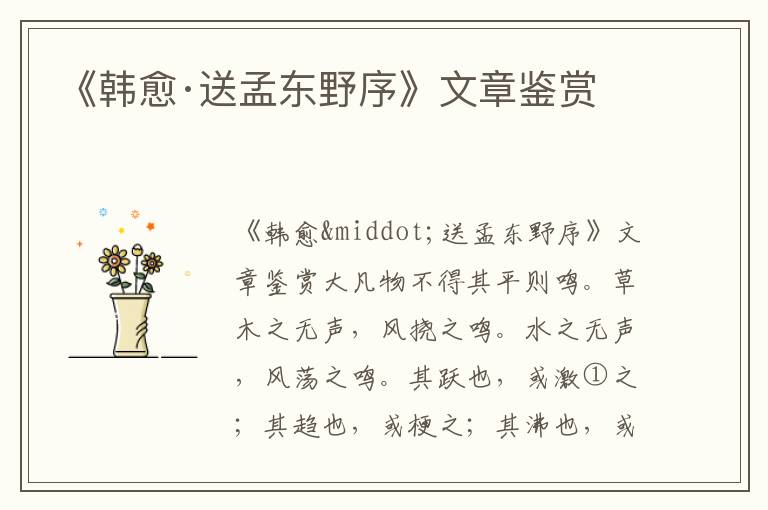
《韓愈·送孟東野序》文章鑒賞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wú)聲,風(fēng)撓之鳴。水之無(wú)聲,風(fēng)蕩之鳴。其躍也,或激①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②之。金石之無(wú)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lè)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③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④,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shí)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fēng)鳴冬。四時(shí)之相推敚⑤,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⑥,咎陶、禹⑦,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⑧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⑨以鳴。夏之時(shí),五子⑩以其歌鳴。伊尹鳴殷{11},周公鳴周{12}。凡載于《詩(shī)》《書》六藝{13},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14},其聲大而遠(yuǎn)。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15}。”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guó)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16}、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17}、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shù)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shí),司馬遷、相如、揚(yáng)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jié)數(shù)以急{18},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19};其為言也,亂雜而無(wú)章。將天丑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20}、蘇源明、元結(jié)、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shī)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21}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22}。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guó)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于江南{23}也,有若不釋然{24}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
【注】
①激:搏擊,阻遏水勢(shì)。后世也用以稱石堰之類的擋水建筑物為激。②炙(zhì質(zhì)):烤,用火指燒煮。③假:借助。④金、石、絲、竹、匏(páo袍)、土、革、木:我國(guó)古代用這八種質(zhì)料制成的各類樂(lè)器的總稱,也稱“八音”。⑤推敚(duó奪):推移。敚,同“奪”。⑥唐、虞:堯帝國(guó)號(hào)為唐,舜帝國(guó)號(hào)為虞。⑦咎陶(gāoyáo高姚):也作咎繇、皋陶。傳說(shuō)為舜帝之臣,主管刑獄之事。⑧夔(kuí奎):人名,傳說(shuō)是舜時(shí)的樂(lè)官。⑨《韶》:樂(lè)曲名,舜時(shí)所作。⑩五子:夏王太康的五個(gè)弟弟。{11}伊尹鳴殷:伊尹,名摯,他是殷湯的賢相,曾助湯伐桀滅夏,湯死后又輔佐其孫太甲。{12}周公鳴周:指周公作《大誥》《康浩》等文章。{13}六藝:漢以后對(duì)六種儒家經(jīng)典的統(tǒng)稱。{14}孔子:字仲尼,春秋時(shí)魯國(guó)人,儒家學(xué)說(shuō)的主要代表。{15}木鐸:古代發(fā)布政策教令時(shí),先搖木鐸以引起人們注意。后遂以木鐸比喻宣揚(yáng)教化的人。{16}臧孫辰:春秋時(shí)魯國(guó)大夫臧文仲。{17}楊朱:字子居,戰(zhàn)國(guó)時(shí)魏人。{18}節(jié)數(shù)(shuò碩):節(jié)奏短促。{19}弛以肆:弛,松弛,引申為頹廢。肆,放蕩。{20}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初唐著名詩(shī)人。浸淫:逐漸滲透。此處有接近意。{22}李翱:字習(xí)之,隴西成紀(jì)人,是韓愈的學(xué)生和侄女婿。張籍:字文昌,吳郡人。{23}役于江南:指赴溧陽(yáng)就任縣尉。唐代溧陽(yáng)縣屬江南道。{24}若不釋然:郁郁不樂(lè),心中好像不開心。
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中唐著名詩(shī)人。他壯年屢試不第,46歲才中進(jìn)士,50歲時(shí)被授為溧陽(yáng)縣尉。他懷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際,韓愈寫此文加以贊揚(yáng)和寬慰,流露出對(duì)朝廷用人不當(dāng)?shù)母锌筒粷M,這一年是貞元十九年(803),韓愈時(shí)年35歲。
文章運(yùn)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韓愈認(rèn)為是人愈“不得其平”,則文學(xué)愈善。韓愈所說(shuō)“不平”的含義,主要傾向于指不平遭遇,不幸的命運(yùn)而引起內(nèi)心的不平衡。這篇序文是專為一生困厄潦倒、懷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鳴”推許孟郊,其重視為窮愁哀怨者“鳴其不幸”的傾向不言自明。
韓愈堪稱語(yǔ)言大師,其文句式和文辭多變,可以說(shuō)達(dá)到了極致。全篇句式靈活,變化無(wú)端,特別是歷數(shù)各個(gè)朝代善鳴者時(shí),句式極錯(cuò)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píng)為“雄奇創(chuàng)辟,橫絕古今”。歷數(shù)各代善鳴者,句句不同。如“其善鳴者也”“假于《韶》以鳴”“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皆鳴之善者也”“孔子之徒鳴之”“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以屈原鳴”“以道鳴者也”“皆以其術(shù)鳴”“李斯鳴之”“其最善鳴者也”“鳴者不及于古”,共14句涉及善鳴者,出現(xiàn)13個(gè)不同句式。而“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wú)聲,或擊之鳴”和“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fēng)鳴冬”這些句子又疏密相間,文氣流暢,搖曳多姿。
此文打破常規(guī)構(gòu)思,用很大篇幅闡釋“不平則鳴”的道理,僅有最后少量筆墨言及孟郊,其他內(nèi)容都憑空結(jié)撰,乍看好像都在說(shuō)題外話,其實(shí)不然,細(xì)品之,無(wú)一言不是為孟郊而設(shè),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顯得空疏游離,體現(xiàn)了布局謀篇上的獨(dú)到造詣。
后人評(píng)論
吳楚材、吳調(diào)侯《古文觀止》:“只是從一鳴之中,發(fā)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于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