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燕《兒時食味》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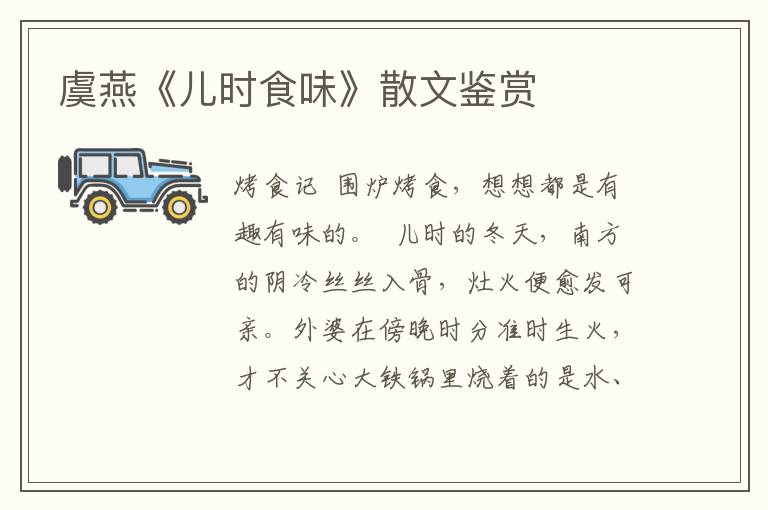
烤食記
圍爐烤食,想想都是有趣有味的。
兒時的冬天,南方的陰冷絲絲入骨,灶火便愈發(fā)可親。外婆在傍晚時分準(zhǔn)時生火,才不關(guān)心大鐵鍋里燒著的是水、飯,還是豬草,我的兩只眼睛獨(dú)獨(dú)盯著灶膛,柴火噼里啪啦唱起歌,火光嗤嗤呼呼伴舞,跳得熱烈,舞得歡騰。我的心亦熱烈而歡騰。
煙囪冒出的炊煙似暗號,鄰家小芬、阿波等齊刷刷來了。或帶些許年糕、土豆、番薯,或什么都不帶直奔而來。食物多,便給它們排隊,嘰嘰嘎嘎討論先烤哪一個,直到口干肚叫;食物少,也不為難,年糕掰塊,紅薯切厚片,分食,一樣心滿意足。
灶膛前擠滿了小腦袋,邊取暖邊等待,小臉紅亮,瞳仁放光,似要見證奇跡的發(fā)生。大鐵鍋咕嘟聲漸響,白氣氤氳如霧,每個人的五官都柔和起來,寒意早被逼到了廚房外。外婆揭鍋查看,被白色霧氣罩住,似被蒙描紙蓋住的人像畫。幾雙眼睛巴巴粘在外婆身上,等著她一聲令下:不用添柴了。
灶火弱下去,直至顯現(xiàn)一大團(tuán)冒著火星的柴火堆,用火棍撥一下,嗤嗤響。紅薯、土豆、芋艿選個頭小的,否則難烤熟;年糕、面包、高粱餅需用報紙包上,不然全成黑包公,無法下嘴。扒開柴火堆,把食物一一埋入。埋下的不是食物,是一絲充滿誘惑的希望。
等吃的過程是一種幸福的煎熬,個個伸長脖子,恨不得將腦袋鉆進(jìn)灶膛里去盯著。空氣里,草木灰的氣味逐漸被誘人的焦香替代,再也按捺不住,幾個人貓著腰輪流探進(jìn)灶膛查看,口水在心里頭瘋漲,要從嘴里漫出來。外婆和阿姨在邊上笑:哎呦,看看你們,還早著呢!
也有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扒出來一個,邊拍灰邊呼呼吹氣,亟不可待地咬一口,燙得閉眼歪嘴,縱是半生不熟也被消滅得點(diǎn)滴不剩。
烤熟透的紅薯、土豆等外皮通常焦黑似炭,剛從柴火堆扒出來時太燙手,阿姨玩起了雜耍,將它們在兩手間來回拋,這一動作引得眾小孩爭相模仿,樂不可支。失手也無礙,吧嗒掉地上,或完好無損,或皮開肉綻,撿起來吃得更歡。那會兒,爐灶旁的笑聲怕早已穿過煙囪飛上云天了。
紅薯甜香綿軟、芋艿粉糯滑溜、土豆噴香嫩軟,急吼吼剝皮,咬幾口,胃里熱乎乎,臉上熱乎乎,頃刻,全身也像烤過似的,暖融融。年糕和高粱餅雖有報紙包著,依然會沾上柴灰,外婆除去報紙,輕輕吹掉黑灰,切塊,給每一塊插上一根筷子。像舉冰棍那樣,我們舉著年糕和高粱餅,啃下去,滿嘴米面香,香味由齒頰漾入脾胃。外婆問好不好吃,我回答得響亮:好吃,跟做神仙一樣。
奶奶好喝幾口,下酒菜最喜燒烤海鮮。
暮色四合,奶奶把小炭爐搬至門口,用干草、干樹葉生起爐子,待明火逐漸減小,便拎爐子回屋。她右肩略往下傾斜,隨著搖晃的步履,發(fā)髻邊的那朵玉蘭花也跟著一顫一顫,我總擔(dān)心它會掉下來。
爐子架上金屬網(wǎng)子。爺爺已在屋子洗凈帶魚、馬鮫魚、蝦子等,帶魚和馬鮫魚切成段,在醬油里浸泡一下。我和弟弟幫不上忙,進(jìn)進(jìn)出出地瞧熱鬧。不一會兒,魚蝦們在網(wǎng)子上“嗞嗞”冒煙,海味特有的鮮香挾裹著煙熏火燎的氣息充滿了整個屋子,我們瞬間安靜,像被粘在了小炭爐上,挪不動步子。
為防止焦掉,要頻繁地翻面,奶奶將這個任務(wù)交給了我。我翻了這塊翻那只,翻著翻著就翻進(jìn)了自己嘴里,呼哧呼哧,燙得舌頭要起泡。怕一旁的弟弟“告發(fā)”,也夾起一小塊堵住他的嘴。兩人偷著樂,好似占了大便宜。
爺爺說,船上的海風(fēng)與日頭特別猛,曬成的烏賊鲞噴噴香。父親便在船上剖曬烏賊,上岸后帶回來,不多,每回一兩串的樣子。
烤烏賊鲞時,網(wǎng)子邊上順便烤一些小魚和土豆片。父親坐在爐子旁慢慢地烤,跟爺爺奶奶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烏賊鲞不易熟,肉質(zhì)韌而緊,烤它得有足夠的耐心。鲞在網(wǎng)子上翻來覆去,我想著自己的小煩惱。花裙子怎么還沒做好?生我氣的小芬明天還會找我玩嗎?
小圓桌就在爐子旁,奶奶已擺上了幾樣小菜,父親給奶奶和自己倒上一盅黃酒,邊喝邊烤邊聊。不沾酒的爺爺幫著翻動烏賊鲞,不時瞅瞅我跟弟弟,呵呵地笑。我托著腮默數(shù)他額頭上的皺紋,小溪似的皺紋……
父親把烤好的兩只烏賊鲞先給爺爺奶奶,酡紅的臉轉(zhuǎn)向我跟弟弟:不要急,馬上有你們的了。待我們的碗里各有了一只,急急去掉烏賊骨,撕下一條大快朵頤。咸香中透著鮮甜,鮮甜里又夾雜了煙火味,越嚼越香,欲罷不能。爺爺奶奶總怕我們不夠吃,他們的兩只烏賊鲞都只撕了一小塊,最后,又端到我們面前。
吃著看著,大家的笑臉在熱騰騰的煙火氣里一會兒朦朧一會兒清晰,我全身暖洋洋懶洋洋,不知何時便在奶奶懷里睡著了……
番薯片
做番薯片會在每年秋季番薯豐收之后,選一個晴好無風(fēng)的日子,召集親戚或鄰居共同完成。
每次做番薯片都像過節(jié),忙碌、熱鬧,其樂融融。一大清早,河埠頭傳來女人們的語笑喧嘩,一個個沾滿了泥的番薯在家長里短中被洗得清清爽爽。“素顏”番薯們躺在籮筐里,被扛進(jìn)院子里,削皮、切塊,從每家小人床下來的搗蛋鬼們一哄而上,惺忪著眼睛偷吃生番薯。大人們打掉我們伸出去的小手:少吃生番薯,當(dāng)心長蛔蟲!
風(fēng)箱的“呼呼”聲和著大鐵鍋的“咕嘟”聲響起,縷縷炊煙輕快地飄向湛藍(lán)的天空,似在以藍(lán)天為宣紙潑一幅水墨畫。我們在番薯的甜香里引頸以待,從屋子到院子,又從院子到屋子,奔進(jìn)奔出不知道多少遍后,熱騰騰香噴噴的番薯終于出鍋。
兩三張桌子早已擺放于院子中央,冒著熱氣的番薯被裝進(jìn)木盆端上桌、搗成泥。有時會加些黑芝麻或切得細(xì)細(xì)碎碎的桔子皮,做成的番薯片就有了芝麻味和桔皮味。什么都不加的就是原味番薯片。幾張桌子上齊發(fā)出搗番薯的“咚咚”“當(dāng)當(dāng)”聲,我們幾個難免心癢手癢,總要搶過大人們手里的鏟子或搟面杖可勁地?fù)v幾下。
我學(xué)著大人的樣兒將浸濕的干凈棉布鋪在餅干箱底部,取用若干糊狀番薯倒在棉布上,用鏟子像攤餅子那樣沿著餅干箱底的形狀攤勻,攤成薄薄的圓形或方形(由餅干箱底的形狀而定),最后輕輕拈起棉布將番薯片倒扣在團(tuán)箕上。每張桌子旁,都有手忙腳亂的小孩和從容不迫的大人,就算孩子做得再不像樣,大人也只是哈哈一笑,不會責(zé)備。
院子成了番薯片的天下,地面上、晾衣繩上、圍墻上到處可見晾曬著番薯片的竹簟和團(tuán)箕,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紅薯香。秋日的陽光忽閃著金光灑在偌大的院子里,院子里的一切都被鍍上了暖色,連大人們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都透著暖洋洋的味道。兩三個小時后,要給番薯片翻面,我們殷勤地跟在大人后邊,表示要幫忙,大人們當(dāng)然心知肚明,在我們歡暢地偷吃番薯片時,她們?nèi)瘫犞谎坶]只眼。這個時候的番薯片韌而不硬,清甜中雜糅了陽光和煙火的味道,可跟烏棗媲美。味蕾的記憶多么強(qiáng)大,幾十年后想起都還能砸吧嘴。
曬干的番薯片能儲藏很久,是兒時的長期零食。平時吃的基本都是直接曬干未經(jīng)任何加工的番薯片,稱作“生番薯片”,原汁原味,有嚼勁。而油炸番薯片在當(dāng)年則屬于奢侈吃法了,基本上只在大日子里出現(xiàn),如大年廿三祭灶日。把番薯片扔進(jìn)冒著熱泡的油鍋里,等炸得金黃酥脆,撈起,嚼在嘴里“咔嘣咔嘣”,又香又酥。算是當(dāng)年祭灶果里的主角之一。將沙子倒入鍋內(nèi)炒熱,再把剪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番薯片下鍋翻炒,韌勁如牛筋的番薯片開始慢慢伸展、變脆,濾去沙子后就是一盤炒番薯片。通常,母親剛端出滿滿一盤,頃刻就被一搶而空。
好幾回夢見,屋檐下,用鉛絲或棉線串成串的番薯片,層層疊疊擠擠挨挨,風(fēng)吹過,夢里都是帶著陽光味的番薯香。
白米粽
“玉粒量米水次淘,裹將箬葉苧絲韜。炊馀脹滿崚嶒角,剝出凝成細(xì)纖膏。”謝墉的這首《粽子》寫得生動形象,將粽子的特點(diǎn)描繪得淋漓盡致——吃粽子是享受美味,裹粽子是享受樂趣。
那時的粽子都是自己裹的。端午節(jié)前夕,深夜里忙碌的身影漸漸地多了,大街小巷開始彌漫起粽葉的清香。外婆和母親都是裹粽子的好手。選粒形短圓、清亮透明的糯米淘洗干凈后放進(jìn)大木盆,用清水浸泡一夜。干的筍殼葉和箬葉也要事先浸泡,使它們變得軟韌,而后一片一片清洗、攤平,用細(xì)麻線扎起,煮個幾分鐘撈出待用。浸泡好的糯米濾去多余的水份,加入適量的堿面,用筷子拌勻,原本白色的米粒就會變成淺黃色。
裹粽子時,邊上備一把剪刀,以便隨時對粽葉進(jìn)行修剪。隨手抽出一片筍殼或箬葉,一疊一卷變成一個圓錐形的筒,用勺子舀起適量糯米填進(jìn)去,晃一晃,使其平整,無需刻意用筷子搗實(shí)壓緊,要給米粒預(yù)留一些膨脹的空間。用拇指將一側(cè)的粽葉折過來壓在米粒上,另一側(cè)的粽葉也折過來用拇指壓住,最后折起粽葉尾部,用粽葉上撕下的長條或棉線綁緊。整套動作干脆利落一氣呵成,有棱有角的三棱粽子就算完成了。
豹紋筍殼粽時尚,綠色箬葉粽清新,下到大鍋后,加水浸沒粽子,最好“咕嘟咕嘟”一氣煮成。米的糯香挾裹著淡淡的堿面清香云霧般在屋子里、鼻子底下打轉(zhuǎn),勾引得人坐立難安。終于等到揭鍋,就像一瓶奇異的香水被打破了,有春芽破土的清新,有米粒軟糯的香甜,禁不住咽口水。滾燙的粽子入盤、上桌,在誘人的香氣折磨中等其稍涼,然后,“寬衣解帶”,露出“香里晶瑩玉一團(tuán)”。糯米與粽葉如切斷的藕,絲絲相連,一粒粒飽滿的糯米緊緊地挨在一起,晶瑩剔透的粽身上仿佛涂了一層薄薄的香油。從糖罐中舀出一湯匙白砂糖,下雪般撒于粽子上,急不可待地咬上一口,堿水特有的香味在齒間留連,混合了粽葉清香的糯米在口中慢慢溶化,偶爾還會咀嚼到未完全化開的白砂糖,發(fā)出“咯吱咯吱”聲,黏而不糊,清甜爽口。
“冰團(tuán)水浸砂糖里,透明解黍菘兒和”。將一顆顆粽子放入一盆冷水里至涼透再吃,口感更佳。外婆家的井水透涼,用來浸泡粽子再好不過,像在冰箱里冰鎮(zhèn)過似的。蘸點(diǎn)白糖,插上一根筷子,像吃冰棍那樣來吃一個粽子,也是非常有趣的。還可以切成薄片,放在盤子里,淋上蜂蜜或桂花醬等,看上去色澤瑩潤,吃起來甜香勁道,涼絲絲甜滋滋,咽下幾口后,渾身舒爽清涼。這個特別適合炎夏食用,清熱解暑,別有風(fēng)味。不過,味道雖好,也不能貪嘴哦,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
如今,鮮能尋見堿水白米粽的身影,但記憶與味蕾會提醒我:想吃。想吃,便慫恿母親:“我們裹粽子吃吧,就那個堿水白米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