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答謝民師推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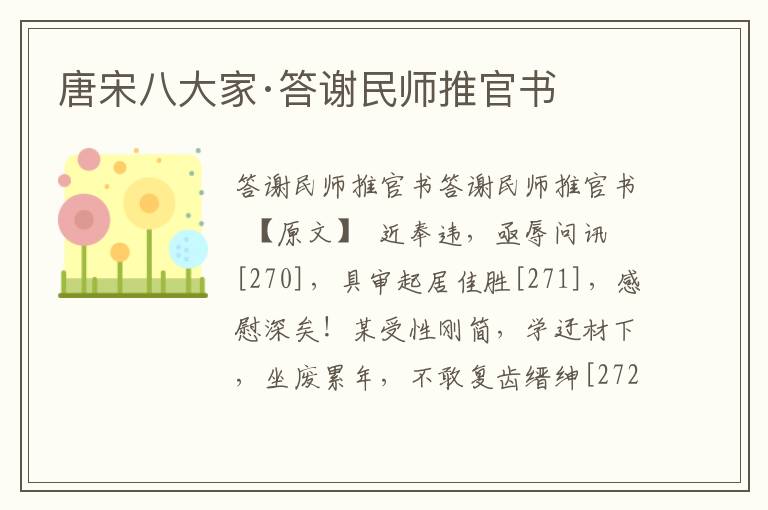
答謝民師推官書
答謝民師推官書
【原文】
近奉違,亟辱問(wèn)訊[270],具審起居佳勝[271],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jiǎn),學(xué)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fù)齒縉紳[272]。自還海北,見(jiàn)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wú)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shù)賜見(jiàn)臨[273],傾蓋如故,幸甚過(guò)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shī)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wú)定質(zhì)[274],但常行于所當(dāng)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yuǎn)。”又曰:“辭,達(dá)而已矣。”夫言止于達(dá)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fēng)捕影[275],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wàn)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dá)[276]。辭至于能達(dá),則文不可勝用矣。
揚(yáng)雄[277]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shuō),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chóng)篆刻[278]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dú)悔于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dú)變其音節(jié),便謂之經(jīng),可乎?屈原作《離騷經(jīng)》,蓋風(fēng)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tīng)?zhēng)光[279]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chóng)乎?使賈誼見(jiàn)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賦鄙之[280],至與司馬相如同科[281]。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歐陽(yáng)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jià),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于左右,愧悚[282]不已。
所須惠力法雨堂兩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qiáng)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283]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guò)臨江,當(dāng)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dāng)為作數(shù)句留院中,慰[284]左右念親之意。今日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yuǎn),惟萬(wàn)萬(wàn)以時(shí)自愛(ài)[285]。
【注釋】
[270]亟辱問(wèn)訊:亟(qì):屢次。屢次承蒙問(wèn)詢。
[271]佳勝:舊時(shí)書札問(wèn)候、祝頌用語(yǔ)。猶言安好、順適。
[272]縉紳:原意是插笏(古代朝會(huì)時(shí)官宦所執(zhí)的手板,有事就寫在上面,以備遺忘)于帶,舊時(shí)官宦的裝束,轉(zhuǎn)用為官宦的代稱。
[273]見(jiàn)臨:猶光臨。
[274]初無(wú)定質(zhì):本來(lái)沒(méi)有固定的形式。
[275]系風(fēng)捕影:拴住風(fēng),捉住影子。比喻無(wú)法辦到的事。也比喻說(shuō)話做事以不可靠的傳聞或表面現(xiàn)象作根據(jù)。
[276]辭達(dá):指文辭或言辭的表述明白暢達(dá)。
[277]揚(yáng)雄:西漢官吏、學(xué)者。少好學(xué),為人口吃,博覽群書,長(zhǎng)于辭賦。
[278]雕蟲(chóng)篆刻:后以“雕蟲(chóng)篆刻”喻詞章小技。
[279]日月?tīng)?zhēng)光:爭(zhēng):競(jìng)爭(zhēng)。與太陽(yáng)、月亮比光輝。常用以稱贊人的精神、功業(yè)偉大。
[280]鄙:輕視。
[281]同科:相提并論。
[282]愧悚:惶恐、慚愧。
[283]局迫:狹窄。
[284]慰:安慰。
[285]自愛(ài):愛(ài)護(hù)自己。
【譯文】
最近分別之后,多次承蒙你來(lái)信問(wèn)詢,詳細(xì)了解了你的日常生活都安好,感到很欣慰。我生性剛直,待人簡(jiǎn)慢,學(xué)識(shí)迂腐,才智低下,因被貶而廢置多年,不敢再與官宦們并列。自從渡海北歸,見(jiàn)到平生的親戚故友,惘然好像不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人,何況與你過(guò)去沒(méi)有一天的交情,怎么敢希求結(jié)交呢?幾次蒙你親自光臨,一見(jiàn)如故,喜出望外,不是言語(yǔ)所能表達(dá)的。
你給我看的公事文件和詩(shī)賦雜文,我都已看過(guò)了。它們大都似行云流水,本來(lái)沒(méi)有固定的形式,而常常起于所當(dāng)起的地方,常常停于所不可不停的地方,文理自然,姿態(tài)富有變化。孔子說(shuō):“語(yǔ)言如果沒(méi)有文采,傳播不會(huì)很遠(yuǎn)。”又說(shuō):“文辭能夠達(dá)意就可以了。”既然說(shuō)能達(dá)意就夠了,就懷疑好像不用講究文采,這是不對(duì)的。探求事物的奧妙,就像追風(fēng)捕影,能夠在心里清楚地了解所寫事物的人,大概千萬(wàn)人中遇不到一個(gè),更何況能夠口說(shuō)和手寫都表達(dá)得清楚明白的人呢?這就是所說(shuō)的文辭或言辭表述明白暢達(dá)。文辭到了能夠達(dá)意,那么文采就不可多用了。
揚(yáng)雄喜歡用艱深的辭句,來(lái)裝飾膚淺簡(jiǎn)單的道理,如果把這樣的道理直接說(shuō)出來(lái),那么大家就都知道他的膚淺了。這正是他所說(shuō)的“雕蟲(chóng)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屬于這一類。可是他只悔恨曾經(jīng)作賦,為什么?他一生雕琢字句只變更了寫賦的音節(jié),便稱之為“經(jīng)”,可以嗎?屈原作《離騷》,是《風(fēng)》《雅》的再次衍變,即使與日月?tīng)?zhēng)光也是可以的;能夠因?yàn)樗褓x而說(shuō)是雕蟲(chóng)嗎?假使能讓賈誼見(jiàn)孔子,(孔子會(huì)評(píng)論賈誼的道德學(xué)問(wèn))登堂入室已經(jīng)夠了。而揚(yáng)雄因?yàn)橘Z誼寫過(guò)賦就輕視他,竟將他與司馬相如相提并論,揚(yáng)雄這類見(jiàn)識(shí)淺陋的事例很多。這只能與那些有知識(shí)的人講,很難和一般人說(shuō)明的。這是談?wù)撐恼屡紶栒劶斑@罷了。
歐陽(yáng)文忠公說(shuō):文章就像精金美玉,在市場(chǎng)上有一定的價(jià)格,不是什么人用嘴巴就能夠定貴賤的。雜亂地說(shuō)了那么多,怎么能有益于你呢,慚愧得很,惶恐得很。
你所要我給惠力寺法雨堂寫幾個(gè)字,我本來(lái)就不善于寫大字,勉強(qiáng)寫也終究寫不好,并且在船上空間狹窄難以書寫,未能按你的囑咐去做。然而我正要經(jīng)過(guò)臨江,一定會(huì)前去游覽,或許僧人要讓我記錄些什么,我會(huì)寫幾句留在院中,來(lái)安慰你的思親之意。今天已到峽山寺,稍稍停留就離開(kāi)了,越來(lái)越遠(yuǎn)了。只希望你千萬(wàn)要時(shí)刻愛(ài)護(hù)自己的身體。
【解析】
《答謝民師推官書》一文寫于元符三年(1100),蘇軾謫居瓊州,遇赦北還,路過(guò)廣州,擔(dān)任廣州推官的謝民師多次攜帶詩(shī)文上門求教,二人在短時(shí)間內(nèi)結(jié)下深厚情誼。蘇軾離開(kāi)廣州之后二人繼續(xù)書信往來(lái),本文是答謝民師的第二封信,從中可以領(lǐng)悟蘇軾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理念的獨(dú)到見(jiàn)解。
蘇軾注意文藝的自然本質(zhì),講求創(chuàng)作的自然天成。他在文中贊揚(yáng)謝民師文章“如行云流水,初無(wú)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dāng)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就是說(shuō)明他主張寫文章要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本質(zhì),起止得當(dāng),文理自然,姿態(tài)富于變化。
此外,蘇軾十分重視文學(xué)的藝術(shù)性,文辭不僅要能準(zhǔn)確表達(dá)意思、思想,而且還應(yīng)該講求文辭的藝術(shù)性、文學(xué)性。在文中他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來(lái)闡述“辭達(dá)”論并進(jìn)一步發(fā)揮。真能達(dá)意的文辭,必須研究描寫對(duì)象的特征,像系風(fēng)捕影一樣,把握稍縱即逝的現(xiàn)象,然后“了然于心”。這就不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現(xiàn)象,而是認(rèn)識(shí)到它們內(nèi)在的本質(zhì)規(guī)律,不僅熟知形態(tài),而且掌握神韻。做到這一點(diǎn)還很不夠,還必須把“了然于心”的事物進(jìn)而“了然于口和手”,這才是達(dá)到了語(yǔ)言藝術(shù)最高造詣。最后,他還表示自己反對(duì)揚(yáng)雄“好為艱深之辭”,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