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散文名篇·峴山亭記》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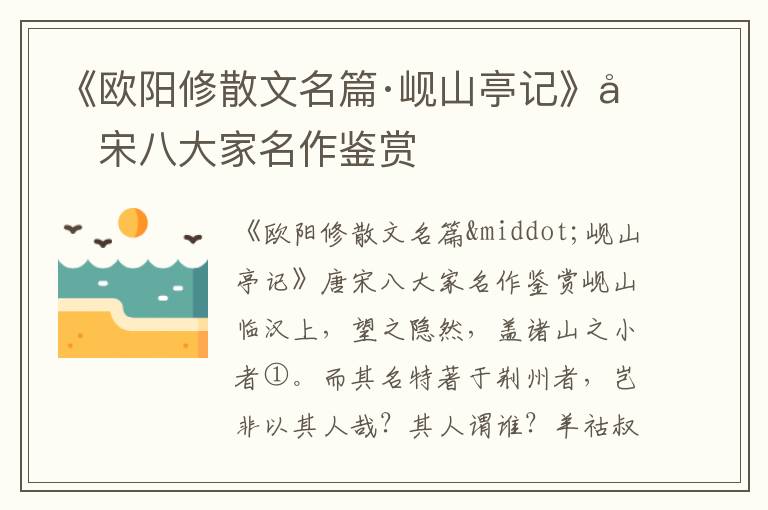
《歐陽修散文名篇·峴山亭記》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①。而其名特著于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于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于當世矣②。至于風流馀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③,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
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④,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于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⑤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后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⑥,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并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余。
余謂君如慕叔子之風⑦,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⑧,與夫草木云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于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⑨。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注】
①漢上:漢水之上。隱然,莊重的樣子。②“方晉”五句:晉武帝司馬炎篡魏后,即有滅吳之志,因荊州是與吳接壤的軍事要地,故任命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準備伐吳。羊枯死時舉杜預自代,杜預于太廢元年(280)平吳。③元凱以其功:杜預領兵伐吳,功勞最大,平吳后封當陽縣侯。④屬:下屬、隨員,指從事鄒潤甫。⑤光祿卿:光祿寺的主管官,掌朝廷祭祀朝會等事。這里指史中輝的官階。⑥所至有聲:所到之處都有官聲,指有善政。⑦慕叔子之風:仰慕羊祜的風流余韻。風,指政治風度。⑧勝勢:指秀麗的風景。⑨“至于亭屢廢興”四句:意思是峴山亭曾多次毀壞重修,以往也會有碑記,但也沒有必要詳細說它的興廢經過了,所以這里都不寫進去。
峴山,在今湖北襄樊市南漢水上。傳說,晉武帝命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駐襄陽,與東吳陸抗對峙,彼此不相侵擾,后入朝陳伐吳之計,舉杜預自代。杜預繼任后,平定東吳。峴山因此二人而知名。
這篇碑記是應襄陽知府史中輝之請而寫的。作者一向反對趨時邀譽,所以文章一方面肯定羊祜、杜預“垂于不朽”的功業,一方面對他們的“汲汲于后世之名”,也發出了“自待者厚”的譏評;特別是對杜預的“紀功于二石”,指出他“不知石有時而磨滅”。因而,文中說到“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并傳于久遠”,是希望史中輝在政事上能有所建樹。
文章從山說起,然后寫到人,最后才寫到亭。至此,才算是切入問題,主要寫了峴山亭的興廢歷史,以及重修和擴建。作者略去峴山的自然風貌,而著重抒發由峴山這一名勝所引起的感想,在碑記文中別具一格。
在寫到作本文的緣由時,作者處理得十分巧妙:“至于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說,史中輝如果真有輝煌的業績的話,將來自然會有本城的百姓為他作記,加以褒揚,因此本文就不加以評述了。如此一來,本文既不為史中輝歌功頌德,也不使得兩位古代名人的功績被磨滅,既表達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又批評了社會上貪慕虛榮的不良作風,委婉曲折,耐人尋味。
后人評論
姚鼐《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四:“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埃者,絕世之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