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洪濤《澡雪記》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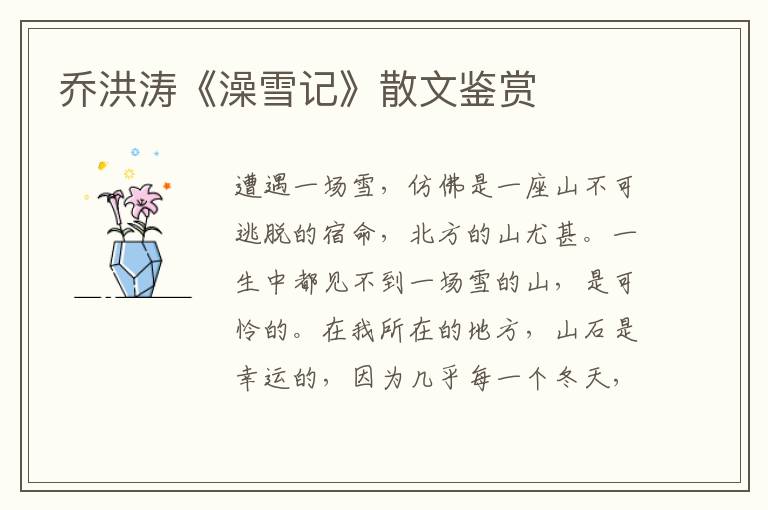
遭遇一場雪,仿佛是一座山不可逃脫的宿命,北方的山尤甚。一生中都見不到一場雪的山,是可憐的。在我所在的地方,山石是幸運的,因為幾乎每一個冬天,都會有雪從天空而來,有時還不是一場,而是兩場,三場,甚至更多。但如果雪足夠大,一場也就夠了——
一場大雪從遙望不可及的天空而來,鋪天蓋地。先是水汽蒸騰,扶搖而上,遮蔽了星辰,遮蔽了日月;繼而陰翳醞釀,光亮隱遁,濃濃的水汽變得灰茫,凝聚成一團一團的云,厚,密,濃,直至濃得再也化不開,就像我們在云層之上俯瞰,腳下全是層層疊疊耀眼的白絮;接著,還要有一場風,凜冽朔風,吹響高山上的林木,直至樹梢間發出呼嘯的聲音,就像是春日夜半窗外沙啞叫春的貓。
氣氛恰當的那一刻,雪終于來了。往往先是微雪,輕飄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讓人誤以為是山林水滴,或者植物吞吐的潮氣,三兩滴落在人裸露的皮膚上,只能感覺到一點點的濕,但那時候的它,還不是雪花,只是水——一滴水開花的過程是多么微妙,礁石撞擊四濺,它就開成一朵浪花;朔風一吹,它就凝固,結晶成雪花,這六瓣的精靈,剔透閃亮,精致對稱,純潔無瑕,足以羞煞所有植物的努力——無根之水,是天賜嗎?雪粒子落下來的時候,先是耳朵聽到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顆粒狀的雪是大雪的前奏,它們身先士卒,穿過高高的林梢,灑向大地,墜落在樹干、樹枝或者未落的樹葉上,有的徑直落地,敲打在山石、地面、落葉上。有節奏的鼓點,密密地響起來,一如山林古寺的鐘聲,唰—唰—唰,嗡—嗡—嗡。最后,大片大片的雪花飄下來,奔向山林,就像命運中的如意吉祥、落寞悲歡,寂靜的山林等待的這一場覆蓋,慷慨而來。往往只是一個夜晚,整座山就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碧翠隱沒,不見顏色;山石遁跡,藏于雪下——白色覆蓋了一切,一切歸于寧靜。
我曾經在落雪的夜晚,親近過一座湖,看到了那湖是如何呼喚一場雪,雪又是如何覆蓋一座湖的。雪落在湖里時,瞬間會融化為水,讓人格外心疼。山腳下十二月的湖水,伴隨著山間遙遠的古寺鐘聲,蕩起微波,像是書寫一篇詩章。而那山間的古寺,一年四季,在每個早晨,都會有鐘聲響起。記得以前寺里面只有一個老和尚,紅漆大門刷得锃亮,閃閃發光的鍍金銅釘明晃晃的耀眼。院內有兩株古柏,直直地頂向天空,樹根遒勁盤錯,一半露出地面,樹干足有合抱之粗,而柏樹下的石碑上,刻著兩首古詩,一首是白居易的,一首是蘇東坡的。
那古寺就在這湖濱的山上,如今大雪紛紛,又一次覆蓋紅墻灰瓦,屋檐的琉璃在雪花中變得愈發光滑,屋角上蹲著的小獸,一只只慈眉善目,溫順得像一座佛。白雪覆蓋下的寺廟,就像歷史冊卷里的一首宋詞,安靜,肅穆,寂寥而又準確。對,準確——一座大山沒有寺廟,總像是沒有了魂魄。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破敗的寺廟,一個小小的和尚,只要有木魚,只要有鐘聲,寂靜的山林就有了深度。何況我所描繪的這座山,正在迎接一場大雪的蒙山,深藏著一座中山古寺。古寺上空,一場從遠方趕來的雪正在落下,屋檐下的鳥雀縮著腦袋看雪,屋內檀香裊裊的繚繞中,一個老和尚正在敲木魚,啪—啪—啪,嗡—嗡—嗡,窗外的雪越下越緊了。
通向寺廟的山路上,我和幾個詩友正在跋涉而行。多年了,我們早已經約好,大雪的當日,我們要去古寺里看一場雪,聽一場經,品一杯茶,誦幾行詩。
古寺里的僧人是我們的朋友,也是一位詩人,但與我們不同。我們的詩作里布滿了酒、肉、欲、幻,繚繞著無法驅趕的煙火氣。僧人的詩卻像這大山的石頭、石頭上的林木,安靜、祥和、澄澈、通達。上山的纜車并沒有停運,坐在纜車上觀雪的游人發出遙遠的歡呼;我們拾級而上,踩著每一級石階,看每一片雪花落在眼前。路上有絡繹不絕下山的游客,只有我們幾個乘雪上山,就像溯游而上的游魚不合時宜——喧囂熱鬧的塵世中,詩人本身不就是與常人方向不同的路人?
中山寺那塊石碑上的兩首詩,是白居易和蘇東坡寫的。白居易寫的是《棲中山寺》,曰:“閑泊池舟靜掩扉,老身慵出客來稀。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殘鶯喚遣歸。揭翁偷嘗新熟酒,開箱試著舊生衣。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陰速似飛。”幾百年后,蘇東坡來山中古寺留宿,作詩《中山寺石刻》:“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余漢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塌香凝帳,夢繞千巖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處涌冰輪。”
迎著一場山雪,奔赴一場雪中的約定,在我,是修行。山路蜿蜒,抬頭只有山石草木,山石草木上正窸窸窣窣落著大雪,看不到盡頭,仿佛人生不可預知的渺茫前路。越往上走,行人越少,也就越安靜,耳邊只是同伴行路喘息的聲音和雪落的聲音。一只灰色的野兔從路上躥過,成為沉默風景里的一個動詞;一只七彩玉翎的山雞也被驚起,從旁邊的峭壁上向山下的茂林飛去,飛行的高度和長度完全出乎了我們的預料——山下的家禽,似乎早已忘了這項本領。
我們頭發全白了,這一次冒雪上山,同行人一路白頭,仿若看到了若干年后我們年老的樣子。但這樣的劈頭蓋臉的雪花,連同山林一起把我們覆蓋,不正是我們渴慕已久的一場雪澡嗎?我們每天在溫室里沐浴我們的肉體,淋浴花灑下,加熱后的水珠流淌過我們的肌肉、我們的毛發、我們的皮膚,我們何嘗遭遇過一場大雪如此醍醐灌頂,進行一場精神的沐浴?
雪越來越大,透過層層密林,可以看到白色的精靈漫天而下。裸露的山石、灌木叢、枯草全變成了白色,樹枝上有松鼠跳躍,發出平時難得一聞的聲音,喜鵲也驚飛了,撲棱棱驟起驟落,藍白相間的顏色,在這山林間顯得格外珍貴。舒展開來的雪花,一片,一片,一片……這是水之花,純白的顏色,勻稱的形態,如此美妙。春夏時節,山林草木葳蕤,每一棵植物的血脈漿管里,都充盈著原生態的水——蓼草開出星米一般乳白色的花,花蕊中水珠欲滴;野杜鵑在潮濕處瘋長,水又成為“啼血”的紅色隱藏于白色的花瓣中;山腰中成片的芭茅草和矮蘆葦,像竹子一樣中空而挺拔,把耳朵貼上去,仿佛就可以聽見地下的水脈嘩嘩地向上流淌。如今,山林之中,盤旋的山路上,我們冒雪而行,水以一種嶄新的形態,鋪天而來,把一切顏色淹沒、把一切聲音淹沒、把一切蹤跡淹沒,所有的生命都被它覆蓋,這多邊形的小天使,從密林中、湖泊中,以水蒸汽的形式升上去,以雪花的形式又降下來,回到自己的初心上來,給天地一場沐浴。我們趕赴這一場雪花之約,享受這澡雪的施禮,難道不是一種冥冥中的昭示?
一場大雪,完全可以改變一座山林。從雪花落下的那一刻,樹木、野草、山花,林林總總的植物們,以及搖頭擺尾的蟲子、振翅飛翔的鳥雀和各種喧囂的小獸們,瞬間就會安靜下來,與山林一起,接受洗禮。生命中常有這樣的時刻,在奔跑的命途中,在漫長的跋涉里,因為外在的一事、一景,忽然撥動我們的心弦,澎湃的感情會海嘯般升起,并迅速把我們淹沒,讓我們不得不停下腳步,慢慢呼吸,慢慢感受,直到那珍藏的淚水緩緩流出,洗滌滿臉的塵埃,身心隨之放空,精神也重新明亮起來。
中山古寺現在的和尚,本來是山下的朋友。當年在煙火的“江湖”中吃肉喝酒,退休后卻突然厭倦了塵世,到山中修行。他剃發的那天,我們喝了最后一場酒,送他上山,自此之后,他幾乎沒有下過山。寺廟里的老和尚坐化之后,就剩下他一個人,他穿上袈裟,拿起木魚,敲響了晨鐘暮鼓。我們偶爾上山看他,他竟然安靜得像一株野草,我們漸漸看到他眸子里的清澈、安詳。每年的下雪天,我們幾個都會上山赴約,喝一杯茶,讀幾首詩,或者就靜靜地聽山中落雪,享受這深山饋贈,身心也便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古人士子多有精神潔癖,在熙熙攘攘的塵世間久了,難免身心沾染銅臭惡俗,他們眼里揉不進一粒沙子,為保持高潔的精神情操,他們經常拿自己的肉體開刀——要么自我放逐,要么絕食反省。宋·陸游《雨后極涼》詩中曰:“孰能痛澡雪,此道庶少進。”魯迅在《墳·摩羅詩力說》中寫到:“其神思之澡雪,既至異於常人,則曠觀天然,自感神閟,凡萬匯之當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他們對自己要求極為苛刻,這正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澡雪精神。
古寺坐落在山頂一處開闊處,紅墻灰瓦,在林木中隱約。朋友早升好了爐火,準備煮茶。茶是普洱。多年的老茶餅,放在爐子上滾燙地煮,人還未進來,便聞到一股泥土的茶香味道。以前的時候,他只喝新茶,明前的龍井、毛尖、大紅袍,如今入到山里,喜歡了老茶。陳茶儲藏,就像經歷了多年時光的老者,風風雨雨,陽光水汽,浸染著茶餅。那些若干年前采摘下來的植物葉子,經過發酵、壓制、烘焙,成為暗褐色的固體。如今,再經水的浸泡,重新舒展開來,脈絡重新吸收水分,茶葉重新活了過來,厚重、馥郁的茶香也慢慢散發,裊裊飄到紛擾的大雪中,整座山仿佛也香氣可人了。這像極一個生命重返的過程,每個人都仿佛溯游進自己的生命道場。
泡茶的水取的是雪水。山頂遍植松柏,白雪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松針之上,雪愈發顯得潔白,松愈發顯得蒼翠。紅袍的袈裟在雪地中像一團火。他手執缽盂,用竹篾輕輕刮掉松枝上的白雪,那小心翼翼的樣子,像呵護一個初生的生命。那是一顆柔軟的心,蒼茫的山石在他的面前,也似乎瞬間柔軟起來。
我們都一身白雪地走進古寺。落座,烹茶,啜飲,沒有客套,也沒有寒暄。桌上,正攤著一個小冊子,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規矩而溫順,是朋友正在抄寫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我抬頭四望,雪天里大殿格外森嚴、空曠,但端坐的菩薩正微笑著注視著我們,那目光里顯現出的慈祥,讓整座佛殿瞬間變得溫暖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