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祭田橫墓文》文章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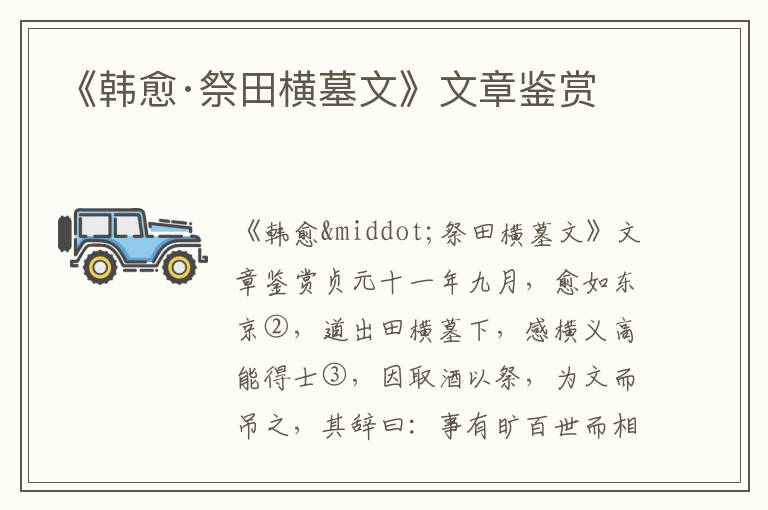
《韓愈·祭田橫墓文》文章鑒賞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②,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③,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吊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④,孰為使余欷歔⑤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fù)生,嗟余去此其從誰(shuí)?當(dāng)秦氏之?dāng)y,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dāng)_擾⑥,而不能脫夫子于劍铓⑦?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⑧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⑨。茍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仿佛而來(lái)享。
【注】
①田橫:戰(zhàn)國(guó)時(shí)齊王之后,曾自立為齊王。齊國(guó)被秦消滅以后,田氏家族堅(jiān)持反秦。秦朝末年,田氏起兵恢復(fù)齊國(guó)。秦亡后,群雄逐鹿,劉邦派韓信攻破齊國(guó),田橫自立為齊王,率部下五百余人退守海島。劉邦稱帝建立漢朝后,遣使招降,田橫帶隨從二人往洛陽(yáng)。未至二十里,羞為漢臣,田橫自殺。島上五百部屬聞田橫死亦全部自殺。史稱“田橫五百士”。②東京:唐代以洛陽(yáng)為東都。③義高能得士:重義氣就能夠得到賢士的擁戴和幫助。④稀:作“希”,崇尚。⑤欷歔:悲傷,嘆息。⑥擾擾:煩擾,多而亂。⑦劍铓(máng芒):劍鋒,劍刃。⑧闕里:孔子故居和講學(xué)授徒之處,孔子生于魯國(guó)曲阜闕里,此處用以指代孔門。⑨遑遑:奔走不停息的樣子。
這是一篇撫今追昔的文章。唐德宗貞元八年(792),韓愈28歲,進(jìn)士及第,但從此直至貞元十一年(795)這四年間,仕途多舛。他在長(zhǎng)安三試博學(xué)宏辭科,皆不中選;三上宰相書以謀官職,均未被理睬,毫無(wú)結(jié)果。于是他帶著滿懷的失意不遇之情,悵然離開(kāi)了長(zhǎng)安,到河南孟縣去掃祖墓。當(dāng)他路過(guò)田橫墓時(shí),田橫這位死于千年之前的古人,其“義高能得士”的遺風(fēng),正好與他失意不遇的情懷,相互映射感發(fā)。于是他借祭田橫而發(fā)泄自己的一腔憤慨,寫下了這篇十分具有特色的祭奠文。
作者并沒(méi)有沿著借古慨今這一思路一直寫下去,而是掉轉(zhuǎn)筆鋒,波瀾突起,使文章不顯得平直、呆板。可以說(shuō),文章雖然以懷古為主調(diào),但卻重在傷今。借對(duì)田橫能得士來(lái)諷刺當(dāng)權(quán)者的無(wú)能,從而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
這篇祭文不過(guò)150個(gè)字,如此短章,卻議論縱橫,回環(huán)往復(fù),辭簡(jiǎn)情深,全從空際翻騰,寫出無(wú)限悲慨,唯恐余而不盡。所謂蕩氣回腸,正是韓愈早期文章的一大特色。
后人評(píng)論
馬其昶評(píng)贊曰:“詞意皆騰空際,似為橫發(fā),又似不為橫發(fā),此等文不徒以雕琢造語(yǔ)為工也。”
清代金圣嘆曰:“以沉郁之氣,發(fā)悲涼之音。逐二句抗聲吟之,真有天崩海立之勢(shì)。”
清代林云銘說(shuō):“以千百年前喪敗武夫之荒冢,何關(guān)于人?乃殷殷陳辭薦酒,豈不扯淡。蓋是時(shí)退之試宏辭科不售,三上宰相書不報(bào),既歸河陽(yáng),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wú)門,眼淚無(wú)處揮灑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jiàn)。中段以為橫能得士,而士不能免橫于死,歸之天命。見(jiàn)得有橫之高義,便足照耀千古,即千古而下皆樂(lè)為之效命,不得較論成敗之跡也。寓意最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