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任《游歷下諸勝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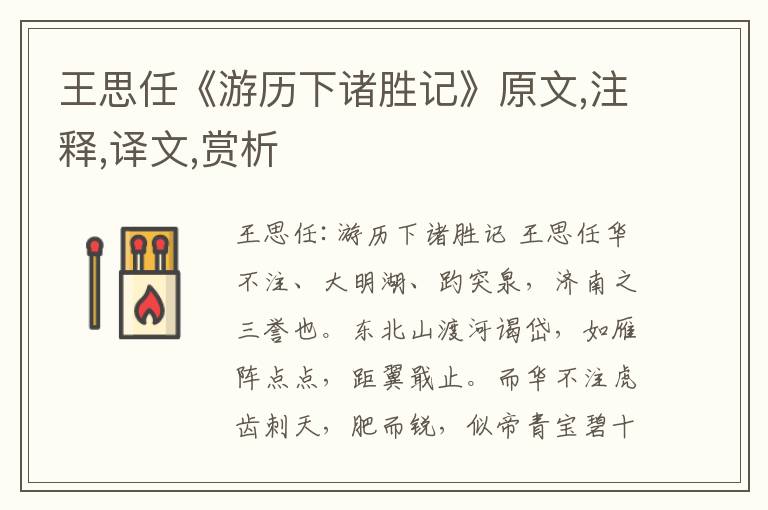
王思任:游歷下諸勝記
王思任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東北山渡河謁岱,如雁陣點點,距翼戢止。而華不注虎齒刺天,肥而銳,似帝青寶碧十分涂塑者。
予時僑居歷山書院。幕僚程、張二君以斗酒洽之漱玉亭上,觀所謂趵突泉者。昔時劍標數尺,而今僅為抽節之蒲,諸童子浴,裸褻之。王屋之氣,日短一日矣!泉也!且泉之左,為于麟先生白雪樓,已別有所屬,何處吊中原吾黨也!樓也!
且明日引鏡,眉間黃起,則既秣馬矣。盡辭上官之后,披襟獨往歷下亭子一看。菡萏千畝,流光溯空。蘆中人,誰與?若肯為我譜漁笛數弄,我不難賡桓伊也。盈盈脈脈,無以持贈,人亦誰可笑語!乃乞北門鎖鑰于某萬戶,倩睥睨為光明焉。南山危矗如佛首者,歷山耶?舜所耕在濮,此何以“歷”焉?戴玄趾詩送我:“平生少知已,慟哭鮑山邊。”東望有青蔚起者是矣。元張養浩《龍洞記》,畫兇刻險,涕中帶笑者也。且寄語東南一片云,愿他日北望華不注,而逢丑父卒智在此間與?安得從濼源賒一葦,直酌華泉下也!
夫山水之理,必不可鹵莽而得。濟南名勝,尚稱幽夥,一眺望間而欲瞭上下千百年之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者,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疏籠之羽,義無反顧,而吾猶得翱翔,成禮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臠全鼎,蜜無中邊,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
泉城濟南,山水勝美,而在眾多名勝中,尤以趵突泉、大明湖、華不注最負盛名,故而文章開頭即以突起之筆寫出:“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這一句對全篇具有統攝作用,既點出三者在濟南山水諸勝中的地位,又為下文分寫三景起了畫龍點睛作用。
在文章的第一段中,主要寫華不注山之美。這里曾是春秋時期晉軍“三周華不注”,追逐齊軍的戰場。但作者撇開晉齊大戰,也不直寫它的美景,而是先從掃描群山寫起,然后收攏目光轉向華不注。只見它體勢雄峻,肥碩而銳,峭峰上指,如虎牙刺天,峰巒聳翠,如顏料涂飾。這一段寫群山如“渡河謁岱”,“雁陳點點”,有靈動之感,而寫華不注體勢色彩之美,喻寫生動形象,有力度,有質感。同時,又是用眾星拱月手法,以群山之多而小烘托出華不注的高大峻峭,著墨無多,而勾畫了了。
文章的第二段,寫漱玉亭上觀泉。一泓清氣,萬斛珠璣的趵突泉,乃是泉城最奇最美的景觀。可是在作者游觀之時,它卻黯然失色。往昔“劍標數尺”的泉涌奇觀不見了,只剩下微弱的泉涌,僅如“抽節之蒲”,加上童子裸浴,褻污不堪。面對此狀,不禁觸景傷情。傳說趵突泉為王屋山水脈伏流至濟南噴涌而成,如今泉涌衰減,于是發出“王屋之氣,日短一日”的感嘆。泉的命運如此,泉側的白雪樓,命運也同樣地不幸。這座獨擅勝境的樓閣,原是明代后七子主將之一李攀龍(字于麟)辭官歸里后所建,作者來游之時,李攀龍早已故去,樓也“別有所屬”,換了主人,故而心下凄然,不勝滄桑之感,發出“何處吊中原吾黨”的悲嘆。這一段明寫泉、樓的今昔變化,暗寓明末國事世事,以泉之衰減、樓之易主,暗寫明代氣數將盡,江山行將易手,感情悲涼,旨意遙深。
第三段寫大明湖之游。先以數語交代收拾行裝,準備離開濟南,返歸故鄉。古人以為眉間發黃是回鄉有期的吉兆,韓愈《郾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云:“城上赤云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故而說引鏡自照,“眉間黃起”。在馬束裝之后,又一一告別上官,便獨自一人去大明湖作最后的游覽。只見大明湖“菡萏千畝,流光溯空”,雖然沒有“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景致,卻也是湖光花色,清美可人。此刻,忽然蘆葦叢中傳來悠揚的豎笛(簫)聲,因而聯想起伍子胥流亡途中藏身蘆中故事和善吹簫曲的桓伊故事,假想蘆中吹笛者如肯為吹奏漁笛數曲,當效桓伊之音,以曲賡續相和。可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雖聞蘆中人笛聲而杳然不見,相會無由,持贈無物,更無可同歡笑語,流連遐思之中,頓生孤寂之感。在無以慰藉的心情下,舉目四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危矗如佛首”的歷山(千佛山),由山的名稱又想及舜耕于河南濮陽歷山的故事,因而對它何以謂之歷山迷惑不解。其實,傳說中舜耕之歷山非止一處,歷史茫昧,又系傳說,既非考察,也不必去細辨,而作者之所以在心中攪起一陣歷史迷茫之感,乃是他心情迷惘的反映。繼而又在迷茫中東望鮑山,遙想龍洞,聯想起友人贈詩和張養浩游記,借以抒發世無知音,苦中為樂的情懷,孤凄不堪、悒郁難釋的心境流溢于字里行間。因為行將離去,對濟南山水不勝依戀,故而寄語白云,表達異日重游的心愿。可是,世事多變,能否如愿,實在渺茫,因而又陷入冥思遐想。在晉齊鞌之戰中,齊師大敗,逢丑父為掩護齊頃公躲開晉軍追捕,便在車上和他調換座位,及至為晉軍截獲,又使頃公到華不注山下汲取泉水,終于使他趁機逃脫。這段歷史久遠的故事,說明逢丑父臨危不懼,急中生智,奮不顧身地保護齊頃公,使他幸免于難。作者追述這個故事,撫今追昔,目的在于感嘆明朝將亡,世無良臣,沒有象逢丑父這樣忠貞智勇之士,也不能使明朝君主免于危難,所以用婉曲而又沉重的筆調故意問出一句:“逢丑父卒智在此間與?”然后又渴望從趵突泉一葦遠航,直至華泉酌取清泉的愿望,借以表達吊古傷今的思想情感。
文章的最后一段,以議論收結全篇。這一段有四層意思:一是說山水之理內蘊幽深,須細加思索方能理解;二是說濟南名勝眾多,歷史綿遠,倉促之間要想了解其中所蘊含的歷史故事,只不過是在屠宰場門前嗅一下氣味而已;三是說既然行將歸去,就應如出籠之鳥,義無反顧,不再逗留,況且已游三景,又依禮辭別過了,雖未盡興滿足,也不算無所收獲;四是說游覽之理有如《呂氏春秋》中所說的“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何況罐中之蜜,無中邊之分,山水風韻之理與此相同,游三景已可知濟南勝概了。最后又引《漢書·轅固傳》的“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寬慰自己,說明游山玩水,擇其精者而觀賞之也就足以心滿意足了。
這篇文章,由情生情,依景敘事,即景議論,又揉合歷史傳說,撫今追昔,借古喻今,打破時空限隔,縱橫發揮,或比喻,或擬人,起伏跳蕩,有氣勢,有深度,真摯深沉,質樸無華而又極富想象力、表現力,是一篇融情、景、事、理于一爐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