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散文·劉勰·情采》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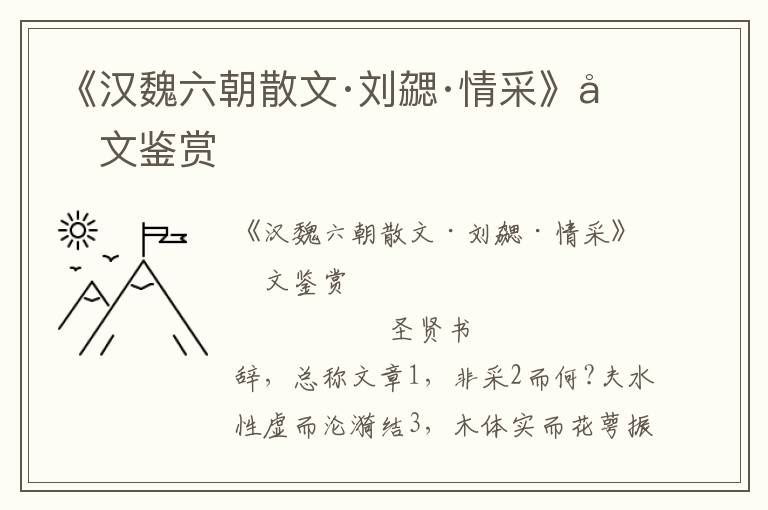
《漢魏六朝散文·劉勰·情采》原文鑒賞
圣賢書辭,總稱文章1,非采2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3,木體實而花萼振4,文附質也5。虎豹無文6,則鞹7同犬羊8;犀兕有皮9,而色資10丹漆:質待文也11。若乃綜述性靈12,敷寫13氣象,鏤心鳥跡14之中,織辭魚網15之上,其為彪炳16,縟17采名矣。故立文之道18,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19是也;二曰聲文,五音20是也;三曰情文,五性21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22,五音比而成《韶》、《夏》23,五情24發而為辭章,神理25之數也。《孝經》垂典26,喪言27不文28;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29也。老子疾30偽,故稱美言不信31,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33,謂藻飾也。韓非云:“艷采辯說34”,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于斯極矣。研味《李》、《老》35,則知文質36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37侈。若擇源于涇、渭之流38,按轡39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40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41;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42,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43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44。
昔詩人什45篇,為情而造文;辭人46賦頌,為文而造情47。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48;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49之徒,心非郁陶50,茍馳夸飾,鬻聲51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52。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53。而后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致54日疏,逐文55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56,而汛詠皋壤57;心纏幾務58,而虛述人外59。真宰60弗存61,翩其反62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63,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64,無其情也65。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66?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67;采濫辭詭68,則心理愈翳69,因知翠綸桂餌70,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71”,殆此謂也。是以“衣錦褧衣72”,惡文太章73;《賁》象窮白74,貴乎反本,夫能沒謨75以位理,擬地76以置心;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摛77藻。使文不滅質78,博不溺79心;正采耀乎朱蘭,間色屏于紅紫80,乃可謂雕琢其章81,彬彬君子矣82。
贊曰:言以文遠83,誠哉斯驗。心術84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85,舜英徒艷86。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注釋】 1文章:最初指刺繡品上五色交錯的花紋。2采:文采。《禮記·樂記》:“文采節奏,聲之師也。”在本篇中泛指作品的藝術形式。3性:性質,特征。淪漪;波紋。4萼:花朵下的綠片。5文:即采。質,即情。這句說明內容和形式關系的一個方面。6文:指虎豹皮毛的花紋。7鞹去了毛的皮革。8《論語·顏淵》: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9犀:兕,都是似牛的野獸,犀雄兕雌;皮堅韌,可制兵甲。10資:憑借,《左傳·宣公》:“華元使驂乘者謂之曰,中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犀咒皮韌,可以制甲,但須涂上丹漆,才有色彩之美。11這句說明內容和形式關系的又一個方面。12性靈:指人的精神方面,此句謂抒情。13敷:鋪陳,敷寫,描寫。此句指狀物。14鏤:刻,鏤心,精心推敲,鳥跡,文字。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15織辭:安排文辭。魚網,指紙。《后漢書,宦者蔡倫傳》:“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16彪炳:光彩鮮明。17縟:繁盛。18道:道路,途徑。19五色:青、黃、赤、白、黑。20五音:宮、商、角、征、羽。21五性:靜、躁、力、堅、智。又《大戴禮·文王官人》以喜、怒、欲、懼、憂為五性。22黼黻:古代禮服上的花紋。23比:綴輯。《韶》,舜樂。《夏》,禹樂。24五情:喜、怒、哀、樂、怨,又有人認為“情”當作“性”。25神理:神妙的道理。從《文心雕龍》全書看,劉勰所謂神妙的道理,就是《原道》篇所說的“自然之道”。26垂:留傳下來。典,法度。27喪言:哀悼父母的話。28不文:不修飾。《孝經·喪親章》:“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 29質:樸質。30疾:憎惡。31美言不信:《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針對某些虛華不實的文辭說的。32五千:即指老子的《道德經》,因它共有五千多字。《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于是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劉勰此句言老子自己的文章寫得很精妙,可見他并不是完全否定文彩之美。33辯雕萬物:《莊子·天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釋文》:“說,音悅。”辯,此指巧言。34艷采辯說:采,一般認為是“乎”字之誤。《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 35《李》:當作“孝”,指《孝經》。《老》,指《老了》。36文質:本來指形式和內容,但這里是復詞偏義,實際只指形式。37華實:也是偏義復詞,這里只指華。淫,過度,華過于實,則流為淫侈。38涇,渭;二水名,一清一濁。“涇渭之流”和后文“邪正之路”,均指文風而言:情辭相符,為正,為清;辭過于情則淫侈,為邪為濁。39轡:韁繩。按轡是騎馬緩行之狀,這里借喻作從容不迫的意思。40鉛:鉛粉。黛:古時女畫眉用的青黑色顏料。鉛黛喻辭采。淑姿喻性情。41倩:笑貌。淑:美好。42情性:指作品中所表達的作家的思想感情。43理:指作品的思想內容。44《經昀評曰》:此一篇之大旨。以上可算作是本篇的第一大段。說明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任何文學作品都必須有藝術表現形式,但內容是更基本的。45詩人:指《詩經》的作者,同時也指能繼承《詩經》優良傳統的作家。什,詩篇。46辭人:辭賦家,同時也指某些具有漢賦鋪陳辭藻特點的作家。47《范注》曰:“彥和,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廖廖數語,古今文章變遷之跡,盛衰之故,盡于此矣。” 48上:指統治者。“志思蓄憤”,即司馬遷《報任安書》聽說:“《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語本《毛詩序》。49郁陶:憂思。50鬻:賣。聲:名。51《范注》曰:《抱樸子·應嘲篇》:‘非不能屬華艷以取悅,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心口不契,即彥和下文所譏者。……夫怨思發于性情,強作抑楊,非為文造情而何?” 52濫:不切實。53體:體現。制,作品。54逐:追求,逐文,單純地追求文采。55軒:有屏藩的車,冕,禮冠。軒冕,官爵的代稱。此四句,謂抒寫情懷,辭出虛偽。56皋壤:指山野隱居的地方。57幾務:即機務,指政事。58人外:指塵世之外。59宰:主。這里指作者的內心。真宰,語本《莊子·齊物論》。60“真宰”二句,謂文中不見真性情。所表現的恰是相反的一面。61翩其反:適得其反。借用《詩經·小雅角弓》的成語。62蹊:路。語出《史記·李廣列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有真情實感的作品人才會百讀不厭。63 《淮南子·繆稱》:“男子樹蘭,美而不芳。“這里借喻為情感虛偽的文章,不可能有強烈的吸引力。64這是本篇第二大段,對文壇上重文輕質的趨勢進行了批判,提出文學創作要以“述志為本”的主張。66經,一作“理”,以作“理”為勝。67濫,不切實。詭,反常。68心理,作者內心所蘊籍的道理,表達為作品的思想內容。翳,隱蔽。69翠綸,用翠翡鳥毛做的釣魚線。桂,肉桂,是一種珍貴的食物。餌,食物。這里指魚食。70隱,埋沒,語見《莊子·齊物論》,“隱”下原有“于”字。71裂,一種套在外面的單衣,語見《詩經·孜孜不衛風·碩人》。72章,鮮明。73《賁》,《易經》卦名,霧,探索到底。這里用以說明華麗的文辭要歸之于自然。74謨,當作模,即規范。是說樹立一個正確的標準,把它放在恰當的地位上。理指思想。75地,底子,這里指文章的基礎。76摛,發布。77文,指作品的文采。質,指思想內容。“文不滅質”語出《莊子·繕性》。原意謂文和博本來是修飾質與心的,但過多的文與博,反而妨害和隱沒了質與心。這里說,要使文與質相符,情與采相應。78博,指辭采的繁盛。溺,淹沒。文意見上注。79屏棄紅紫類的雜色而不用。80章,文采。81語出《論語·雍也》。彬彬,文質兼顧,指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恰當,以上是本篇第三段,說明偏重形式就會損害內容,因此主張文學創作首先要有正確的內容,從而產生文質并茂的作品。82遠,流傳久遠。語本《左傳》襄公五十二年:“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83心術,動用心思的方法,這里指創作的構思方法。語本《禮記·樂記》:“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 。” 84渝,變。吳錦好渝,喻文章繁采寡情。85舜,木槿。英,花。木槿花朝開暮落,有花無實,故云。
【今譯】 古代圣賢的著作,都稱作“文章”,這不是由于它們都具有文采嗎?由于水的本性空靈,才有微波蕩漾,由于樹的本性質實,才有花兒開放。可見文采必須依附于特定的實物,虎豹的皮如果沒有斑文,那就跟犬羊一樣了;犀牛雖然有皮,但用作器物時,要靠涂上丹漆,才有漂亮的顏色:可見物體的實質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寫人類的思想情感,描繪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組織成辭句寫在紙上;其所以能夠光輝燦爛,就因為文采繁茂的緣故。
從藝術創作的道理來說,其文理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表形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顏色而成的;第二是表聲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聲音而成的,第三種是表情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種顏色互相錯雜,就構成鮮艷的花紋,各種聲音互相調和,就構成動聽的樂章,各種性情表達出來,就構成優美的作品,這是自然的道理所決定了的。《孝經》傳下來的教訓,只說父母死了,孝子守喪,說話才不加文飾。可知君子之人,在平時說話,未嘗沒有文采。老子痛恨虛偽,所以他說:“華麗的語言往往靠不住”,但他的《道德經》可是詞句精妙。這就表明他對語言的華美,可并非一概反對。莊周用輕視的口氣所說的“用巧妙的言辭來描繪萬事萬物”,指的就是修飾過度了。韓非子用反對的口吻所說的“對說話要求漂亮”,指的就是綺麗的詞句。文采太多的議論,修飾過度的言辭,使文章之變達于頂點,我們體會《孝經》,《老子》等書中的內容,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細看《莊子》、《韓非子》等書中的話,就明白作品的華麗是過分淫侈了。如果能夠在清流與濁流之間加以適當的選擇,在邪道與正路面前從容考慮,也就可以在文學創作中適當地駕馭文采了。脂粉是用來修飾容貌的,但少女的巧笑美目卻來自天生麗質;文采是用來修飾語言的,但言語的美妙動人卻是由于發乎至情。正如機杼上的經緯一樣,情性是文章的經,語言是思想的緯。只有經線拉正了,緯線才能織成布帛;只有思想明確了,語言才能通達流暢。這就是文學創作根本的道理。
從前《詩經》的作者所寫的詩歌,是為了表達思想感情而成的,后代辭賦家所寫的作品,則是為了寫作而去捏造出情感來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風》、《雅》的創作,是由于詩人憋著滿肚子的憤懣,最后忍不住了,才吟詠出來,以諷刺在上的人,這就是為了發泄感情才進行創作。一幫子的辭賦家,肚皮里本來就沒有憋著要說的話,卻勉強夸大其辭,沽名釣譽:這就是為了寫文章而捏造情感。所以為了表達情感而寫出來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辭精煉而內容真實:僅僅為了寫作勉強而成的文章,就往往是過于華麗而內容雜亂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愛好虛華而輕視真實,拋棄了古代《詩經》的傳統,只習染近世辭賦的風尚,因此,描寫性情的作品在一天天的減少,而追求詞藻的篇章則一天天增加。所以有的人內心里深深思念著高官厚祿,卻滿口歌頌著山林的隱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對人間名利關心之至,卻虛情假意地來抒發塵世之外的情趣。心里本來就沒有真實的感情,嘴上說的話,其效果也只能適得其反罷了。桃李不須自吹自擂,樹下便自然會走出一條小路,那是由于樹上已結滿了果實;男子種蘭花而聞不到它的清香,那是由于他沒有這種幽情。以草木那么微末的事物,尚且都要依情待實,何況以抒情述志為本的文章,口是心非,怎能取信于人?
因此,寫文章時運用辭藻,目的是要講明事理。如果文采浮泛而怪異,作品的思想內容就必然模糊不清。這就好比釣魚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釣繩,用桂枝做魚食,反而釣不到魚。古書上說的:“言辭的涵義被過繁的文采所掩蓋了”,指的大約就是這類事情。《詩經》上說:“穿了錦繡衣服,外面再加上罩衫。”這就是因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賁卦》最后一爻之象還是以白色為正,所看重的就是回復本來的面目。
進行創作應該樹立一個正確的規范來安置作品的內容,擬定一個適當的基礎來表達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體現的思想感情確定了,才能據以配上音節,綴以辭采。從而做到形式雖然華美,但不掩蓋其內容;辭采雖然繁富,但不至淹沒作家的心情。要使紅、藍等正色發揚光大,而把青、紫等雜色拋棄不用。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內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總而言之,說話因有文采才能流傳久遠,這的確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真理。但思想感情表現了出來,才能談得上文采華瞻。就象太華麗的錦繡,卻容易改變了顏色;又如朝開而暮落的本槿花,嬌艷也是徒然。只有繁麗的文采,而缺少真情實感,這樣的作品細心玩味起來,定會令人生厭。
【集評】: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曰:“舍人處齊梁之世,其時文體方趨于繁縟,以藻飾相高,文勝質衰,是以不得無救正之術。此篇恉歸,即在挽爾日之頹風,令循其本,故所譏獨在采溢于情,而于淺露樸陋之文未遑多責,蓋揉曲木者未有不過其直者也。雖然,彥和之言文質之宜,亦甚明憭矣。首推文章之稱,緣于采繪,次論文質相待,本于神理,上舉經子以證文之未嘗質,文之不棄美,其重視文采如此,曷嘗有偏畸之論乎。”
【總案】: 自孔子提出“文質彬彬”這種關于人的修養與風范的一般關系的看法,應算是先秦的思想家們對于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有了初步體認。曹丕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標志著文學進入了“自覺的時期”(魯迅語)至陸機“詩緣情而綺靡”,才算是給予藝術形式以最充分的肯定,這個高度也許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始終都未曾被突破。
劉勰的成就是單辟一章來討論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十分全面而具體,涉及到方方面面,這種規模與深思熟慮是前人未曾作到的。但盡管劉勰給了藝術內容的角度來討論。而倒底也沒有象陸機那樣痛痛快快的地大喝一聲,沒有讓藝術形式擺脫“為它人作嫁衣裳”的地位,讓它高高興興地“獨對東風舞一場”。這表明劉勰的觀點仍不失為穩健。
當文藝已發展進入“現代”的今天,這種對藝術形式的傳統看法,毫無疑問也有了重新商榷的必要。這些動態與發展無疑也應引起古文論研究的警覺與深思。
所談是藝術形式的問題,給人的感覺是這個題目激發了劉勰更多的熱情。這是為他所鍾愛的題目之一。他的筆觸熱烈而奔放,深情而綺麗。這很符合他睿智的看法,就是對形式頗多非議的圣賢,自己寫起文章來,也是不廢文辭的,故劉勰不愿埋沒自己的才情,不愿放棄自己的濃墨重彩,很難想象,這些絢麗的篇章就是在青燈古卷旁寫就的,是出自一位清心寡欲,深諳佛理的僧侶或候補僧侶之手。人類的精神現象真是何等奇妙呵。
《文心雕龍》為自己在文批史上盛大的聲名所掩,使人幾乎忘記了,它也是第一流的美文,故在有關本書的介紹與闡釋的文章中,鮮能看到從純文藝的角度,即它本身的藝術質量。成就的角度加以論述的。而《情采》篇似乎在暗示和提醒我們,哪怕就是討論艱深枯燥的理論問題,劉勰也沒有忘記給它一個美麗的外衣,給它絢麗的……情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