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京派”和“海派”》散文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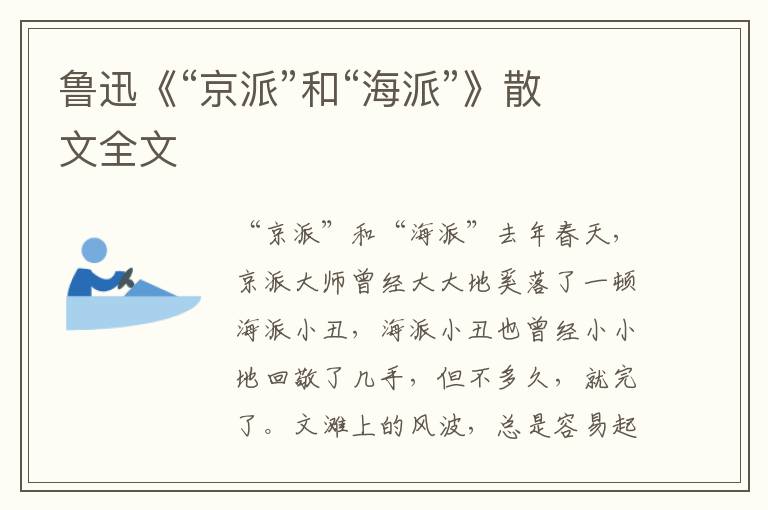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師曾經大大地奚落了一頓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經小小地回敬了幾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灘上的風波,總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當。我也曾經略略地趕了一下熱鬧,在許多唇槍舌劍中,以為那時我發表的所說,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錯了的。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過一整年帶點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說的并不圓滿。目前的事實,是證明著京派已經自己貶損,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現身說法,演述了派別并不專與地域相關,而且實踐了“因為愛他,所以恨他”的妙語。當初的京海之爭,看作“龍虎斗”固然是錯誤,就是認為有一條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為現在已經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過黃鱔、田雞,炒在一起的蘇式萊——“京海雜燴”來了。
實例,自然是瑣屑的,而且自然也不會有重大的例子。舉一點罷。一是選印明人小品的大權,分給海派來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選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說是冒牌的,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簽,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缽。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頭,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開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東西,和純粹海派自說是自掏腰包來辦的出產品頗有區別的。要而言之:今兒和前兒已不一樣,京海兩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這里要附帶一點聲明:我是故意不舉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來的。先前,曾經有人用過“某”字,什么緣故我不知道。但后來該刊的一個作者在該刊上說,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為這是因為不替它來做廣告。這真是聰明的好朋友,不愧為“熟悉商情”。由此啟發,仔細一想,他的話實在千真萬確:被稱贊固然可以代廣告,被罵也可以代廣告,張揚了榮是廣告,張揚了辱又何嘗非廣告。例如罷,甲乙決斗,甲贏,乙死了,人們固然要看殺人的兇手,但也一樣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蘆席圍起來,兩個銅板看一下,準可以發一點小財的。我這回的不說出這刊物的名目來,主意卻正在不替它作廣告,我有時很不講陰德,簡直要妨礙別人的借死尸斂錢。然而,請老實的看官不要立刻責備我刻薄。他們哪里肯放過這機會,他們自己會敲了鑼來承認的。
聲明太長了一點了。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直到現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來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實本領的,法郎士做過一本《泰綺思》,中國已有兩種譯本了,其中就透露著這樣的消息。他說有一個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亞歷山大府的名妓泰綺思,是一個貽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們,也給自己積無量功德。事情還算順手,泰綺思竟出家了,他恨恨地毀壞了她在俗時候的衣飾。但是,奇怪得很,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獨房里繼續修行時,卻再也靜不下來了,見妖怪,見裸體的女人。他急遁、遠行,然而仍然沒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為其實愛上了泰綺思,所以神魂顛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卻還是硬要當他圣僧,到處跟著他祈求、禮拜,拜得他“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終于決計自白,跑回泰綺思那里去,叫道:“我愛你!”然而泰綺思這時已經離死期不遠,自說看見了天國,不久就斷氣了。
不過京海之爭的目前的結局,卻和這一本書的不同,上海的泰綺思并沒有死,她也張開兩條臂膊,叫道:“來!”于是,團圓了。
《泰綺思》的構想,很多是應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倘有嚴正的批評家,以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實本領”,我也不想來爭辯。但我覺得自己卻真如那本書里所寫的愚民一樣,在沒有聽到“我愛你”和“來”之前,總以為奚落單是奚落,鄙薄單是鄙薄,連現在已經出了氣的弗洛伊特學說也想不到。
到這里又要附帶一點聲明:我舉出《泰綺思》來,不過取其事跡,并非處心積慮,要用妓女來比海派的文人。這種小說中的人物,是不妨隨意改換的,即改作隱士、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類,都無不可。況且泰綺恩其實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時是潑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地修,比起我們的有些所謂“文人”,剛到中年,就自嘆道“我是心灰意懶了”的死樣活氣來,實在更其像人樣。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寧可向潑剌的妓女立正,卻不愿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
至于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來”了呢?說起來,可又是事前的推測,對不對很難定了。我想:也許是因為幫閑幫忙,近來都有些“不景氣”,所以只好兩界合辦,把斷磚、舊襪、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兒之類,湊在一處,重行開張,算是新公司,想借此來新一下主顧們的耳目罷。
四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