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列子·仲尼篇(節選)》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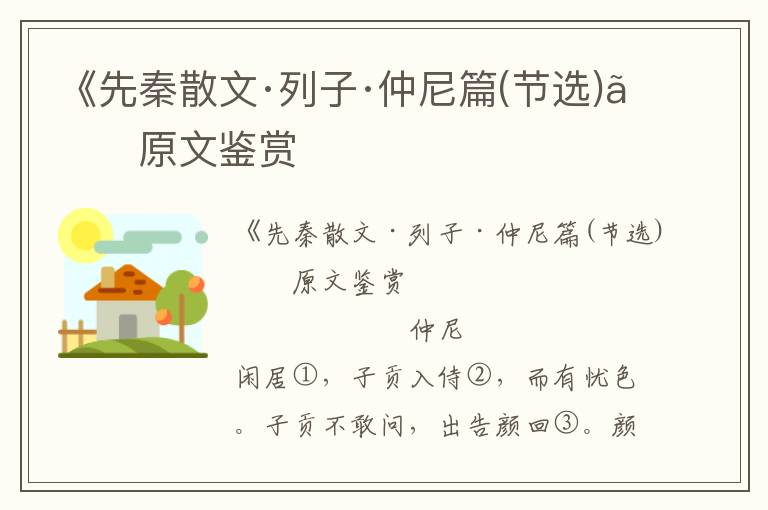
《先秦散文·列子·仲尼篇(節選)》原文鑒賞
仲尼閑居①,子貢入侍②,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③。顏回援琴而歌④。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⑤?”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⑥’,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閑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⑦。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⑧。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⑨:修一身⑩,任窮達(11),知去來之非我(12),亡變亂于心慮(13),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英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14),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于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15):“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16),不寢不食,以至骨立(17)。顏回重往喻之(18),乃反丘門,弦歌誦書(19),終身不輟(20)。
【注釋】 ①閑居:閑坐,閑處。 ②子貢:即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③顏回:魯國人,字子淵。 ④援琴:彈琴。援:引。⑤一本“濁”上有“敢”字。 ⑥命:數運。 ⑦意:度。 ⑧正:是。 ⑨實:實質,內涵。 ⑩修:安。 (11)任:聽任。窮:困,謂困于仕途。達:進,謂身入仕途。 (12)去:指致仕。來:指入仕。(13)亡:本作“止”。 (14)當(dang音檔) 年:現時。當:今。 (15)拜:當作“拜⒋”,誤作“拜”。即今“拱”字。 (16)淫(yin音寅):久。 (17)骨立:比喻形貌清瘦。 (18)喻:曉。 (19)弦(xian音賢):彈琴瑟。(20)輟(chuo音綽):停止。
【今譯】 孔子閑坐,子貢進去陪老師,孔子面有愁容。子貢不敢問,出來告訴顏回。顏回彈琴唱起歌來。孔子聽見后,果真把顏回叫進去,問道:“你為什么一個人快樂?”顏回說:“老師為什么一個人憂愁?”孔子說:“先談談你的想法。”,顏回說:“我從前聽到老師說:過:‘安于自然之分,任于窮達之理,所以不憂愁’,我因此快樂啊。”孔子變了臉色,停了一會兒說:“有這樣的話嗎?你的理解太偏狹了。這不過是我從前說的話罷了,請以今天說的為準吧。你只理解樂天知命而無憂,還不理解樂天知命有大憂啊。現在我告訴你真正的含義:一人修身自好,任其窮困或顯達,致仕入仕不是自己所能掌握,在心里把一切主亂統統忘掉,這就是你所認為的樂天知命而無憂。從前我刪定詩書,訂正禮樂,打算以它治理天下,留給后世;不只是一人修身自好,用來治理魯國。但魯國的君臣一天天顛倒了人倫,仁義日益衰落,人情日益澆薄。這治世之術在一國在今世都行不通,那整個天下與將來怎么樣呢?我才知道詩書、禮樂不能挽救世亂,而且不知如何革除時弊的方法。這就是樂天知命的人的憂愁。雖說如此,我還是懂得了一個道理。這里說的樂和知,不是古人所說的樂和知。沒有樂,沒有知,才是真樂真知;所以沒有不樂的,沒有不知的。沒有不憂的,沒有不做的。詩書、禮樂,有什么可拋棄的呢?又怎樣革除時弊呢?”顏回面朝北拱手說:“我也懂得了這個道理啊。”出來告訴子貢。子貢茫然不得其意。回家深思了七天,睡不著覺,吃不下飯,以至于瘦削不堪。顏回又前去開導他,然后回到孔子的門下,彈琴唱歌,誦讀詩書,終生不停。
【集評】 宋·劉辰翁《列子沖虛真經評點》:“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又:“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并憂樂無之,知憂樂而為憂樂,不若并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卻寓言以抑揚之,甚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書。”
明·孫礦《列子沖虛真經評》“此又是粗直文字,雖不甚煉細,卻慷慨有氣。”
明·陳仁錫《列子奇賞》:“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有憂者,圣人之體也。”
又:“回賜根器不同。”
民國·張之純《評注諸子菁華錄》:迂徐而入筆,妙似檀弓。”
又:“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君門則萬者二人,季氏則工備八佾,子家不歸君知其出郭重猶在食言而肥,彼婦出走,遑恤迷陽一老,遺何裨兩社,蓋貌不瘁而神傷矣。此真宣圣遺訓,非同百家偽托。”
又:“結以禮樂詩書為歸宿,神不外散。”
【總案】 《論語》記載了孔子和他的學生許多坐而論道的事,這則即從此改妝而來。孔子對“樂天知命”,“正禮樂以治天下”的懺悔,即是作者的一番喬裝打扮。在本段文意三轉,對儒道抑揚軒輊之間,以示有了道家的“無樂無知”神不外散的功夫,才能獲得“無所不為”的法力無邊的境界。這樣高妙的道理,對于熱衷于入世的子貢這類人,當然會“茫然自失”,而且“淫思七日”而不解,一旦徹悟,則終身樂之無窮。這大概也是作者喚醒世人的一番苦心。文字樸直,不事鉛華;徐徐論道,絮絮而談,旋折轉換之間不乏“慷慨有氣”(孫礦語)的特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溪公言之于周宣王①,王備禮以聘之②。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③。宣王心惑而疑曰④:“女之力何如⑤?”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⑥,堪秋蟬之翼。⑦”王作色曰⑧:“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⑨,猶憾其弱⑩。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11);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于內者無難于外,于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于負其力者乎?”
【注釋】 ①公儀、堂溪:姓氏。 ②聘:求。 ③懦:弱。④疑:難,詰問。 ⑤女:同“汝”。 ⑥螽(zhong音終):蝗蟲。⑦堪(kan音刊):通“戡”,刺。 ⑧作:變。 ⑨曳(yi音益):拖;拉。 ⑩憾:恨。 (11)六親:指父、母、兄、弟、妻、子,或泛指親屬。
【今譯】 公儀伯因有力氣聞名于諸侯,堂溪公把他引薦給周宣王,周宣王準備禮物聘請他。公儀伯來了,看他的模樣,是一個懦夫。宣王心里疑惑地詰問說:“你的力氣到底怎么樣?”公儀伯說:“我的力氣可以折斷春蝗的腿,能刺破秋蟬的翅。”宣王變了臉色說:“我的力氣能撕裂犀牛和兕的皮,能拉住九頭牛的尾巴,還嫌力氣小。你能折斷春蝗的腿,能刺破秋蟬的翅,就以力聞名天下,為什么呢?”公儀伯長嘆著離開坐席,說:“大王問得好啊!我冒昧拿實情來回答你。我的老師商丘子,力氣在天下沒有對手,但是他的親戚們一點兒也不知道;因為他不曾用過力氣的緣故。我以死來事奉他。他才告訴我說:‘人要顯露自己所不易顯露的,看別人所不愿看的;要得到自己所不易得到的,做別人所不愿做的。所以學看的首先看見一車柴,學聽的首先聽見敲鐘。在心里容易的在外表就沒有什么難處,在外表沒有什么難處,所以名聲從他一個家庭傳不出來。’現在我在諸侯中很知名,這是因為我違背老師的教導,顯示我自己的能耐。然而我的名聲不是因為憑我的力氣,而是因為我善于用力氣;不是勝過了那些僅憑自己力氣的人嗎?”
【集評】 宋·劉辰翁《列子沖虛經真評點》:“此處亦微有意,然語不白,甚欠發明。”
又:“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于有若無實。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
明·孫礦《列子沖虛真經評》:“大約與莊子庖丁章同意,是戲為詭語以見奇,然至理卻亦寓于兵法避實擊虛,攻其不守,守其不攻,皆是此意。”
民國·張之純《評注諸子菁華錄》:“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下一能字,上又冠以臣之力三字,絕世奇文。”
又:“為自負其能者,痛下針砭,真覺天地可容好名之心。”
無名氏《列子精華》:“意妙。”
又:“運用精神之極,勁而腴,峭而潤。”
【總案】 這一場較量力氣大小的比賽,出于一般人所料,只能舉起秋蟬翅膀的弱者,卻戰勝了能拖九條牛尾的力士。其實質則是對老子以弱治強觀點的闡揚,“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于負其力者乎”的看法,是道家政治哲學中最有生命力的見解。不過這個極致,在這里說得不甚曉暢,正如劉辰翁所批評的“語不白,甚欠發明”,因之和同篇其他寓言相較,哲理文辭則稍為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