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佺《游武夷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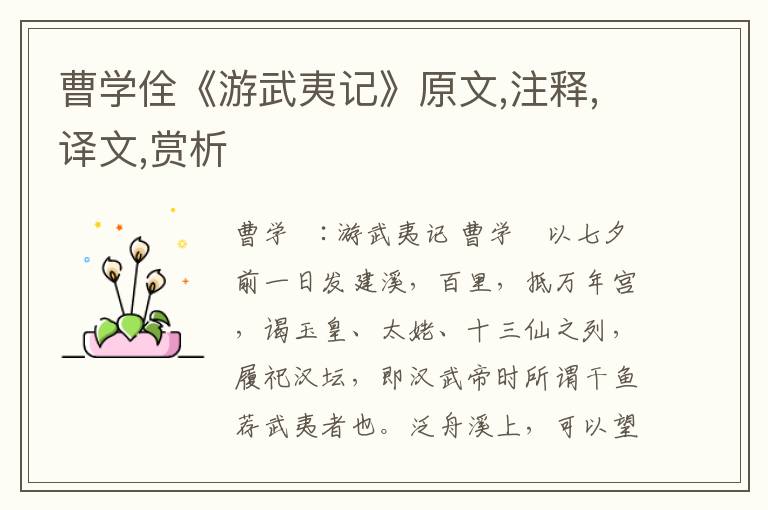
曹學佺:游武夷記
曹學佺
以七夕前一日發建溪,百里,抵萬年宮,謁玉皇、太姥、十三仙之列,履祀漢壇,即漢武帝時所謂干魚薦武夷者也。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峰,巍然首出為大王,次而稍廣為幔亭。按《志》:“魏子騫為十三仙地主,筑升真觀于峰頂,有天鑒池、摹鶴巖諸勝。以始皇二年,架虹橋而宴曾孫,奏‘人間可哀’之曲。”今大王梯絕不可登,幔亭亦唯秋蟬咽衰草矣。玉女、兜鍪之下數里為一線天。道經友定故城,虎為政,游人不敢深入。兩崖相闔者里許,中露天光僅一線。有風洞,白玉蟾斬蛇于此,今祠之,而肅殺之氣猶存云。
移舟過大藏峰,踵御茶園,萬磴而上,其山如鳥巢,蓋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為更衣臺。渡隔岸,謁朱子讀書所,拜其遺像,徘徊久之。以一逕入云窩,陳丹樞修煉之所,存其石灶。出大隱屏以西,登接簡、木梯鐵纜之路,視上則恐錯趾、視下則恐眩目。千盤而度龍脊,乃有仙奕亭可憩。修竹鳴蟬之外,黃冠啟閉于丹房而已。天游雖稱崔嵬過之,然迢遞可肩輿入。登一覽臺,于是三十六峰之勝,可屈指數矣。
復命舟里許,過隘嶺,為陷石堂。小橋流水之中,度石門而桑麻布野,雞犬聲聞,依稀武陵之境乎?于是望鼓子峰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棧道,相為鉤連。叩巖石,逢然作鼓聲。巖下為吳公洞,洞旁為道院。是游凡以次達九曲矣。乃歸萬年宮。從山麓走二十里,游水簾,亂崖飛瀑而下,衣裾入翠微盡濕。以別澗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學佺曰:“余考《武夷祀典志》,詳哉!其言之。則知人主之媚于神仙,所從來矣。始皇遣方士徐市求仙海上,而武夷不少概見,何以故?又按魏子騫遇張湛十三仙,及宴曾孫,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后無聞焉。夫山靈之不以此易彼明矣。語云:‘遺榮可以修真’,是之謂夫?”
武夷山,也稱小武夷,在福建崇安縣南,相傳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綿亙百二十里,有三十六峰,九曲溪穿流其中,形成“溪曲三三水,山環六六峰”的回環曲折之美,為福建第一名山。曹學佺這篇《游武夷記》寫他乘舟游山過程,純用白描速寫,內容豐富,要言不繁。
游記開頭先介紹游武夷山的時間、路線,拜謁了玉皇、太姥、十三仙,登上漢武帝時所建的武夷君祀壇。因當時按祭禮規定,武夷君以干魚祭,故而說“干魚薦武夷”。接下來,作者從萬年宮出發,沿著盤繞于山中的九曲溪觀賞武夷勝景,隨游程所至輕筆快寫途中所見、所聞、所感。
雄踞九曲溪口的大王峰是游程的第一步。作者先用它的“巍然首出”與“次而稍廣”的幔亭峰作一比較,描寫它們不同的形態;再引武夷山有關史志,點出魏人王子騫作為十三仙之主,曾在大王峰頂筑有升真觀,除此還有天鑒池、摹鶴巖等勝跡。并敘述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架虹橋宴請諸鄉人的情景。然而,這只不過是虛緲的傳說。眼前的大王峰已梯絕路斷,不可攀登,幔亭峰也只有蟬鳴衰草,荒涼冷落。繼而過玉女峰、兜鍪峰下,中途經陳友定故城,游“一線天”。作者先用“兩崖相闔者里許,中露天光僅一線”,勾畫出一線天的景觀特征。隨后寫一線天“三洞”(伏羲、靈巖、風洞)之一的風洞,傳說白玉蟾(即宋人葛長庚,因歸白氏而改名,)曾在此斬蛇除害,當地立有紀念他的祠堂,昔日的肅殺之氣仿佛還在洞中徘徊。
船到大藏峰,作者訪御茶園后往右“萬磴而上”,游魏子騫更衣臺,然后渡水拜謁紫陽書院(即武夷精舍),宋代朱熹曾在這里著書講學達十年之久。從作者“拜其遺像,徘徊久之”這一自身情態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對朱熹的由衷贊賞和敬佩。接著游覽“陳丹樞修煉之所”的云窩,又出大隱屏,登木梯、鐵纜架設的險徑,以“視上則恐錯趾,視下則恐眩目”的真切感受寫出山路的險峻異常。在步過千盤山道而度龍脊險路之后,又到了修竹鳴蟬,”,清靜幽雅的仙奕亭,這里只有黃冠道士在煉丹房進出往來,是一個遠絕塵世的地方。接著到天游峰,雖然其峰高峻,但可乘小轎而上。登上一覽臺,武夷三十六峰的勝境便盡收眼底了。
依游程所至,過隘嶺,至陷石堂,穿越石門,見到了山中難得一見的“小橋流水”,“桑麻布野,雞犬聲聞”的田園風光,依稀間,恍如置身于陶淵明所寫的桃源仙境。而后“穿修篁五里”到鼓子峰游覽,用“叩巖石,逢然作鼓聲”,只七八字便寫出以手叩石的動作和奇石異響。接著順筆說明“巖下為吳公洞,洞旁為道院”。到此,作者遍游了武夷九曲勝境,重又回到萬年宮。然而,作者似乎興猶未盡,于是又帶出游水簾洞一節。“泛舟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這一筆回應文章開頭,把游程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
作者顯然是沒有著力于山水氣象的渲染,也沒有具體細的物象刻寫。他似乎總想采取依景作畫的方式,把一個接一個的景觀組合成山水畫面,將那些傳說軼事、風俗民情娓娓道于讀者耳旁。在他或泛舟、或穿洞、武度、或謁、或過之中,對武夷山作了全景式的掃描,從而那幅溪山環繞、奇峰迭出的武夷山水圖便簡潔明了地展示在讀者眼前。寫景中總帶有一種興之所致的輕快感,仿佛信手拈來,卻又形象鮮明,物象豐富,簡潔傳神,充分地體現出銳敏的觀察力和高超的表現力。
武夷山被列為道教第十六洞天,文中隨游程引述有關道教仙人的傳說,突出了武夷山的特點。作者的情趣并不在欣賞這些道教所虛構的荒誕故事,只是借事寫景,刻畫出武夷山神奇的風貌。所以最后一段對秦始皇時代盛行求仙之風頗有微辭,而認為“山靈不以此易彼”,依然是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而求仙之事只不過是過眼云煙,早已在歷史的風雨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