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費(fèi)誓第三十一》譯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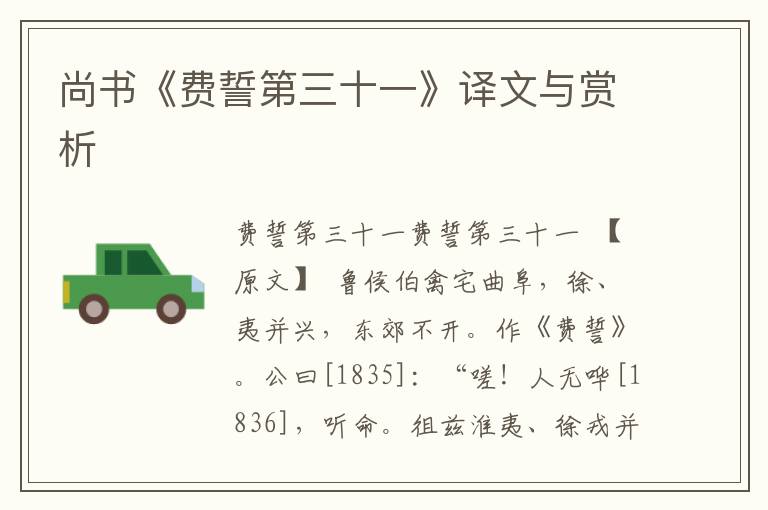
費(fèi)誓第三十一
費(fèi)誓第三十一
【原文】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費(fèi)誓》。公曰[1835]:“嗟!人無嘩[1836],聽命。徂茲淮夷、徐戎并興[1837]。善乃甲胄[1838],敿乃干[1839],無敢不吊[1840]!備乃弓矢,鍛乃戈矛[1841],礪乃鋒刃[1842],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1843],杜乃擭[1844],敜乃阱[1845],無敢傷牿[1846]。牿之傷,汝則有常刑[1847]!馬牛其風(fēng)[1848],臣妾逋逃[1849],勿敢越逐[1850],祗復(fù)之[1851],我商賚汝[1852]。乃越逐不復(fù)[1853],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1854],逾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注釋】
[1835]公:指魯侯伯禽,周公的兒子。
[1836]人:眾軍士和費(fèi)地的百姓。
[1837]徂:讀為“且”,今日。淮夷:淮水之夷。徐戎:徐水之戎。興:起。
[1838]敊(liáo):縫綴。甲:軍衣。胄:頭盔。
[1839]敿(jiǎo):系連。干:盾牌。
[1840]吊:善。
[1841]鍛:鍛煉。
[1842]礪:磨。
[1843]淫:大。舍:放。捁(gù):牛馬的畜棚。
[1844]杜:閉。擭(huò):裝著機(jī)關(guān)的捕獸器。
[1845]敜(niè):填塞。阱:陷阱。
[1846]傷捁(gù):指傷牛馬。承上文捁牛馬而言,這是一種借代方法。
[1847]有:得到。
[1848]風(fēng):走失。
[1849]臣妾:奴仆。古代男仆叫臣,女仆叫妾。逋:逃跑。
[1850]越逐:離開部隊(duì)去追逐。越,逾。
[1851]祗:敬。復(fù):還,指歸還原主。
[1852]商:賞。賚:賜予。
[1853]乃:如果。
[1854]寇:劫取。攘:偷取。
【譯文】
徐夷東夷勃興,屢屢作亂,魯侯伯禽坐鎮(zhèn)曲阜,準(zhǔn)備興兵討伐。臨行作前動(dòng)員令,即《費(fèi)誓》。魯公伯禽說:“好了!大家不要喧嘩,聽我的命令。現(xiàn)今淮夷、徐戎同時(shí)起來作亂。好好縫綴你們的軍服頭盔,系連你們的盾牌,不許敷衍了事!準(zhǔn)備你們的弓箭,鍛造你們的戈矛,磨利你們的大刀,不許敷衍了事!現(xiàn)在要大放圈中的牛馬,掩蓋你們捕獸的工具,填塞你們捕獸的陷阱,不要傷害牛馬。傷害了牛馬,你們就要受到常刑!牛馬走失了,男女奴仆逃跑了,不許離開隊(duì)伍去追趕!得到了的,要恭敬送還原主,我會(huì)賞賜你們。如果你們擅自離開隊(duì)伍去追趕,或者不歸還原主,你們就要受到懲罰!不許搶奪掠取,跨過圍墻,偷竊馬牛,騙取別人的男女奴仆,這樣,你們都要受到懲罰!
【原文】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1855],無敢不逮[1856];汝則有大刑[1857]!魯人三郊三遂[1858],峙乃楨干[1859]。甲戌,我惟筑[1860],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馀刑[1861],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1862],無敢不多[1863];汝則有大刑[1864]!”
【注釋】
[1855]峙:具備,準(zhǔn)備。糗(qiǔ):炒熟的米麥。糗糧,就是干糧。
[1856]逮:及,到。
[1857]大刑:死刑。“汝則有大刑”的前面,省去了“不逮”二字。
[1858]郊:近郊。遂:遠(yuǎn)郊。三郊三遂:古代諸侯出兵先在國都附近征兵,兵員不足則在全國范圍內(nèi)征兵。
[1859]楨干:筑墻的工具。楨用在墻的兩端,干用在墻的兩旁。
[1860]筑:修筑營壘。
[1861]馀:釋放。無馀刑,就是終身監(jiān)禁而不釋放。
[1862]芻:生草。茭:干草。
[1863]多:《史記·魯世家》寫作“及”。
[1864]大刑:最重的懲罰。
【譯文】
“甲戌這天,我們征伐徐戎。準(zhǔn)備你們的干糧,不許不到;不到,你們就要受到死刑!我們魯國三郊三遂的人,要準(zhǔn)備你們的筑墻工具。甲戌這天,我們要修筑營壘,不許不供給;如果不供給,你們將受到終身不釋放的刑罰,只是不殺頭。我們魯國三郊三遂的人,要準(zhǔn)備你們的生草料和干草料,不許不夠;如果不夠,你們就要受到死刑!”
【解析】
《費(fèi)誓》是一篇很有價(jià)值的歷史文獻(xiàn)。當(dāng)時(shí)居住在淮河流域的“淮夷”和“徐戎”等少數(shù)民族的部落和國家群起叛亂。于是,封在今山東曲阜一帶的魯國國君,就組織軍隊(duì)前往征伐。《費(fèi)誓》就是魯公在軍隊(duì)出征行至費(fèi)(今山東費(fèi)縣)時(shí)對全體戰(zhàn)士的訓(xùn)話。在這篇講話中,魯公命令戰(zhàn)士:縫綴好你們的盔甲,準(zhǔn)備好你們的弓箭,鍛煉好你們的戈矛,磨礪好你們的鋒刃。由此可以知道當(dāng)時(shí)的武器裝備情況。
魯公又對戰(zhàn)士們說:“馬牛走失,奴隸逃亡的,不要去追逐。如果偷竊馬牛,拐騙臣妾的就要受到懲罰。”這里又透露了當(dāng)時(shí)的奴隸逃亡情況。其中還提到魯人在“三郊三遂”內(nèi)大量的征兵。“郊”是離國都較近的區(qū)域,“遂”是郊以外的邊遠(yuǎn)地區(qū)。由此又可知當(dāng)時(shí)諸侯國的行政區(qū)劃情況。總之,《費(fèi)誓》中保存了許多軍事、政治、社會(huì)的珍貴史料。但是,這篇文獻(xiàn)究竟是何時(shí)作的?發(fā)令的魯公又是誰呢?歷來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最早的一種意見認(rèn)為,《費(fèi)誓》作于西周成王時(shí),講話的魯公就是初封魯國的周公之子伯禽。《史記·魯世家》說:“伯禽即位之后,管叔、蔡叔等反。……淮夷、徐戎亦并興反”,于是伯禽率師征伐,作《費(fèi)誓》。后漢至魏晉間人編寫的《書序》,唐孔穎達(dá)纂修的《尚書正義》,都持此說。然而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據(jù)《史記·周本紀(jì)》載:成王初年,周公“攝政當(dāng)國”,管叔、蔡叔與武庚、淮夷叛亂。“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可知東伐管叔、蔡叔,平定淮夷之役,是在成王年少,周公代行王政時(shí)。而周公之子伯禽封魯,是在周公攝政七年,還政成王之后。
《尚書·洛誥》記:“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即攝政)惟七年”,于是“王命周公后”即成王命封周公的后代。這樣,伯禽封魯時(shí),管叔、蔡叔、淮夷的反叛早已平定。伯禽怎么能在魯國,作為魯公去征伐它們呢?鑒于上述與歷史記載的矛盾,《后漢書·東夷傳》上說:周康王之后,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黃河邊上。穆王畏懼它的勢力強(qiáng)大,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根據(jù)這條材料,清人孫星衍認(rèn)為,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shí)。所以編《尚書》者把這篇放在記康王事的《顧命》之后,而在記穆王事的《呂刑》之前(《尚書今古文注疏》)。但是這種說法,顯然論據(jù)不足。《東夷傳》僅說周穆王令徐偃王主管東方諸侯,它既沒有提及魯國征徐戎的事,更沒有說出征徐戎的魯公是誰。
《費(fèi)誓》作于春秋時(shí)代魯僖公的說法,雖然佐證較多,但疑點(diǎn)仍然不少。還不能作為定論。伯禽封魯之后,淮夷、徐戎是否可能又起反叛,而魯公伯禽再次進(jìn)行征討?周穆王時(shí)是否有魯公伐淮夷、徐戎的記載?如果伐淮夷、作《費(fèi)誓》的是春秋時(shí)的魯僖公,那么作為魯國記春秋史實(shí)的《左傳》,為什么沒有詳載其事?這些問題,都需作進(jìn)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