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原文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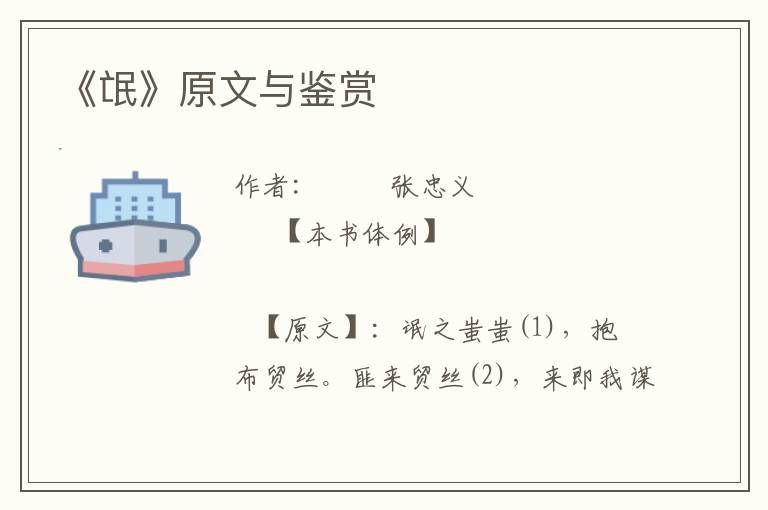
作者: 張忠義 【本書體例】
【原文】:
氓之蚩蚩(1),抱布貿絲。匪來貿絲(2),來即我謀(3)。送子涉淇(4),至于頓丘(5)。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6),秋以為期。
乘彼垝垣(7),以望復關(8)。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9),體無咎言(10)。以爾車來,以我賄遷(11)。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12)。于嗟鳩兮(13),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14)。士之耽兮,猶可說也(15)。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16),三歲食貧(17)。淇水湯湯,漸車帷裳(18)。女也不爽(19),士貳其行。士也罔極(20),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21)。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22)。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23)。總角之宴(24),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25)。
【鑒賞】:
《氓》是《詩經》中棄婦詩的名篇。通過一位婦女和氓從相識、相愛,到最終被冷遇、被遺棄的過程的敘述,反映了當時婦女在愛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
全詩共分六章。第一章寫氓向棄婦求婚,第二章寫二人相愛、結婚;第三章寫棄婦的悔恨;第四章寫棄婦的被棄;第五章寫棄婦敘說自己婚后的不幸,第六章寫棄婦對氓的怨恨。
《毛詩序》說:“《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敘其事以諷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詩集傳》說:“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這些見解,都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上對婚姻問題的裁判,顯然是荒謬的。詩中當“刺”當“諷”的,應該是當時吃人的禮教和氓那樣忘恩負義的流氓惡棍,而絕不是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的善良的婦女。
詩中描敘的棄婦是一位善良、勤勞而又忠于愛情的婦女。她把一顆純潔無瑕的心全部獻給了氓,而氓給予她的卻是欺侮和凌虐。“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是棄婦通過對自己愛情悲劇的深刻反思所總結出的沉痛教訓,也是對天下無數癡情者的善意忠告。
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說明,在當時的社會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就無怪乎先儒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棄婦為“淫婦”,初不自重,以色事人,華落色衰,卒被人輕了。也無怪乎棄婦的不幸遭遇非但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同情,甚至連自己的親兄弟也“咥其笑矣”。
事實上,棄婦對氓的愛情是從氓對棄婦的追求開始的。“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你看,氓在未得到棄婦愛情之時,他偽裝的是何等的虔誠。然而棄婦并未草率從命,甚至由于“子無良媒”而拖延了婚期。可見,棄婦在當時的禮教面前是不越雷池半步的,而并不象《毛詩序》中所說的“男女無別,遂相奔誘”。氓是以自己虛假的情誼騙取了棄婦對他甚篤的愛情。二人結合之后,棄婦“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其勞作之苦由此可見一斑。盡管如此,棄婦仍未擺脫自己被拋棄的命運,實在可悲可嘆。然而令人快慰的是,棄婦痛定思痛,終于還是下定了“亦已焉哉”的決心,這深刻表明,血淚的代價最終還是換來了人的覺醒。
與棄婦恰恰相反,詩中的氓是一個流氓式的反面形象。開始他佯裝買絲來與棄婦求愛,接著又卜又筮,儼然一副虔誠的面孔。但當其目的達到之后,便一改初衷,“二三其德”;繼而又翻臉無情,“至于暴矣”。其為人卑劣,心性之狡猾,皆為流氓惡棍所具有。
對這一丑惡形象的批判,詩中并無一句過激之辭,然而伴隨著女主人公如泣如訴的敘說,讀者莫不義憤填膺。
魯迅先生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氓》作為一篇現實主義作品,它深深地觸及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這樣的愛情悲劇在當時既有其典型性又有其普遍性,它反映了當時男女不平等、婦女受欺壓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
《氓》是一首敘事性較強的詩篇,可以把它看作我國詩歌史上早期的敘事詩作。全詩情節完整、形象鮮明,敘事和抒情有機結合、結構嚴謹、波瀾起伏。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此篇層次分明,工于敘事。‘子無良媒’而‘愆期”、‘不見復關’而‘泣涕’,皆具無往不復,無垂不縮之致。然文字之妙有波瀾,讀之只覺是人事之應有曲折。”(《管錐編》)。它對我國漢樂府中的著名敘事詩《孔雀東南飛》等恐也不無影響。
賦、比、興是《詩經》的主要表現手法。作為敘事詩的《氓》自然以賦為主,但在運用賦的同時作者又兼用比、興,這樣在表現手法上富于變化,增強了它的藝術性。如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喻女子年青貌美、二人情深意篤;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喻女子華落色衰,男子一改初衷。
總之,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表現手法上看,《氓》都無愧為我國早期詩歌的一塊碧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