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小山《招隱士》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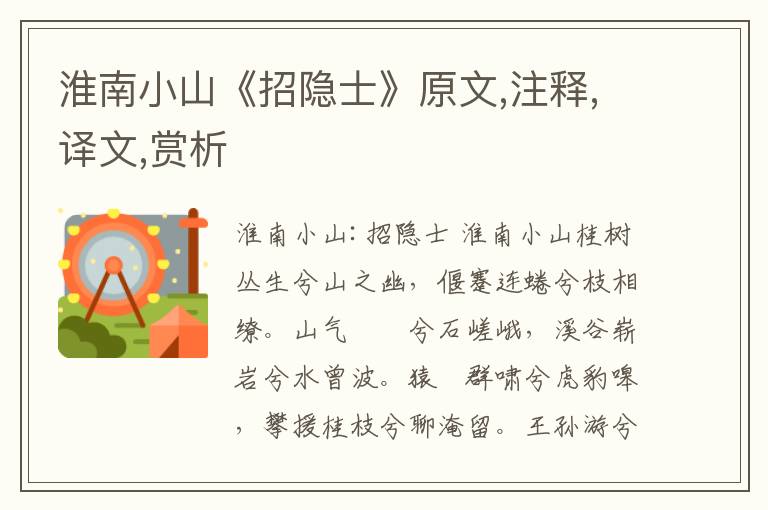
淮南小山:招隱士
淮南小山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巄嵷兮石嵯峨,溪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塽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僚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栗。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骩。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崯崯兮峨峨,凄凄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這篇作品為淮南小山所作,但據漢代王逸《楚辭章句》說,淮南小山并不是一個人,而是淮南王劉安賓客的總稱,也就是說,本文是由集體創作而成。所謂“招隱士”,究竟招的是誰?歷史上有兩種說法。一說招的是屈原,屈原雖投汨羅江而歿,然其聲名德行顯聞于世,與隱居山澤無異,故作此文,以章其志。一說招的是劉安,因劉安常到長安見漢帝,而朝中情況復雜險惡,賓客們怕他遇害,所以希望他不要在朝中久留。從作品的內容看,這兩種說法均屬牽強,它只是泛招隱居山澤之士歸來,并不特指某人或帶有象征寓意。
全文可分為兩大段。從開頭到“蟪蛄鳴兮啾啾”為第一大段,主要描寫隱士所處的山中景物及表示自己對隱士的思念。開頭六句,通過桂樹茂密、云氣郁蓊、山石高聳、溪谷險峻、水流迅疾、野獸吼叫的描繪,勾勒出一幅幽深險阻的山谷景象。作者描寫這些景物是深有用意的。桂樹,南方之珍木。其枝甘辛而香烈,非深山邃谷不生,故君子常以此比德而樂游其下。然幽深險阻之地,非君子之所處;猿狖虎豹之獸,更非君子之所偶。因而,山中不可淹留之意已於寫景中微微透出。接下去,“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嗚兮啾啾”四句,轉入招者之情的描寫。王孫,指隱士,秦漢以上,士多王侯之裔,故有是稱。蟪蛄,即寒螀,是一種蟬,夏秋時鳴。這幾句意思是說,王孫在山中淹留不出,令人從春到秋直至歲末,一直深切地思念他。
第二大段從“坱兮軋”起至全文結束,極言山中不可淹留之狀,以此勸王孫早日歸來。作者先以七句總述山中境況,說山路崎嶇,山勢高險,景色雖幽峻,但久處其中便會心神迷亂,再加上草叢深林,虎豹巢穴,更使孤游者目困心怵,顫顫自慄。接下去,分四個方面具體描述山中險幽之狀。“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是從山勢寫;“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骩”,是從樹木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是從雜草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崯崯兮峨峨,凄凄兮漇漇”,是從禽獸寫。寫山勢,則絕壁巉岏,如墜而壓然;寫樹木,則交錯糾結,如森寒相迫;寫雜草,則凌雜覆道,徑路難行;寫禽獸,則走住異趨,形狀奇殊。然后以野獸為喻,勸隱士下山。“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以下五句,包括兩層意思,前一層說即是猿猴熊羆也會因離群而悲鳴,故王孫孤處山中,必有人間之想。后一層說山上虎豹相斗,熊羆咆哮,禽獸驚駭失群。最后順勢而下,道出:“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這篇《招隱士》在藝術上有很多獨到之處。首先是描寫景物鮮明生動。作者通過細致的觀察,選擇了景物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加以描繪,因此,雖只寥寥幾筆,形象卻栩栩如生。如“坱兮軋”這一段中描寫的山勢、樹木、雜草、禽獸,在眼前就會浮現出高山崔巍、樹木繁茂、雜草遍地、猛獸爭食的畫面。其次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作品的大部分是寫景,抒情的筆墨極少,但無不感受到“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其原因在于采用了不正面抒情而讓感情由景物中自然透露出來的手法。如寫隱士居處,作者致力于山勢險峻,巖石傾危,雜草叢生,群獸交鳴等情景的描繪與氣氛的渲染,從而傳達出山中不可久留之意及招者迫切之情。這種在寫景中滲透著作者感情的表現方法,使得情因景而顯,景因情而深,令人有無窮回味。再次是語句配合感情而富有變化。全文從三字句到八字句,錯綜交雜,字句的變化完全是順著感情的變化而進行的。如第一段前六句描寫山中之景,用的是八字句,因而顯得非常舒緩,而到“王孫游兮不歸”四句抒情時,便用六字句,語句顯得短促,從而配合了懷思之切,招賢之急的氣氛。又如第二段寫山石險峻等情景,則以短句為主,因而詞氣緊湊,節奏急促,充分表達了山中不可久留的感情色彩。這種通過語句的長短來加強感情的起伏變化,正是作者藝術匠心的充分體現。朱熹指出:“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楚辭集注》)王夫之指出:“其可以類附《離騷》之后者,以音節局度,瀏漓昂激,紹楚辭之余韻,非他詞賦之比,雖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楚辭通釋》)可見歷來評價之高。
最后還應指出,這篇文章題為《招隱士》,寫殷盼隱士歸來之情,說明自古以來就有一批志行高潔、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知識分子,不愿競逐官場,同流合污,而隱遁于山林巖穴之中。他們有著強烈的山水意識、山水感情,“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山林之樂與廟堂之樂在他們看來,是完全對立的兩種人生、兩種情趣。他們這種近自然而遠世俗的思想行為和生活風尚,始終受到人們的敬重,視為高尚之士、峻潔之行,所以歷代統治者都企求征召隱士以美朝政。但是,真正的隱士寧肯老死于林泉之下,自甘清貧,也不愿入朝為官,供帝王役使。被稱為千古隱逸之宗的陶淵明便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毫無疑問,他們的志節在深化山水意識,促進人與自然的融合方面,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所以,從山水旅游文學的角度鑒賞這篇文章,可以啟發我們對隱棲之士的理解,加深人與自然密切相關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