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戲劇《孟漢卿·張鼎智勘魔合羅》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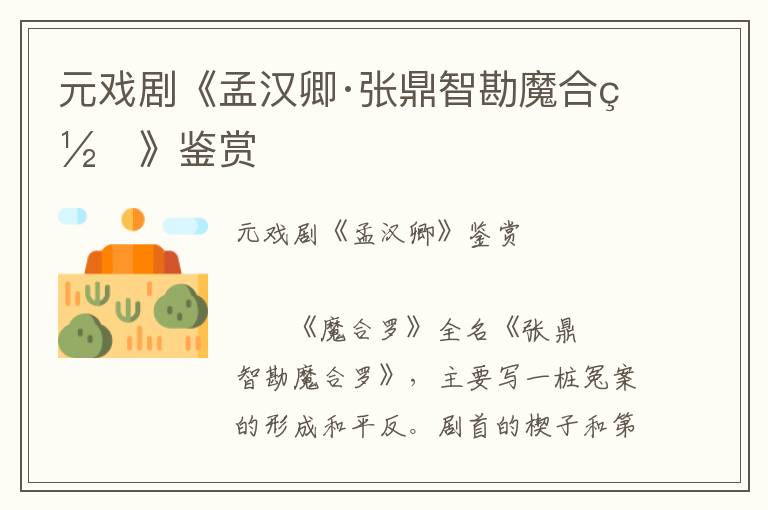
元戲劇《孟漢卿》鑒賞
《魔合羅》全名《張鼎智勘魔合羅》,主要寫一樁冤案的形成和平反。
劇首的楔子和第一、第二折寫冤案形成的經(jīng)過,第三、第四折寫冤案的重新審理和平伸。在河南府錄事司醋務(wù)巷居住的李德昌,平時開著個絨線鋪過活。一天他在長街市算了一卦,說他有一百日災(zāi)難,千里之外可避。他為躲災(zāi)避難,同時做些買賣,便挑了好日辰,辭別家對面居住的叔父李彥實及兄弟李文道、妻子劉玉娘和兒子佛留,往南昌去了。不久李德昌財增百倍,作商歸來,在城外五道將軍廟避雨時著涼染病,托賣魔合羅的老頭高山給妻兒捎信。其弟李文道從高山口中予知詳情,搶先跑至廟中,以給兄長治病為名,用毒藥將李德昌藥昏,盡掠其財而去。李德昌被子接回家中,七竊流血而死。李文道早就對嫂嫂劉玉娘有不軌之心,現(xiàn)在趁機誣蔑劉玉娘通奸害夫,逼其允婚。劉玉娘寧死不肯給他做老婆。官司打到官府,縣官是個只愛錢鈔不管事的人,推給蕭令史去審。蕭令史當(dāng)場接受李文道五個銀子的賄賂,把劉玉娘屈打成招,判為死罪。新到府尹雖有為民作主之心,但在提審劉玉娘時,因這個女囚口稱“小婦人無有詞因”而判一“斬” 字,同意將其“押出市曹殺壞了者” 。劉玉娘的冤案就這樣草率鑄成,只差項上一刀了。
就在劉玉娘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刻,掌管六房事務(wù)的六案都孔目張鼎,奉府尹臺旨勸農(nóng)歸來。此人官職不算大,責(zé)任心很強,深知自己“身擔(dān)受公私利害,筆尖注生死存亡” ,這是他辦案認(rèn)真負(fù)責(zé)的思想基礎(chǔ)。府尹早就了解到他是個“能吏” ,在他匯報完樁樁清楚無弊的文卷之后,便與他十個免帖,給他十日假期,以示關(guān)懷。劉玉娘的案件是他下鄉(xiāng)勸農(nóng)期間審理的,本與他無關(guān)。但他出于為民伸冤的責(zé)任心,還是主動插手這一案件之中。
作者先寫張鼎對劉玉娘冤情的覺察。張鼎勸農(nóng)歸來后拿著幾宗合僉押的文書送府衙相公僉押(簽發(fā)批準(zhǔn)) ,看見如虎似狼的公人推擁著一個愁眉淚眼、血污衣裳、身耽棒瘡、帶鎖披枷的待報的“犯婦” 。他看到此婦“眼淚不住點兒流下” ,又根據(jù)古人所說“存平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的經(jīng)驗之談,一個感覺涌上腦際: “受刑的婦人,必然冤枉” 。這一心事使他放慢了腳步,拉遲了行速。當(dāng)他 “轉(zhuǎn)過兩廊” 、“行至稟堂”時,張千叫那“犯婦” 向他這位“孔目哥哥”呼救,犯婦“緊拽定”他的衣服不放,他便停下來向犯婦問明詞因,并答應(yīng)替犯婦“相公行說去” 。可是他向府尹匯報完自己經(jīng)手的文書后轉(zhuǎn)身便走,準(zhǔn)備回家休假,只字末提劉玉娘的事。這決不是他的健忘,也不是他思想動搖,而是他的機智表現(xiàn)。因為此案府尹所判“斬”字墨跡未干,又與他毫無關(guān)系,他卻出來過問,不能不費一番腦筋。當(dāng)張千向他提醒劉玉娘一事未稟時,他沒有絲毫猶豫的表示,轉(zhuǎn)回身向府尹稟道: “恰才出的衙門,只見稟墻外有個受刑婦人,在那里聲冤叫屈,知道的說他貪生怕死,不知道的則道俺衙門中錯斷了公事,相公試尋思波” 。本來他見劉玉娘是在他進衙門時,他現(xiàn)在卻說“出的衙門” ,這變“進”為“出” ,說明他第一次見府尹不提劉玉娘一案不是健忘,更不是動搖,而是有意為之,為的是自己干予此案不讓府尹感到“多管閑事” 。張鼎深知衙門經(jīng)常錯斷公事,“扭曲作直,舞文弄法,只這一管筆上,送了多少人也呵” 。但他向府尹說的這番話卻從維護衙門聲譽出發(fā),好象唯恐衙門錯斷了公事造成不好影響才過問此案,而不是為犯婦鳴冤過問此案,這就使府尹容易接受他的復(fù)審建議,這正是他機智的表現(xiàn),是他富于翻案經(jīng)驗的表現(xiàn)。新府尹說明此案乃“前官斷定,蕭令史該房” ,實際有推托己任、對張鼎重提此案不大高興的意思在內(nèi)。張鼎不好和新府尹爭辯,責(zé)問蕭令史: “我須是六案都孔目,這是人命重事,怎生不教我知道?”蕭令史以他出外勸農(nóng)為借口給自己獨斷此案辯護,張鼎并不讓步,要來狀子細(xì)看,發(fā)現(xiàn)其中漏洞百出: 李德昌做買賣的銀子不見下落,李德昌托付給妻子寄信的人沒有下落,李文道所告發(fā)的劉玉娘的奸夫沒有下落,合毒藥的人沒有下落,合謀的人沒有下落。他的這些擊中要害的發(fā)現(xiàn)使府尹為之松動,使令史無言抵賴。他又指出: “人命事關(guān)天關(guān)地,非同小可” ,“這為官的性忒剛” ,“為吏的見不長” ,“這一樁公事總荒唐” ,“可怎生葫蘆提推擁他上云陽?”張鼎這些話本來是責(zé)備斷定此案的前官和該房的蕭令史,可蕭令史為了挑撥張鼎和新府尹的關(guān)系、逃脫罪責(zé),當(dāng)場在新府尹面前誣蔑張鼎罵新府尹葫尹提,這一點新府尹不會不知,但他卻接過蕭令史之言,“責(zé)怪”了張鼎一番之后,命張鼎三日之內(nèi)問成此案,若問不成,定斬不饒。這種作法既可遮掩剛才的失誤和輕率,又可使自己有臺階可下,彎子轉(zhuǎn)得自然,而教令史無話可說,信以為真,還可讓張鼎復(fù)審此案,可謂一箭三雕,這又是新府尹清明和機智的表現(xiàn)。至于張鼎審成與否,均與他無礙,亦可謂作官之狡。可是張鼎卻一下未體會出此中奧妙,后悔自找麻煩,自招“不是”。但這后悔淹沒不了他救善懲惡、“直教平人無事罪人償”的正直之心。
他先提審劉玉娘。命張千為劉玉娘松綁,審問玉娘詞因。因案子已過一年,再加上案情發(fā)展蹺蹊,劉玉娘只知冤屈,什么也回答不上來。張鼎便從各方面啟發(fā)她: “則問你出城時主何心?則他入門死因何意?”那位送信人,“莫不他同買賣是新伴當(dāng)?” “莫不是原茶酒舊相知?他可也怎生來寄家書,因甚上通消息?” “那廝身材是長共短?肌肉兒瘦和肥?他可是面皮黑面皮黃?他可是有髭髟無髭髟” “莫不是身居在小巷東?家住在大街西?他可是甚坊曲甚莊村?何姓字何名諱?”“莫不是買油面為節(jié)食?莫不是裁段匹作秋衣?我問你為何事離宅院?有甚干來城內(nèi)?”張鼎深知那個送信人對于此案的重要,或者更確切些說,他甚至認(rèn)為李德昌就是送信人害死的,所以他從捎信人與李德昌的關(guān)系、外貌、住址、職業(yè)等方面啟發(fā)劉玉娘的記憶,但均未湊效。他不灰心,又想從送信時間上打開缺口,便隨意問張千: “明日是甚日?”張千回答“明日是七月七” ,這一下,啟發(fā)劉玉娘記起“當(dāng)年正是七月七,有一個賣魔合羅的寄信來,又與我一個魔合羅兒。”
接著,張鼎提審魔合羅。“魔合羅,是誰圖財致命?李德昌怎生入門就死了?你對我說咱” 。“你曾把愚癡的小孩提,教誨教誨的心聰慧,若把這冤屈事說與勘官知” ,“不強似你教幼女演裁縫,勸佳人學(xué)繡刺。要分別那不明白的重刑名,魔合羅全在你。你若出脫了這婦銜冤,我教人將你享祭,煞強如小兒博戲” 。“魔合羅,你說波,可怎不言語? 想當(dāng)日狗有展草之恩,馬有垂韁之報,禽獸尚然如此,何況你乎?你既教人撥火燒香,你何不通靈顯圣,可憐負(fù)屈銜冤鬼,你指出圖財害命人。”可是他審來問去,魔合羅卻無動于衷,“不起一點朱唇說是非。”張鼎于是責(zé)怪魔合羅: “枉塑你似觀音象儀,怎無那半點兒慈悲面皮! 空著我盤問你,你將我不應(yīng)對”。此劇中的魔合羅,本是雕塑的觀音大士,七月七婦女、小孩用來 “乞巧” (請求織女提高其紡織刺繡等技巧) 的,它既不會言語,更不通人性,而赫赫有名的能吏張鼎卻一本正經(jīng)、煞有介事地審問起它來,看來似乎過于滑稽,實際上從審問魔合羅的內(nèi)容看,她是用此滑稽方法從側(cè)面啟發(fā)劉玉娘思考回憶,使她那因為受重刑蒙深冤而萎糜的精神在審問魔合羅的滑稽場面下活躍起來,使她那因為冤、痛重壓而失去的記憶重返腦際。他企圖從正面、側(cè)面啟發(fā)劉玉娘,從她那里了解捎信人的線索,沒有如愿,卻在“徹上下,細(xì)觀窺”魔合羅時,意外地發(fā)現(xiàn)魔合羅底座兒下雕有“高山塑”的字樣。原來這魔合羅是送信人高山為向李德昌表明自己不負(fù)其托,捎信至家,留給劉玉娘兒子佛留的證見。
張鼎滿以為送信的高山就是“殺人賊” ,喝命張千把高山“一步一棍打?qū)怼?。高山雖遭痛打,就是不承認(rèn)害死李德昌。張鼎在追問他捎信途中撞著誰時,高山招出賽盧醫(yī)李文道。張鼎從劉玉娘口中得知李文道與她雖為叔嫂,卻素不和睦,以此判斷害人的是李文道而不是高山。但他為了維護孔目的尊嚴(yán),卻命打了高山八十,搶了出去,理由是“不應(yīng)塑魔合羅” 。實際上正是高山所塑魔合羅在審案中幫了他的大忙,按理他應(yīng)該感謝高山才對哩! 這正是他這個清官不清的地方。張鼎審問李文道與審問劉玉娘和高山不同,他假稱: “老相公夫人染病,這是五兩銀子,權(quán)當(dāng)藥資,休嫌少” 。李文道不知是計,把隨身帶的藥讓張千拿給老夫人吃。一會兒,張千來報: “老夫人吃了藥,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 。李文道向張鼎求救,張鼎提出條件: 要求李文道舍老子以救自己; 在張鼎審問“誰合毒藥來” 、“誰生情造意來” 、“誰拿銀子來”等問題時,李文道必須一一回答“是俺老子來”,“并不干小的事”。李文道滿口答應(yīng)。張鼎命張千把李文道老子李彥實“一步一棍打?qū)ⅰ?來。
張鼎見了李彥實,劈頭一句: “你孩兒李文道告你” 。李彥實不信,張鼎大著嗓門向押在司房里的李文道發(fā)問: “誰合毒藥來?” “誰生情造意來?” “誰拿銀子來?”李文道毫不猶豫地一一答應(yīng),“是俺父親來” ,“并不干我的事” 。李彥實聽見李文道咬住自己不放,一氣之下說出兒子殺死哥哥的真情,并畫了字,等到兒子從司房中放出,父子相見,方知中計,后悔莫及。在這里,張鼎用的計謀雖似有“詐”,但卻沒有冤枉李文道。原因有二: 一是李文道為求活命,寧愿犧牲八十歲老父親,說明此人無骨肉情分,心腸殘忍,更不會把叔輩哥哥放在眼里; 二是張鼎所假說的老夫人服藥后七竅流血而死,與李德昌七竅流血而死一樣; 當(dāng)著李彥實的面向在司房中不露面的李文道所提問題與李德昌一案的要害問題一樣,很容易在父子反目的情況下觸發(fā)李彥實對李德昌被害一事的揭發(fā)。如李文道無殺兄之事,李德昌不會馬上招出兒子圖財害命的罪惡。因此張鼎所用之法貌似有“詐” ,實則不會冤枉惡人。
總之,此劇寫張鼎審案雖只用了兩折戲的篇幅,但把此人關(guān)心民命、機智老練的特點卻寫得生動深刻。審劉玉娘、審魔合羅、審高山、審李文道、審李彥實,方法各異,曲折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