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殘酷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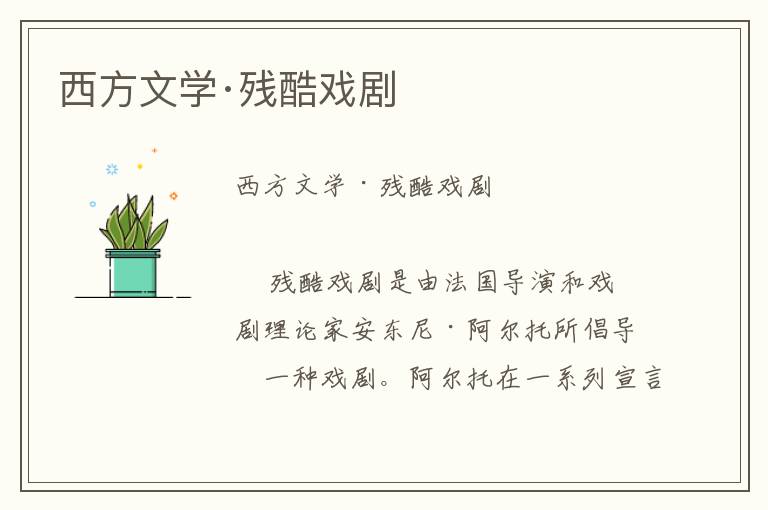
西方文學·殘酷戲劇
殘酷戲劇是由法國導演和戲劇理論家安東尼·阿爾托所倡導的一種戲劇。阿爾托在一系列宣言中,激烈反對以對白為主的僵化的心理戲劇,而提倡一種由東方儀式戲劇注入生氣的戲劇。阿爾托開始明確形成自己的戲劇觀念是在1931年,當時他在巴黎的殖民地展覽館親眼目睹了巴厘舞蹈。寓言性的面具,異國情調和演員的風格化的姿勢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10月,阿爾托在《法蘭西新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殘酷戲劇》的第一個宣言,綱要性地陳述了有關一種總體戲劇的理論。他希望戲劇不僅通過大腦的理智而且通過器官的感覺深入地打動人。阿爾托認為戲劇場而應是一種儀式,傳統的以性格描寫和對生活枯燥的模仿為主的文學性和心理學的戲劇將被推翻,應借助視覺上、音響上令人震驚的具體表現在舞臺上的意象、奇想、怪物,和對文本的咒語般的復誦這些訴諸感情而非訴諸理性的東西,來揭示人的命運,普遍的哲理,阿爾托希望借助戲劇化的魔術般的儀式,把戲劇提高到一種宗教儀式的水平。他認為人的行為就是轉變成形式的觀念,人的姿勢揭示出一種意識的現實或者一種形而上的意圖,人的行為與人的觀念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同。所謂殘酷,并非是指折磨,血腥味。在他看來,殘酷主要是指演員和劇作家由于嚴厲地審視和喚起了在人和世界的最內在的存在中所發現的令人害怕的力量而經受痛苦,也是指觀眾殘酷地經受痛苦,這些觀眾在肉體上受到視覺的和音響的意象襲擊,被迫放棄文明化的西方精神,從而發現自己與真實然而討厭的自我相遇。阿爾托希望恢復戲劇動作固有的多義性,創造一種動作的語言、姿勢的語言,打破僵化的理智,于是言詞變得多余了,因為演員的姿勢能夠喚起人的本能的感情,具有風格化形式的藝術能達到每個人各有的內心深度,他認為,犯罪傾向和色情傾向也能被真實地處理。而不必考慮時代的道德觀; 而為了體驗真實的感情,觀眾必須在情感上介入構成事件或事變的戲劇動作。總之,阿爾托希望創造一種集體精神錯亂,甚至一種肉體上的震驚,以便揭示一切戲劇動作基礎的根本上的殘酷。這種殘酷是人必須完全屈從之的命定論的殘酷,是罪惡的永存,愛情的吞沒力量的永存,性欲的永存和死亡的永存。
殘酷戲劇實質上是一種形體戲劇,它企圖通過人的感官深入人,以便揭示人、社會、自然和客體的有機聯系。這樣一種戲劇的基本觀念當然包含了導演作用的新觀念和舞臺技巧的新觀念。在他看來,這不是一個技巧上的問題,而是喚醒觀眾的人生意識的一系列步驟,藝術與生活決不會分離。為了使戲劇具有新的活力,應讓舞臺面即舞臺布景和動作處于優越地位,而不是劇本文本,言語必須成為空間的詩,姿勢必須具有不同于言詞的獨立意義。藝術家必須運用區別于其他藝術的舞臺的獨特要素來創造他自己的形式,而且要運用與舞臺有關的一切手段,如繪畫、舞蹈、姿勢、運動、物體、色彩、聲響、燈光,使戲劇成為一種揭示性藝術而不是裝飾性藝術。這樣,每一種思想和感情就會在舞臺上有一種空間存在,成為一種可以精確地閱讀的符號和交流信息。同時,阿爾托的戲劇觀念還要求新的戲劇空間觀和新的演員與觀眾關系觀。阿爾托希望觀眾參與戲劇,處于戲劇的總體會環境中,這樣更有利于演員與觀眾的交流。
在1933年發表的有關殘酷戲劇的第二個宣言中,阿爾托希望戲劇揭示現代的激情和焦慮,尤其是社會騷動和種族沖突。戲劇應對全部的人說話,而不是對被宗教和文明弄得畸形的單薄的心理的人說話。
雖然阿爾托的戲劇理論在其生前并未獲得成功,他的《欽西》僅上演了7次就被人忘卻了,但他對使存在意識成形的方法的探討卻鼓舞了許多先鋒派導演和劇作家,諸如佩特·魏斯,佩特·布魯克,讓·路易斯·巴羅,羅歇·布林,讓·冉奈,阿爾索爾·阿達莫夫、弗爾南多·阿拉巴爾,以及羅曼·魏恩加爾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