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橋》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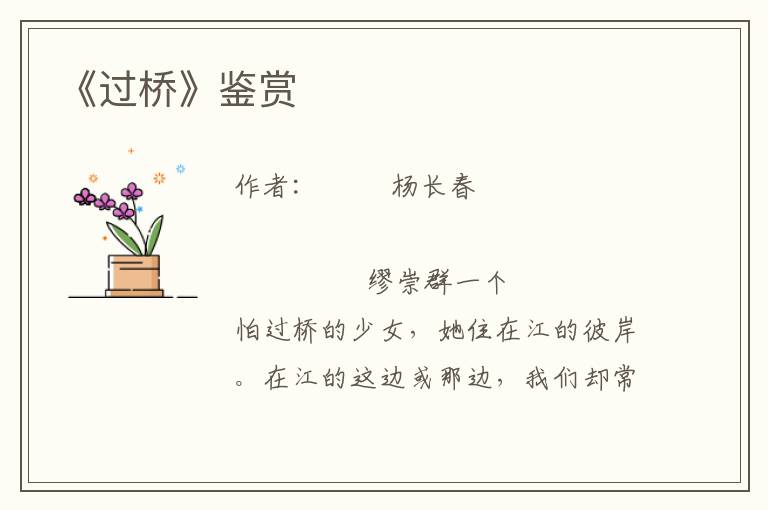
作者: 楊長春
繆崇群
一個怕過橋的少女,她住在江的彼岸。
在江的這邊或那邊,我們卻常常會見,記不清誰從橋上過來,誰從橋上過去。
那邊有油綠的原野,和青螺般的峰巒,這邊有鬧市,有商店,有齊整的城垣。
輕輕地詛咒它,這橋,正橫在我們兩者之間。
默默地感謝它,這橋,也是連系著兩邊的一條線。
用喜懼與憂患捻成的線,悄悄地它會穿過了我們心靈的眼。
我喜歡這個怕過橋的少女,因為她是天真而沒有一點邪念。我喜歡橋,橋通著彼岸。或者更多的純真的少女們也住在彼岸。
橋的影子投在江上,任憑那些嗚咽著的,奔騰著的,象無數生命似的波流吻它,它不作一聲語言。
橋的影子映在雨過的天上,那是一條彩虹,象征了它的光明與燦爛。
我認識了真理,真理住在光明里。
我認識了橋,橋是被真理砌成的一面。
橋永遠連著兩岸,真理使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接近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
橋,作為此岸和彼岸之間的聯系物,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意象。
江或河隔斷了世界,于是便有了岸與岸的隔膜、對峙、對立。其實在現實世界中,這對立何止僅僅存在于岸與岸之間。作為一個認識主體,就“我”而言,那些“我”不能認識、不能理解、不能交流的外部世界何嘗不是“我”的對立面。雖然它們是美好的,雖然它們對“我”而言充滿魅力,但它們卻與“我”毫不相干。擴展自身是人類的一種天性,而發展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了解未知的東西,變異已為自我的一部分,建立起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這個過程,也正與過橋相似。
被阻隔的兩岸遙遙地對立著,一個個獨立的個體陌生地遙望著。聯系起它們的,只能是橋或橋一類的東西。兩岸之間有形的橋是用磚砌成的,而那些看不見的橋,譬如溝通“我”與外部世界、聯系著心靈與心靈的橋是用什么砌成的?“我”最后認識到,那“是被真理砌成的一面”——是真理使“我”認識了萬物,是真理溝通著人們的心靈。我們要了解世界、獲得世界,只有沿著真理的橋梁去接近它們。
這雖不是一篇情緒性散文,而是重在表現一種哲理性思考。但是卻也有“情”的投射。作者找到了一種很準確的意象——“過橋”——來表達他的感悟,作品中“我”和那位少女隔江相望、過橋相會的故事使“過橋”這一意象變得更加豐滿具體,哲理中也就滲入情感的汁液;而結尾處高度概括的語言則使這種思考進一步明朗化:“橋永遠連著兩岸,真理使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接近了。”猶如明燈高懸,照徹了全篇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