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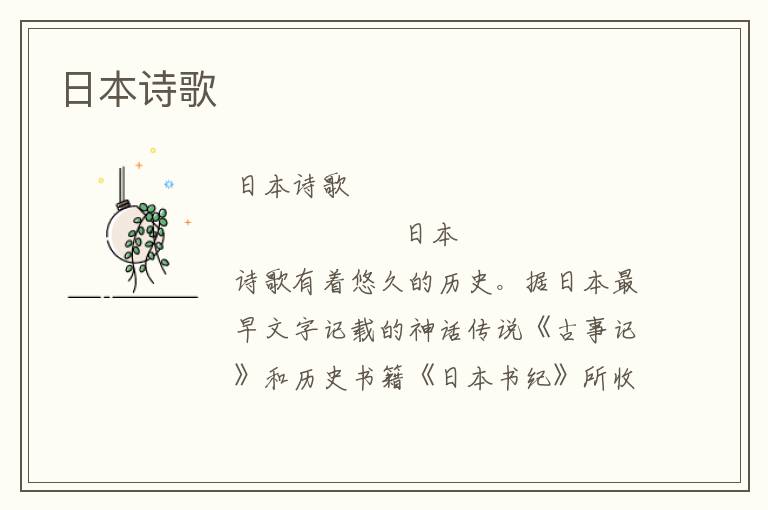
日本詩歌
日本詩歌有著悠久的歷史。據日本最早文字記載的神話傳說《古事記》和歷史書籍《日本書紀》所收集的歌謠,早在4世紀末5世紀初,日本人就在祭祀、勞動及酒宴之際,采用相對固定的形式吟歌娛樂抒發情感。這種相對固定的形式經過數十代“無名詩人”的不斷完善,形成了日本詩歌的基本格律——五七句式(即各種類型的格律詩歌都是由5個和7個假名構成的詩行相互交替吟詠)。例如早期詩歌中的片歌歌體為“五七七”,四句歌為“五七五七”或“七五七五”,旋頭歌為“五七七五七七”,佛足跡歌為“五七五七七七”,短歌為“五七五七七”,長歌則為“五七五七……五七七”。這種早期詩歌格律受歷代日本詩人的喜愛,一直延用至今,形成了日本詩歌的基本格律。
日本詩歌,從廣義上講,除長歌、短歌、旋頭歌等格律詩外,還應包括日本詩人創作的大量漢詩(中國格律詩,但因本條目范圍所限,在此不作討論)和近代自由詩。然而,和歌是最具體表性的格律詩。
一、古代前期的詩歌(公元794年以前)
“記紀歌謠”
7世紀中葉的大化革新,推動了日本歷史的發展。這場變革,結束了舊有的“氏姓制度”,建立了日本第一個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奈良時代初期的和銅5年(712),日本文人奉敕撰集成了現存最早的典籍《古事記》,時隔8年又撰集出了《日本書紀》。所謂“記紀歌謠”,是專指收錄在這兩本典籍中的200余首歷經數百年廣泛流傳的民間歌謠。作為官撰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明顯帶有歌頌和神化國家締造者的色彩。其中的歌謠也只是為了襯托與天皇有關的神話和傳說而被編選的。不難想象,在當時的民間,人們相互吟詠抒發情感的與史書無關的優秀歌謠,在數量上遠遠超過“記紀歌謠”。遺憾的是那些表達上古日本人真實情感的歌謠終未變成文字,如朵朵雪白的云團消失在碧藍的天空。
口傳時代的歌謠除“記紀歌謠”外,在其他典籍中也偶有發現。如《風土記》中收有13首,《古語拾遺》中有1首,《佛足跡歌碑》中有21首,《琴歌譜》中也有21首。現存的上古歌謠雖數量不多,卻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同時也反映了早期日本民族雄健向上、樸實美好的人生理想。
上古歌謠在修辭方面,已運用了對句、序言、反復和枕詞(一般與歌意并無關系的墊詞)等手段。從文學的角度看,大部分歌謠還嫌稚拙,但也正是這種稚拙往往產生出良好的感人效果。
現存的上古歌謠,在五七句式上顯然經過了編選者的加工。同時正因為有了這種完善和加工,才奠定了后來日本詩歌——和歌的基礎。
《萬葉集》
《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全集20卷,共收和歌4500余首。其中長歌約260首,短歌約4200首,旋頭歌60首,連歌1首,佛足跡歌1首。其成書年代眾說不一,但日本學術界基本認定,此書經多次編輯,最后是在奈良朝末期的760年由大伴家持(718—785)總匯而成。
《萬葉集》所收集的和歌全部借用中國漢字寫成,所借用的漢字又通稱為“萬葉假名”。其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借用漢字的音,用近似日語發音的漢字,一個漢字表示一個音;二是將漢字當外來語使用,只用其義不用其音。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日本上古時代尚無自己民族的文字,后隨中國文化、律令及佛教的傳人,作為載體的漢字漢文及漢譯佛經一并傳人日本,使漢字充當了記述歷史文化的工具。
和“記紀歌謠”相比,《萬葉集》所收和歌,大都有明確的作者。因此,萬葉和歌有著鮮明的個性和藝術特色。作者階層上自天皇、皇妃、皇子、貴族、大臣、官吏,下到一般庶民——農民、士兵、乞丐,乃至妓女等。作品有署名的和不署名的。署名的作者大都是皇族、貴族及宮廷專業詩人,總數達500余人。從地域性來看,集中所收作品以當時的國都奈良為中心,東至東部日本,南達九州一帶。作品的吟詠年代,自4世紀到8世紀,前后跨度約450余年。
全集作品的創作年代有其自然形成的特點,按其特點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為壬申之亂(672)前。這一期間的作品除10多首帶有濃厚“記紀歌謠”風格的之外,大部分是飛鳥近江時代的。詩歌已基本定型為五七句式。詩人主要是天皇和皇族,以舒明(593—641)、天智(614—671)天皇及額田王(鏡王的二女兒、受寵于天武天皇,是當時惟一的女歌人)為代表的詩人,著眼于大化革新到壬申之亂期間動蕩不安的社會現狀,將自己的感受吟作雄健質樸且富于感染力的詩歌。第二期自壬申之亂至遷都奈良(710)。在此期間涌現出了一批專業宮廷詩人。主要代表有柿本人麻呂(生卒年不詳)和高市黑人(生卒年不詳)。他們在擴大詩歌創作題材、完善和歌韻律、增強詩歌語言的文學色彩方面做出了不朽的業績。第三期自遷都奈良到天平5年(733)。此時期萬葉詩歌發展到了頂峰,作品個性鮮明,題材多樣,意境深廣。山部赤人(生卒年不詳)的寫景詩,大伴旅人(665—731)的純情詩,山上憶良(660—約733)的人生詩以及高橋蟲麻呂(生卒年不詳)的以傳說為素材的詩歌為萬葉詩歌增添了綺麗色彩。第四期自733至759年,這是萬葉詩歌由鼎盛走向衰落的一個時期。和歌失去了以往直面人生、詠唱現實的風格,取而代之出現了大量純娛樂純感傷的詩歌,但大伴家持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在詠唱郁悶、焦躁和感傷心情方面,筆調細膩,情感柔和,開創了自己獨特的詩歌天地。
由于《萬葉集》不是一次編成的,編輯體例很不統一。雖大體可分為雜歌、相聞和挽歌三大類,但有些卷本卻又按表現方式分為正述心緒歌、寄物陳思歌和比喻歌。
《萬葉集》中收有數百首“東歌”和“防人歌”。這些詩歌大都采集于日本東部地區。“東歌”帶有濃厚的民歌色彩,樸實地反映了庶民的生活情感。“防人歌”主要是長年守衛在邊疆的將士所作的歌,其中有情歌和思鄉歌。大部分詩歌,內容健康,風格樸實,屬《萬葉集》中獨放異彩的詩篇。
二、古代后期的詩歌(794—1192)
《古今和歌集》
《古今和歌集》于延喜5年(905),由紀貫之(卒于945年)等四位詩人奉醒醐天皇之敕命編集而成。作為日本最早的敕撰和歌集,意義十分重大。全集20卷,載和歌約1100首。
古今集所收歌的創作年代前后跨度達150年,按其風格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無名詩人時代。整個歌集中以“作者不詳”而出現的和歌約占百分之四十之多。其中的大部分和歌,主要創作于《萬葉集》向古今集的過渡期。其風格依然保留著萬葉詩歌所具有的質樸和真率,斷句方式也保留著被稱為萬葉調的“五七調”。第二期稱六歌仙時代。即以遍昭(816—890)、在原業平(825—880)、文屋康秀(生卒年不詳)、喜撰(生卒年不詳)、小野小丁(生卒年不詳)、大友黑主(生卒年不詳)六位和歌詩人為代表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和歌已逐步形成了貴族意識細膩流暢的風格,注重表現技巧,改“五七調”為“七五調”,產生了更加優美的韻律效果。第三期為撰集者時代。此時期的作者善于用自己的趣旨和感受捕捉素材,巧妙利用優美的“七五調”及“緣語”“掛詞”(諧音)“比喻”等手法,加之運用了疑問和推量詞語的語言表達方式,大部分和歌曲折委婉、耐人尋味。在全歌集中,僅撰集者所創作的和歌就占五分之一。這一時期的和歌風格在古今集中最具代表性。
《古今和歌集》的編纂使日本的傳統和歌作為公開文學得以復興。同時也使婦女之間長期孕育的“假名”變成了公開通用的日本文字。
《古今和歌集》雖然復興了《萬葉集》所形成的傳統和歌,但其風格卻與萬葉詩歌大相徑庭。古今集的作者主要是宮廷官吏,和歌內容缺乏廣泛的現實生活,過于偏重趣味性。
《古今和歌集》的序文用“假名(日文)”和“真名(漢文)”兩種語言寫成。它是日本有關和歌的最早的歌論文章,對后世日本和歌的發展長期發揮著指導作用。
作為有影響的古代和歌集,除《古今和歌集》外,還有《后撰集》(951年,1426首)、《拾遺集》(1005年,1351首)、《后拾遺集》(1036年,1220首)、《金葉集》(1126年、712首)、《詞花集》(1151年,413首)、《千載集》(1133年、1287首)、《新古今和歌集》(1205年,1981首),一并被譽為“八大和歌集”。
三、中世紀詩歌(1192—1603)
12世紀末葉,日本新興的武士階級取代了沒落的貴族階級在鐮倉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但由于古代天皇制依然存在著可利用的價值,所以武士階級在掌握政治實權的同時,繼續擁立幼小的后鳥羽為天皇。后鳥羽天皇成人之后,深感自己肩負著復興王政的使命。他著眼于傳統文化即和歌的振興,創立了日本和歌史上最為盛大的“后鳥羽院歌壇”,頻繁舉行歌會和歌合(一種和歌比賽)。這種賽歌活動一方面推出了眾多優秀歌人,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和歌及和歌理論的發展。作為“后鳥羽院歌壇”最初導師的俊成入道(1114—1204)為和歌事業做出了畢生的貢獻。他所著述的《古來風體抄》被譽為日本最早的和歌史書。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俊成之子定家(1162—1241)繼承了父親的事業,于元久二年(1205),在后鳥羽院的敕令下,與通具(1171—1227)、有家(1155—1216)、家隆(1158—1237)、雅經(1170—1221)、寂蓮(卒于1203年)五位歌人編集成了輝煌的《新古今和歌集》。
《新古今和歌集》
《新古今和歌集》共20卷,收歌1901首,全部為短歌。全集分春、夏、秋、冬、賀、哀傷、離別、羈旅、戀、雜、神祇、釋教十二類。部首附有“假名”“真名”兩種文字撰寫的序言。
《新古今和歌集》與《萬葉集》《古今和歌集》并存,形成了和歌世界的三大星座,同時也是一部經過升華提煉為最優美的和歌集。作為后鳥羽院的敕撰集,集中收有大量表達政治抱負的王政復古思想的作品。這些作品形成了新古今集的一大特色。歌人們為表達自己多樣的浪漫主義意象,采用了客觀具體的象征主義表現手法,但就其本質來說,他們抒發的決不是對現實社會或實際生活的感受和情懷,而追求的是綺麗而無章的風景,虛無縹緲的旋律,妖艷凄迷的美女容貌以及思慕王朝的戀情。他們崇尚佛教的凈土思想,推行藝術至上主義,沉湎于不問世事的唯美境界中。新古今和歌超現實的繪畫美和物語情趣,在整個日本和歌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在中世紀的四百余年間,和歌集除以《新古今和歌集》為代表的14部敕撰集之外,還有私家和歌集。有代表性的如被稱為“鐮倉石大臣家集”的《金槐和歌集》(1213年,663首),收歌1萬首的《草根和歌集》(1459年以前)。
連歌
連歌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萬葉集》,平安朝(794—1192)中期的《拾遺集》和《金葉集》中也有收集,但都是些兩聯句的短連歌。進入中世紀,連歌才逐步得以完善。連歌活動最初只在上層社會和專業歌人之間進行,后來經過宗祗(1421—1502)和山崎宗鑒(1460—約1540)等幾代歌人的不懈努力,才逐漸使連歌庶民化。但隨著連歌活動的普及,其文學價值也逐漸降低、后來幾乎成為一種純娛樂的消遣活動。
作連歌需把一首短歌分為長(五、七、五).短(七、七)兩句。長連歌的基本形式為百韻,即第一句用稱為“發句”的長句,第二句用稱作“脅句”的短句,然后第三句長、第四句短,依次聯句至100句;另外還有歌仙(36句)、世吉(44句)、50韻、千句(百句十卷)、萬句(千句十卷)等形式。作長連歌原則上需要幾人或十幾人,但也有獨吟的。因此,一個人吟唱稱“獨吟”,二人稱“兩吟”,三人稱“三吟”。
具代表性的連歌集有《菟玫波集》(1356年,藤原良基主編)、《水無瀨三吟》(1488年,宗祗及其弟子作)、《新撰大筑波集》(約1523年,山崎宗鑒編集)。
四、近世詩歌(1603—1868)
俳諧(后稱俳句)
17世紀初葉,德川家康統一了諸侯割據近百年的分裂局面,于1603年在江戶(今東京)設立了幕府,史稱江戶時代。始于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進入江戶時代后再次得到了鞏固,鎖國政策的推行以及幕藩封建制的建立,近世特有的文化得到了發展,文學的平民化便是一大特征。
俳諧源自中世紀的俳諧連歌,山崎宗鑒和荒木田守武(1473—1549)便是俳諧連歌的大師。寬永(1624—1644)年間,俳諧在當時的連歌、歌學權威松永貞德(1571—1653)的倡導下,很快得以盛行。貞德于1651年編著了《御傘》,書中制定了俳諧的規則,從而使俳諧真正從連歌獨立開來,開辟了俳諧的新紀元。但貞德并不認為俳諧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他只把俳諧放在通向和歌和連歌的階梯位置。以貞德為代表的“貞門”派雖確立了俳諧的文學地位,但終因過于拘泥形式(規則),未能使俳諧得到發展。而以西山宗因(1605—1682)為首的“談林”派,開展了俳諧的革新運動,強調俳諧的滑稽性,主張創作上的自由奔放。他們無視貴族式的傳統權威,使俳諧真正變成了平民的文學。但因“談林”派在打破傳統上操之過急,很快使俳諧陷入輕佻游戲的泥潭。
正當“談林”派所主張的俳諧走入死胡同之際,俳諧界出現了一位才華橫溢的新秀——松尾芭蕉(1644—1694)。芭蕉身為下級武士,20歲時在京都鉆研俳諧。在初期深受“貞門”和“談林”風格的影響,但他更著重探討人生,觀察自然,很快便確立了閑寂高雅的俳諧風格。芭蕉的成功在于他將中世紀以來的詩歌傳統融于新興的平民藝術,并使之發揚光大。芭蕉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旅行中度過的。旅行培養和磨練了他的詩心,同時,也為他的創作帶來了取之不盡的素材。芭蕉的風格被稱為“蕉風”。他的俳諧七部集《冬之日》《春之日》《曠野》《猿蓑》等使日本俳諧登上了頂峰。
芭蕉去世后的半個多世紀,日本俳諧曾一度中落,到18世紀中葉,與謝蕪村(1716—1783)又重振俳壇。蕪村是一位畫家,他采用繪畫手法和自己對事物的獨特感受來美化現實,開拓了自己浪漫化的俳諧世界。小林一茶(1763—1827)在稍后的俳壇也獨樹一幟。一茶大膽地將口語、俗語、象聲詞運用于自己的作品,從而拓寬了俳諧的語言表現力。
俳諧由連歌的發句(五、七、五)獨立而成。創作時加上“季題”(表示季節的特定詞語)和“切字”(斷句所用的助詞和助動詞),使之成為17字音的短詩。
和歌
和歌作為貴族文學,一時難以適應新興文學的發展。近世時期的和歌作者主要是部分公卿和知識階層中研究古典文學的國學家。江戶初期,細川幽齋(1534—1610)在和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績,被譽為近世和歌學之父。其弟子貞德和木下長嘯子(1570—1649)的成績也十分引人注目。以國學家真淵(1697—1769)為首的萬葉復古派倡導“Masura oburi”(陽剛灑脫的詩風),成為江戶中期歌壇的主力軍。到了江戶晚期,京都的小澤蘆庵(1723—1801)與真淵門派所倡導的萬葉情調相抗衡,主張和歌的創作應以古今集之序為宗旨,提出了用自然樸實的語言表達感情的學說。香川景樹(1768—1843)受蘆庵的影響,進一步倡導作為和歌內容的思想與其表現形式的文字之間的協調,從而確立了自己優美的詩風。景樹有歌集《桂園一枝》。以他為首的“桂園”派自江戶末期至明治維新,在歌壇上始終占有很大的勢力。另外,作為禪僧的良寬(1757—1331),在江戶末期也吟詠了許多很有特色的和歌。
五、近代詩歌(1868—1923)
新體詩
明治維新打破了江戶末期沉悶的社會局面,使西方的政治思想及文藝思潮得以在日本流行。明治15年,當時任東京大學教授的外山正一和自己的另外兩位同事,受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出版了一部《新體詩抄》。這部詩集收有3首譯詩和6首模仿詩,正如序言所講,外山等人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洋風格,創造一種新體詩”。由于外山等人本不是詩人,故集中詩句的意境與語言表達都很稚拙。但就日本新體詩的開創而言,《新體詩抄》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明治22年(1889),文學家森歐外(1862—1922)等在雜志《國民之友》上刊載了一組取名《面影》的歐洲譯詩。較之七年前的《新體詩抄》,歐外的譯詩不論形式或語言都有較高的文學性。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面影》對以北村透谷(1863—1894)和島崎藤村(1872—1943)為首的文學青年產生了極大影響。透谷在當年就吟唱了一部充滿感傷情調的詩集《楚囚之詩》。島崎藤村也于明治30年(1897)出版了著名的詩集《嫩葉集》。集中的詩歌以浪漫主義方式及柔和嫻雅的筆調,表現了明治20年代末日本青年的喜悅和優傷。《嫩葉集》在日本近代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明治32年(1899),土井晚翠(1881—1952)出版了詩集《天地有情》。晚翠的風格不同于藤村的細膩、嫻雅和柔順,而極富陽剛之美。他那用哲理化的思維和雄渾的筆力寫就的詩篇,受到許多青年的青睞。因此,在當時的詩壇,藤村和晚翠有雙璧之美譽。明治33年,與謝野晶子(1878—1942)同其丈夫與謝野鐵干(1873—1935)主辦創刊了詩刊雜志《明星》,對明治末期日本新體詩及短歌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日本象征詩完成于明治末期。上田敏(1874—1916)自明治35年起,連續在雜志《萬年草》上發表了一系列西歐象征派和高蹈派詩人的譯詩(后編輯成譯詩集《海潮音》),引起詩壇的注目。薄原有明(1876—1952)、薄田泣堇(1877—1945)和三木露風(1889—1964)等新一代詩人受其影響,分別以《春鳥集》(1905)、《白羊宮》(1906)和《白手獵人》(1913)等詩集確立了日本象征詩的風格。
作為同期詩人的北原白秋(1885—1942 ),在詩集《邪宗門》(1909)中,用絢麗豐富的語言表達了官能的頹廢和異國情調,使世人大為震驚。另外,以三木露風、相馬御風(1883—1950)和川路柳虹(1888—1959)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受當時自然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開始了口語詩的創作。柳虹于1907年發表了口語詩《新詩四章》,引起詩壇的重視。御風和露風還撰寫了《詩界的根本革新》(1907),以求解決口語新體詩的理論問題。
社會主義詩人同樣是明治末期詩壇上不可忽視的力量。以兒玉花外(1874—1943)和石川啄木(1886—1912)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詩人群體,對后來革命詩歌的興起發揮了先導作用。花外于1903年出版的《社會主義詩歌》,政府以不利于社會安定為由,將它當做禁書沒收。這也是日本近代詩歌史上遭禁的第一部詩集,至二戰結束后才得以重見天日。
“文語自由詩”和“口語自由詩”的互補和并存,是日本大正(1912—1926)詩壇的一大特征。高村光太郎(1883—1956)受“白樺派”人道主義思想之影響,創作了著名的詩集《里程》《1914》。被稱作“民眾派詩人”的福士幸次郎(1889—1946)、千家元麻呂(1888—1948)和山村暮鳥(1884—1924)也分別留下了各自的不朽之作《太陽之子》(1914)、《圣三梭玻璃》(1915)和《云》(1925)。室生犀星(1889—1962)深受《邪宗門》的影響,開拓了自己獨特的詩歌境界,于1918年創作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愛之詩集》和《抒情小曲集》。萩原朔太郎(1886—1942)可稱為大正詩壇的一面旗幟,他以自己的詩集《吼月》(1917)和《青貓》(1923)使日本“口語自由詩”在創作上日臻完善。另外,創作了《黑衣圣母》(1921)的日夏耿之(18901966)和創作了《殉情詩集》(1921)的佐藤春夫(1892—1964),被譽為藝術派詩人,而宮澤賢治(1896—1933)則以其明快的詩句肯定人生,詠唱宇宙及自然,創作出收集在《春與修羅》(1924)中的大量詩篇。
短歌
明治初期,日本歌壇依然維護著固有的傳統,“桂園”派的歌風一度受到崇尚。到了明治26年(1893),短歌界出現了革新氣象。國文學家兼歌人的落合直文(1861—1903)成立了“淺香社”。他在短歌的題材和表現方面提倡清新自由的風格。受其影響,與謝野鐵干先后發表了短歌革新論《亡國之音》(1894)和歌集《東西南北》(1896)。1899年,鐵干又創立了“東京新詩社”,并于翌年創刊《明星》,從而掀起明治中期的浪漫主義的詩歌運動。鐵干之妻與謝野晶子的處女歌集《亂發》(1901),以自由奔放的熱情和浪漫主義手法詠唱新時代的愛情,震動了當時的社會。石川啄木受自然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出版了歌集《一把砂子》(1910)和《悲哀的玩具》(1912)。若山牧水(1885—1928)則以感情至上,創作了歌集《別離》(1910)和《路上》(1911)。他所詠唱的短歌廣泛受到世人的喜愛。正岡子規繼鐵干之后,于1898年發表《致歌人書》,主張以萬葉風格式的“寫生”“寫實”手法革新短歌,對以后的日本短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齋藤茂吉(1882—1953)是日本大正歌壇最具代表性的歌人之一。他發展了子規的“寫生”學說,進而提出“感知實相”的新理論。其影響波及整個大正歌壇和文壇。《赤光》是茂吉的代表作之一。活躍于這一時期的歌人還有:島木赤彥(1876—1926)、土屋文明(生于1890年)和木下利玄(1886—1925)等。
俳句
明治前期的俳壇依然受江戶末期俳諧傳統的影響。明治26年(1893),正岡子規在報紙《日本》上發表《獺祭書屋俳話》,提倡徘句革新運動。子規著眼于蕪村的“繪畫式俳句”,從而提出俳句的寫生手法。以子規為首的寫生派被稱作“日本派”。他們還創刊了機關雜志《杜鵑》。子規的代表作主要有《俳諧大要》(1895)、《俳句問答》(1896)和俳句集《春夏秋冬》(1901)。河東碧梧桐(1873—1937)和高浜虛子(1874—1959)是日本派的主要成員。作為同期的徘句社團還有“筑波會”和“秋聲會”。
子規逝世后的日本近代俳壇主要分為兩大派:一派以虛子為首,繼續以《杜鵑》為陣地,師承子規的傳統;另一派則以碧梧桐和荻原井泉水(1884—1976)為主,受自然主義打破形式的影響,提倡韻律自由和無季題,由此也被稱為“新傾向派”。
虛子曾一度熱心小說創作。但進入大正年代后,他再次重返俳壇,恪守子規的傳統,培養了諸如村上鬼城(1865—1938)、飯田蛇笏(1885—1962)、原石鼎(1886—1952)、寒川鼠骨(1875—1954)、松根東洋城(1878—1964)等一批俳人,從而迎來了“杜鵑派”的全盛期。
六、現代詩歌(1924— )
新體詩
大正末年,曾在西歐掀起的前衛藝術運動影響到日本詩壇。以平戶廉吉(1893—1922)、高橋新吉(生于1901年)和萩原恭次郎(1899—1938)為首的未來派詩人開創了日本的前衛詩運動。新吉的詩集《達達主義者新吉之詩》(1923)和恭次郎的《宣告死刑》(1925)正是日本前衛詩草創期的代表作。另外,隨著無產階級文學在日本的興起,出現了以同人雜志《騾子》(1926—1928)為陣地的無產階級詩人——中野重治(1902—1979)、壺井繁治(1898—1975)和小熊秀雄(1901—1940)等。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無產階級文學很快遭到法西斯鎮壓。昭和8年(1933),掘辰雄(1904—1953)等人創辦了詩刊雜志《四季》(1933—1944)。《四季》時代的詩人主要有三好達治(1900—1964)、丸山薰(1899—1974)、萩原朔太郎、中原中也(1907—1937)和室生犀星等。這些詩人在日本法西斯主義分子統治的黑暗年代,以理智與感情的協調,創作了許多具有較高美學價值的抒情詩篇。“四季派”詩人,又被稱做“日本浪漫派”,其主要作品有達治的《一點鐘》(1941)、丸山薰的《物象詩集》(1941)和中也的《山羊之歌》(1924)。作為反戰詩人而著名的金子光晴(1895—1975),在戰爭年代創作的大量抨擊帝國主義侵略的詩,到戰后結集為《降落傘》(1948)和《鬼子之歌》(1949)。但戰爭年代的許多詩人屈服于法西斯統治,寫了大量歌頌侵略者的“戰爭詩”,因而后來受到無產階級派的嚴厲批判。昭和22年(1947)詩刊《荒地》誕生了。這是一種由親身經歷過戰爭、戰場的年輕詩人為重建戰后詩歌而創辦的刊物。其存在時間雖不足一年,但《荒地》的歷史作用卻不可低估。其間最具代表的詩人和作品有鲇川信夫(生于1920)的《鲇川信夫全詩集》(1965)、田村隆一(生于1923)的《新年的信》(1973)、中桐雅夫(生于1933)的《中桐雅夫詩集》(1964)等。此外,像飯島耕一(生于1930)、大岡信(生于1931)、谷川俊太郎(生于1931)等新一代詩人也十分引人注目。
短歌
昭和初期的無產階級文學及近代藝術派的思潮直接波及歌壇,在左翼思潮的影響下,西村陽吉(1892—1959)和渡邊順三(1894—1972)為推動口語體短歌運動的發展創刊了雜志《藝術與自由》(1925),隨后又與大熊信行(1893—1977)、前川佐英雄(生于1903)等建立了“無產者歌人同盟”(1929),形成一股歌壇的新生力量。但此時整個歌壇的主要力量依然是以齋藤茂吉和土屋文明(生于1890)為首的近代歌人。他們與左翼派歌人相對立,開辟了思想性較強的抒情短歌的新天地。另外,北原白秋等為在現代短歌中復興新古今式的浪漫主義風格,于1935年創刊了《多磨》。白秋在這一時期的歌集有《白南風》(1934)和《黑檜》(1940)。木俁修(生于1906)和宮冬二(生于1912)是白秋的門人。戰后的歌壇出現了桑原武夫(生于1904)、小田切秀雄(生于1916)、田井吉見(生于1905)等人所倡導的“第二藝術論”,即徹底否定短歌創作的觀點。他們的觀點使整個歌壇動蕩不安。但歌壇很快又出現了以近藤芳美(生于1913)和宮冬二為首的“戰后新歌人群體”。他們把戰后的短歌確立為具有新時代的理性和肉體的文學,使短歌具備了新的風格。與此同時,年輕一代的歌人冢本邦雄(生于1922)、岡井隆(生于1928)和寺山修司(生于1936)等掀起了前衛短歌運動的高潮,并在60年代成為歌壇的中堅力量。
俳句
昭和初期的俳壇和歌壇一樣,首先受到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栗林一石路(1894—1961)和橋本夢道(生于1903)等人于1930年創刊了《旗》。由此掀起了無產者俳句運動。但以虛子為代表的杜鵑派正處于空前的興盛階段,迎來了水源秋櫻子(1892—1981)、高野素十(1893—1976)、阿波野青畝(生于1899)、山口誓子所謂四S時代。然而,秋櫻子不滿足于同派俳人那風花雪月的單一格調,獨自主辦《馬醉木》(1928),在創作充滿初戀情感的俳句的同時,還培育了諸如加藤楸邨(生于1905)和石田波鄉(1913—1969)那樣的優秀歌人。在稍后的40年代,誓子也加盟于秋櫻子,掀起了反“杜鵑”格調的新興俳句運動。另一方面,杜鵑派門人中村草田男(生于1901)和《馬醉木》派門人石田波鄉、加藤楸邨一道為維護傳統詩格律和探尋人間真情,采取了與新興俳句相對立的態度,從而被稱作“人間探索派”。但是,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侵略戰爭的年代里,日本俳壇同樣受所謂“文學報國”的右派思想的統治,一些御用文人寫了許多令后人唾棄的“圣戰俳句”。戰后的俳壇也受到了“第二藝術論”的沖擊。1948年,誓子脫離《馬醉木》后創刊了《天狼》;波鄉等也重返《馬醉木》。《天狼》的西東三鬼(1900—1962)和波鄉等為戰后日本俳句的復興起了推動作用。另外,創作俳句集《少年》(1955)的金子兜太是年輕前衛俳人的代表之一,他的《金子兜太俳句集》(1961)對現代日本俳壇有較大影響。
綜觀日本詩歌的發展,“記紀歌謠”如同我國《詩經》,其中大多詩篇都有濃厚的歌頌和神化國家締造者的色彩,但其思想內容積極向上,語言樸實無華,音節自然和諧,對日本詩歌的發展影響深廣。《萬葉集》集日本古代詩歌之大成,開創了日本詩歌“寫生”“寫實”的先河。《古今和歌集》在繼承發揚萬葉詩歌雄壯質樸之風格的同時,在格律上變“五七調”為“七五調”,使和歌逐步形成了貴族意識的細膩流暢優美的格調,而且表現手法靈活,詩歌曲折委婉,耐人尋味。《新古今和歌集》廣泛運用浪漫主義的意象和象征主義手法,追求藝術至上唯美境界,和《萬葉集》《古今和歌集》并存,構成了日本和歌界的三大星座。松尾芭蕉的出現,不僅確立了俳諧(俳句)在日本詩歌中的地位,而且以他那閑寂高雅的“蕉風”為俳壇開辟了新天地。日本近現代詩歌在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下,社團林立,流派眾多,新人輩出。新體詩由外山正一的模仿,森歐外翻譯向島崎藤村、與謝野夫婦、蒲原有明、北原白秋及萩原朔太郎等詩人的創作逐步發展,日臻完善。短歌和俳句在與謝野鐵干和正岡子規所倡導的革新運動推動下,其思想內容和創作手法均取得了長足發展,并涌現出諸如與謝野晶子、石川啄木、齋藤茂吉、高浜虛子及水原秋櫻子等一批著名歌人和俳人。總之,日本詩歌歷史悠久、形式獨特、易于吟詠,很受日本民族的喜愛。因此,它的未來必將是輝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