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花》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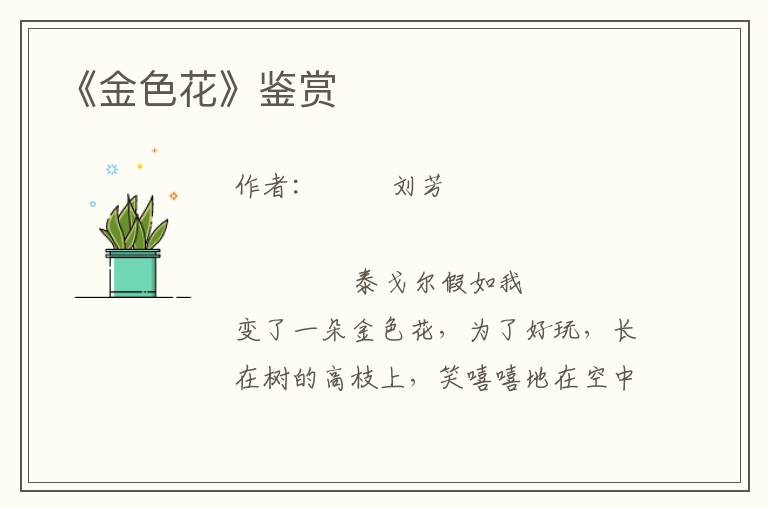
作者: 劉芳
泰戈爾
假如我變了一朵金色花,為了好玩,長在樹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搖擺,又在新葉上跳舞,媽媽,你會認識我么?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卻一聲兒不響。
我要悄悄地開放花瓣兒,看著你工作。
當你沐浴后,濕發披在兩肩,穿過金色花的林蔭,走到做禱告的小庭院時,你會嗅到這花香,卻不知道這香氣是從我身上來的。
當你吃過午飯,坐在窗前讀《羅摩衍那》、,那棵樹的陰影落在你的頭發與膝上時,我便要將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書頁上,正投在你所讀的地方。
但是你會猜得出這就是你孩子的小小影子嗎?
當你黃昏時拿了燈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來,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講故事給我聽。
“你到哪里去了,你這壞孩子?”
“我不告訴你,媽媽。”這就是你同我那時所要說的話了。
(鄭振鐸 譯)
泰戈爾談論美感時說過:“心靈通過自己美的力量,用語言、聲音或色彩記錄下所發現的驚喜和快樂。就在這里,有著創作技巧的運用。而這就是文學,這就是音樂,這就是繪畫”。
泰戈爾的散文詩《金色花》,就是作者的心靈之美與藝術技巧完美結合的產物。
基于和諧與愛的美好的理想,憑借卜卜躍動的童心,通過孩童般純正無邪的眼睛,從天真孩子的思維角度,運用嫻熟自然的創作手段,作者別開生面,將想象空靈的《金色花》奉獻給世人。它不僅是一首格調高雅的詩篇,而且是一幅充滿夢幻色彩的油畫,更是一曲節奏輕緩、旋律優美的樂章。
《金色花》的創作技巧,最突出地表現為構思的新穎和選材的獨特。作品不從某一具體的生活場景著筆,也不在敘事的基礎上發揮,更不通過議論直陳所感,而是另辟蹊經,選取了讓人拍案稱奇的嶄新角度——通篇所寫的,不過是一個孩子的想象,是天真童心的幻想!孩子設想自己變成一朵金色花,在高高的樹枝上舞蹈嬉戲,媽媽認不出他,也找不到他,他卻能看著媽媽工作,可以觀察到媽媽的一舉一動。他能讓媽媽新浴之后聞到自己的花香,能把影子投到媽媽正讀的書頁上,而且是正投在媽媽讀到的那個地方,讓婆娑晃動的花影去攪亂媽媽的目光,讓媽媽怎么也猜不出那是自己的影子。黃昏,當媽媽端燈從樹下走過,自己要突然從天而降,將媽媽嚇的驀然一驚,卻又不告訴自己去哪里了,那將是自己一個非常有趣的秘密。……從這一獨特角度入手,以孩子的奇特想象為內容,用墨不多,展示出孩子天真爛熳的內心世界,把孩子的嬌憨和純真寫得活靈活現,饒有情趣,讓人愛不自禁。
《金色花》的意境恬靜,優美,格調輕柔和諧,自然清新的語言,為我們描繪出有聲、有色、有香、有情致、有靈氣那樣一種境界,的確達到了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地步,給讀者以無限的審美愉悅。
凡是走向世界的優美作品,總是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的。《金色花》盡管只是一首短短的散文詩,卻不僅僅代表了泰戈爾的創作風格,而且顯示出印度民族的某些特色。開著金黃色碎花的“占波伽”樹,那是印度的圣樹;《羅摩衍那》,那是印度民族代代相傳的英雄史詩;長發披肩,紗麗拖地,那是印度女性的通常妝扮;而沐浴后的虔誠禱告,更是釋伽牟尼信徒們每天的必修深。《金色花》里的這些信息,無不烘托出一種濃郁的宗教氛圍,無不顯示出獨特的地域色彩、充盈于作品中那舒緩融睦的韻味,更凸現了東方文明的基本情調。正因為如此,《金色花》可以溝通不同膚色、不同地域的共同理解,可以使不同閱歷、不同性格的人同樣感受到心靈的震顫,可以使不同地位、不同教養者雅俗共賞。
這就是真正優秀作品的藝術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