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記:越窯遺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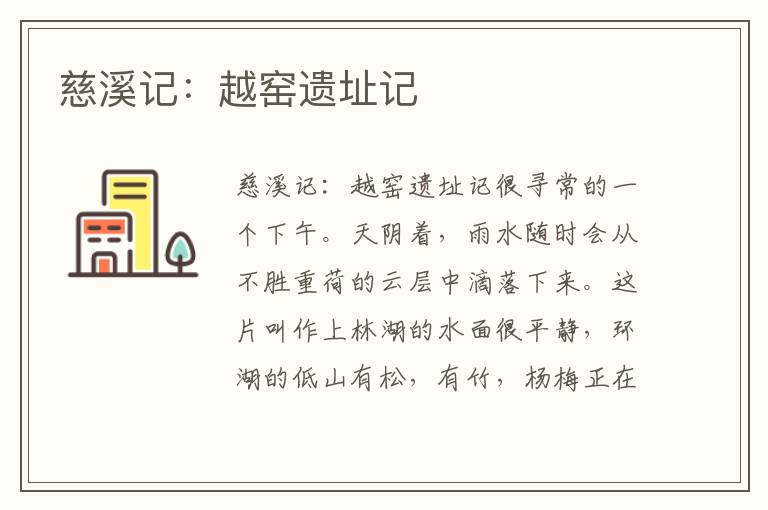
慈溪記:越窯遺址記
很尋常的一個下午。
天陰著,雨水隨時會從不勝重荷的云層中滴落下來。這片叫作上林湖的水面很平靜,環湖的低山有松,有竹,楊梅正在結果,合歡正在開花。載我們劃過水面的狹長的船很漂亮,只是驅動船的柴油機嗓門對這片山水來說,是有點唐突了。
想想那個下午,去到這片水面時還有什么?是的,還有一對新人在湖邊拍婚紗照。準新娘的肩與胸、頸與背因為洋裝的需要而裸露在清冷的空氣中。其實,如此天氣是不適合這樣裸露的,中國人的肌膚也不太適應這樣的裸露。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愿意一輩子至少有這么一回,雖然天氣有些冷,但還是帶著某種不很強烈的歡欣感而這么裸露著了。人生即便再庸常,也希望能建立并擁有一段美麗的回憶。
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境下,來到這里,看一個越窯舊址。更準確地說,是來懷念,來憑吊一種非常中國的物質:瓷。青瓷。青瓷的老窯址。來追懷一種遙遠的美麗。
窯,一個非常中國的詞。
不僅是一部分中國人棲止其中的地方,更是中國人把軟和的泥土塑型,火焙而使之堅硬,并各派用場。這是中國人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火的力量,發現土這種最普通的物質的物理性質,并使之產生奇妙轉換的場所,給最普通的物質塑胎煉骨的偉大所在。那時候,中國人探求物理世界的秘密是多么持續專注,多么愿意在技藝精進后使技藝更加精進啊!我不搞收藏,也沒有想過要一夜暴富。但是,只要是到博物館一類的地方,我總是首先奔向有陶與瓷的地方。所以,主人說,在這個叫作上林的湖邊可以看到一個千年前的舊窯址時,這種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中國,曾經在不同的窯口里出來那么多東西:磚、瓦、俑……缸、瓶、甕、罐……都是與日常生活關涉緊密的器物,卻總能在某個不知名的匠人的手下,靈光一閃之時,上升為藝術,培養了中國人基本的日常的美感。
最奇妙的是,中國人還用燒瓷的方法從窯中煉出了用于活字印刷的字。
但就在某一天,某一個時代,一口一口的窯,莫名地開始坍縮了,那些神奇的火焰也慢慢熄滅了。
這些窯,其中的火熄滅后,終于沒有再點燃,在漸行漸遠的時間深處被遺忘,被荒草雜樹淹沒,那被拍岸的湖水沖刷出來,層層堆積在岸邊的碎瓷片是多么寂寞啊!
在窯火熄滅后的好多好多年里,應該也有很多的人經過了窯群的廢墟和窯場四周瓷器的碎片,卻是毫無知覺的吧。文明的進程常常是這樣,一個地方,一種文化,曾經是創造力勃發的,曾經讓各種生產技藝日益精進,曾經是把美當作內在的蘊含與外在的形態來追求的。可到了某一天,這樣的東西起身離開了,連留下的遺跡人們都會熟視無睹。這樣的時代,是人們的心靈墮入麻木與粗鄙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眾生似乎只是陷于求生與求富的掙扎。又到了某種歷史關口,人們又從荒煙蔓草中重新發現它們,好像內心深處又被觸動了什么,喚醒了什么,意識到它們閃爍著遙遠的、卻是中國人努力追求生活的質地與美感的那些時代的光。那是自己的祖先曾經創造出來的一段輝煌。
人們開始懷著一點慚愧的心情站在這樣的遺址面前。
一口冷窯。
一只其實只剩下一個窯底的冷了一千多年的窯。
多么安靜啊。水還是像當年攪拌過細密的瓷土、像拉坯匠人的手潤濕的那些水一樣,被云彩從海上帶過來,落在地上,又滲入地下,然后,從那些淺山間的某一處縫隙中涌現,成溪,成河,并匯集成湖。
湖邊還站著許多松樹。它們和當年那些燃起熊熊窯火的松樹應該是祖先與子孫的關系。因為安靜,因為有小風,所以能嗅到空氣中松樹特有的那種香氣,針葉的香氣,松脂的香氣。當年,這些香氣進入窯口時就被高溫焚化了。但我還是在此時假想:這些香氣,在窯中也參與了神奇的窯變,變成了青瓷上最神秘最美最不容易捕捉與名狀的那種光,是青瓷中的極品秘色瓷上那個變幻莫測的“秘”。如果松樹的命運一定是被伐倒、被焚燒的話,那進入某一窯口,就是一種最好的選擇了。雖然自己化煙化灰,卻讓焙燒的對象得到了升華,而不是另外的火,使所遇到的東西一起同歸于盡,一起化灰化煙。
腦子里煙一樣縈回著這些想法時,面前其實只是一個只剩個底子的冷窯。在被掩埋和遺忘很多很多年后,重新被發現,被發掘,被考證,被保護,被展示。讓我們記起,史書里記載的開疆拓土的時代,四方來朝的時代,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美流光溢彩的時代。那樣的時代不只是精神強健,氣質也更為典雅雍容。今天的中國人,來到這里,就是被喚醒,被引導。那么,至少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愿意被美所喚醒的時代了。
窯里有火的時候,這地方該是多么喧鬧多么生機勃勃啊!山路上,運送瓷土的人絡繹而來。窯前,一定整出了大片的平地,土和上水被攪,被拌,被搗,被搓,被揉,被塑造成種種坯子。起先沒有釉,后來有了釉。制釉與施釉,給生產流程增加了更多的技術含量,更多的美感。坯入窯了,點火那一刻應該是越來越有儀式感的吧。儀式也給勞動過程增加美感。火點燃了,熱力順著依山坡而建的窯壁自低而高向上升騰。加上瓷土中的金屬性礦物元素,這一下,真是金、木、水、火、土共舞一爐了。互相滲透,互相催發,互相轉化,在當時的世界能夠達到的最高的人工溫度中,以最熾烈的方式升華。如此這般,打開窯上的封泥,讓曾經的熾烈慢慢冷卻下來,這個世界就得到漂亮的青瓷了。大多的青瓷的質地都是可以預期的,最激動人心的是,每一窯口中不可見的物質間的相互轉化,都可能產生出絕世精品。那么,瓷器出窯時又是怎樣的情景?尤其是批量的定制中神奇的窯變奉獻了難以預期的瓷中極品的時刻。在人類的全部勞動中,像這種生產流程中就充滿了出現神來之筆的可能,時刻都有著創造驚世之美的可能的勞動真是不多。人類利用工具來勞動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讓勞動過程和勞動的結果具備美感。這是一種關于勞動的崇高倫理。美的勞動與勞動的美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一些神性的光彩。
站在上林的越窯舊址旁,在一片冷寂的情境中,我追懷那個熾烈而美艷的過程,同時依稀看到,櫓聲咿呀中,出窯的瓷器上船了,從水路去往四面八方,去往中國大陸更深廣的內部,也去往海上,甚至到了海上也不知真要去往何方。那是貿易了,海上吹起的風鼓起滿帆時,就是催動貿易的風了。今天,貿易的進行是越來越頻繁與密集了。正是種種的貿易,讓這片土地正在重現甚至超越昔日曾經有過的物質的繁華。甚至使我們有能力用以千萬以億計數的資金拍賣與收藏穿過時代種種劇烈跌宕而依然幸存于世的瓷中珍品。我愿意將其理解為這是對過去時代的偉大之處的一種追懷,一種對美器、對美器所傳達出來的生活中美的質地的一種尊崇與追求。所以,我期望,這些幸存的美器在博物館中對公眾展示,對我們施以無聲的美的教育,而不是神秘上拍,然后,秘藏,升值,再拍賣。
窯旁,有許多菊花樣開著的淡青花朵。
要知道,在這座窯口中有火熊熊燃燒,有無數種的瓷器,被打捆包扎好了,順著水路去向四面八方的時候,中國的土地上還沒有這種野草。那時候它們還只生長在美洲的荒野。我愿意相信,這些植物的種子是從那些把這個窯口的瓷器運往海外的船只帶回來的。其實,這種看起來很本土的植物很晚才來到這片土地。據植物學家考察,最初在中國的發現,是一八八六年,在上海。但現在,它們全然是本土的樣子了。因為植物之美與周遭的自然環境那么容易協調起來,這是美的一個巨大的功能,不僅本身能和環境協調,而且能把我們周遭很多不美的不和諧的東西協調起來。所以,我這時想到瓷器,就不只是想到它們在重重保安措施下安放在博物架上的樣子,而是想到它們怎樣一天天深入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使大多數時候都黯淡無光的日子變得有了稍許的光亮。
美的光亮。
那真是一種遙遠綿長的光亮。可是怎么形容這種光亮呢?特別是在湖水拍擊下永遠晶瑩的碎瓷片上的光亮呢?突然想到杜甫曾用過一個詞:“哀玉”。他就是用這么一個詞來形容一種瓷。這個詞很好,移用到眼前的情景,那些一天天任湖水與時光淘洗的碎瓷的質感有了,而我們這些憑吊者的心情也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