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圖體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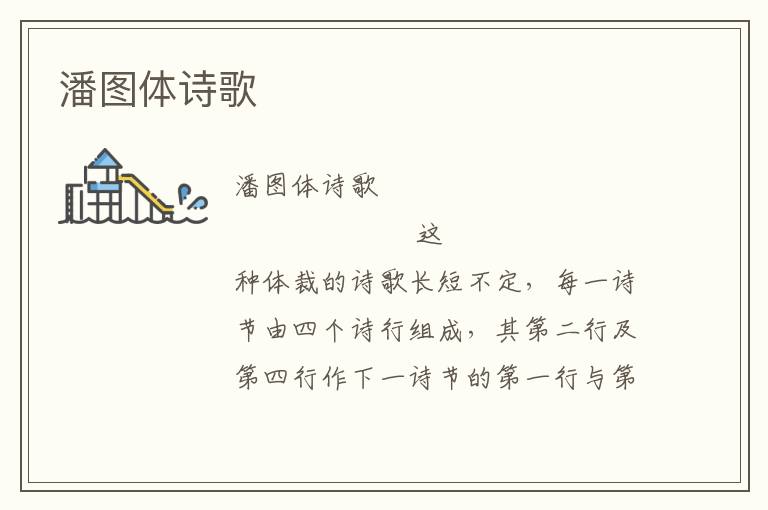
潘圖體詩歌
這種體裁的詩歌長短不定,每一詩節由四個詩行組成,其第二行及第四行作下一詩節的第一行與第三行,以此類推,直到最后一節為止。在最后一節詩中,全詩的第一行又用作為它的結尾一行。在有些英國潘圖體詩歌中,全詩的第三行用作最后一節的第二行。因此,這種詩歌的開始與結尾都是同一個詩行。該詩體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不同的主題必須同時在全詩各部分同時展開;每節的前兩行是一個主題,后兩行是另一個主題,兩對詩行只是在音韻上互相聯結。
潘圖詩體原是馬來亞的一種詩歌形式,最早由法國的東方學者厄內斯特·福伊內引入西方詩歌,后由維克多·雨果在其詩集《東方吟》的注釋中將這一詩體形式確定下來。法國文壇中擅長此體的詩人有邦維爾、西埃費爾、李斯勒以及波德萊爾等。雖然這一詩體源于東方,而且西方接受較遲,但它經常被人們與法國較古老的一些詩體,如回旋體、八行體、三節聯韻體、田園歌體等相提并論。批評(Criticism)
一、批評的功能
和本文第二部分(即“批評的種類”)相比,這一部分篇幅較短,內容少,理論性強。本文對批評的分類是以其可能具有的目的為根據的,這種區分方式打破了各個流派的界限。批評的功能可分為四種(也有人認為是五種),即:技巧的,社會的,實用的和理論的。還有一些與此有關的目的,但嚴格地講,它們不屬于批評的范疇。
1.技巧批評
技巧批評是指對具體寫作實踐的指導。這種批評尚無公認的術語,我們還可把它稱為“寫作課式”批評,“說教式”批評,“實用式”批評,甚至“創作式”批評。后者容易和卡萊爾及蘭姆采用的批評方式相混淆,他們往往由于有創作的沖動卻苦于無法表達而使用批評性論文作為表達這種沖動的一種形式。技巧批評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十分流行。喬治·加斯科因的《英語韻文寫作指導》的標題就揭示了他撰寫該文的目的。帕特納姆的《英國詩歌的藝術》告訴我們,其目的是“指導淑女……和悠閑的朝臣偶然寫點快活小調”。今天嚴肅的批評家對他們的做法不屑一顧。我們由于對藝術的獨創性無比尊重,而不再相信幾句空泛的說教能為學習寫詩的人提供真正的有益的幫助。做詩的規則也許有點意義,但就一首詩的目的而言,這些規則是批評家最少考慮的。
間接的技巧批評更重要。大部分批評者對現有作品進行批評的目的之一是對尚未寫成的作品提出間接指導。唐納德·戴維宣稱他的《純潔的英國詩歌用語》是專門寫給“未來”的詩人的。龐德和艾略特是這類批評的代表。艾略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龐德早期的批評文章主要是寫給“風格尚未形成的年輕詩人”的。其實,不僅在龐德的批評中,而且在艾略特的大部分詩歌中都流露出對詩的未來發展的巨大關注。他的詩作《休·賽爾溫·毛伯利》和譯作《水手》的可鑒之處僅僅是其風格對年輕詩人有所啟迪。艾略特在這篇文章中說:“我最好的文學批評是我個人的詩歌創作的副產品。”這不一定能說明他應用的是技巧批評,因為我們關心的是批評的功能,而不是其來源。但是艾略特在提醒人們注意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和18世紀的玄學派詩人有著共同之處時,他的目的不僅是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這些詩,而且為現代英語詩歌的發展揭開了新的一頁。因此盡管艾略特對玄學派詩歌的理解并非無懈可擊,然而他或其他人應用這種理解(或者誤解)進行批評的方式,卻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
2.社會批評
重要的是詩歌應該有意義,而且應該對社會有意義,因此文學批評應該重視作品的社會作用,幫助文學建立受人尊敬的地位。這個任務可以在不同水平上完成。從最低層次上講,書籍只要有人評論,不論說些什么,都是有益的。日報、周刊的書評欄的作用不僅僅是對一些書籍進行評價,而是吸引人們對文學作品進行不間斷的討論。從高一點的層次上講,這種社會功能在于喚起人們對文學的熱情。羅伯特·林德、德斯蒙德·麥卡錫、菲利浦·湯因比等作家和知名學者亞瑟·奎勒一庫奇爵士等人的文章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閱讀他們的文章使人了解他們的人格,傾聽他們真誠地敘說自己對文學的厚愛。當然,這種文章的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過分袒露自己對文學的熱情容易導致虛張聲勢;大談特談對文學的熱愛無異于嘩眾取寵;一味取悅讀者難免流于庸俗無聊。盡管如此,只要這類文章能夠促使讀者閱讀并討論所讀的書籍,其作用就是令人贊賞的。這類批評若是對一部書做出有分量的評論,就變成了實用批評,若是系統地評論文學的重要性和價值,就成為了理論批評。
3.實用批評
實用批評是指對具體作品的認識研究。實用批評并不古老。18世紀以前針對某一具體的文學作品的評論還是鳳毛麟角,即使有也不詳盡,而且缺少真知灼見。艾迪生在自己創辦的《旁觀者》雜志上率先撰文評論彌爾頓的《失樂園》。與此同時,威廉·理查遜和莫里斯·摩根也開始評論莎士比亞的作品,但是,實用批評的真正的創始人卻是柯爾律治。從他的身上,我們首次發現了“新批評”派的典型特征:仔細研讀作品以掌握要旨,并且引述細節,周密論證。
柯爾律治在《文學傳記》中評論了華茲華斯的詩作和莎士比亞的《維納斯和阿多尼斯》,如果他把這些評論以及他的一些關于莎士比亞的講演,寄給《細繹》和《肯尼恩評論》的編輯們,他們肯定會如獲至寶。而人們可以想象他們在接到艾迪生評論彌爾頓的文章時則會猶豫不決。然而即使是柯爾律治的評論也夠不上現代實用批評的典范;而19世紀的著名批評家如巴杰霍特、佩特、阿諾德等人的評論也使我們感到是差強人意的,或者認為這是由于他們的批評目的和我們的不盡一致。例如,阿諾德檢驗文學作品的“標準”初看起來和現在流行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很相似,然而,他的比較僅僅是啟蒙性的,并不像現代著名的批評家那樣,仔細挑選作品,精心比較其相似之處。
嚴格意義上的實用批評形成于20世紀。1920年的一天,I·A·理查茲在劍橋大學向學生分發了未署名的詩作,讓他們議論和評價。學生們的評論讓人震驚:在雜志上發表作品的末流詩人被吹得天花亂墜,而多恩·霍普金斯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等著名詩人卻遭到無情的謾罵和詆毀。學生們對妙語佳句無情嘲弄,而對荒唐蹩腳的詩行推崇備至。理查茲在《實用批評》一書中描述了上述實驗,并且討論了困擾文學批評的主要問題。這本書和它的續篇《教學中的解釋》已經成為英美各大學從事批評實踐的標準資料中的一部分,其方法是:仔細閱讀原作。學院以外的一批詩人如格雷夫斯、T·S·艾略特、燕卜蓀等也加入了這一潮流,爭相撰文。艾略特的《圣林》(1920)成為本世紀影響最大的批評論文集。格雷夫斯和萊丁合寫的《現代派詩歌概述》不僅評論了莎士比亞,而且也評論了霍普金斯和E·E·肯明斯。他們的文章對燕卜蓀影響頗大。燕卜蓀后來寫了多篇精細入微而又富有挑戰性的文章。他致力于挖掘詩的隱秘含義,研究雙關語、諷刺和語義含混的詞句。《晦澀的七種類型》(1930)就是他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燕卜蓀的基本信念是,卓越的詩歌都是復雜深奧的。“任何時候,讀者若被簡單明白的詩行深深打動,真正打動他的是詩行部分地再現了他往日的經歷和往日的判斷的結構”。果真是這樣,實用批評家便有了大加發揮的余地。加入實用批評潮流的還有F·T·利維斯、克利恩斯·布魯克斯、R·P·布萊克默、蘭塞姆和奈茨。利維斯堅持認為,批評家應禁止使用與具體作品毫不相干的空話。他的批評出色地貫徹了這一主張。他主辦了21年的刊物《細繹》,不僅在名稱上而且在內容上體現了他的一貫主張。布魯克斯的批評文章,他與羅伯特·潘·華倫合寫的大學教材《理解詩歌》一書奠定了他的地位,也使他成為這一批評派中的佼佼者。
實用批評既是一種目的又是一種方法。作為方法,它要求人們批評時必須緊扣原文;作為目的,它與教學法相似,是為了幫助讀者欣賞詩作。讀者一旦能夠欣賞一首詩,評論就無關緊要了,就像詩人一旦把要寫的內容寫成詩后,技巧批評就失去了意義一樣。當然,這種目的是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即對一首詩有一種所謂的“正確”理解之上的,批評的目的就是將讀者逐步引向這個正確的理解。實用批評的反對者駁斥的也正是這一點。
激烈的反對者認為,文學鑒賞既然是主觀的,那么每個人的理解只是對他自己而言是正確的。如果兩個人對一首詩的意義或價值產生了分歧,就每一位而言,都是正確的。F·L·盧卡斯是這種論點的激烈倡導者。這種觀點就字面理解,會使文學討論變得無益。既然沒有外在的標準,重新仔細閱讀原著便沒有意義,因為人們不必修正和提高自己的認識。查爾斯·莫里斯在理論上反駁了上述觀點,他提出了“主觀意識相互聯系”的論點,認為在實踐中,即使是最激烈的相對論者也會偏重某些讀者對一首詩的理解,而不會把所有的理解都看成是同等重要的。
一種較為溫和的然而卻更嚴肅的反對觀點認為,文藝作品的價值是隨著每一代讀者的變化而變化的。T·S·艾略特說,當一件新的藝術品被創作出來之時,“這件藝術品之前的所有藝術品也隨之發生了某種變化”。韋勒克和華倫在討論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時(見《文藝理論》)從理論上對艾略特這一觀點做了最好的闡述;艾略特也用自己的詩歌的影響為此做了完美的例證。這種觀點會很自然地導致歷史相對論,會使人相信“凡是值得翻譯的古典詩歌每過50年都應重譯”,也會使人們認為,每一代讀者都是用自己的方式閱讀古典名著。
如果說某一個時代本身只有一種正確的理解,這種回答是不夠的。時代相互重疊,而初看是荒誕不經的理解也許標志著一種新思潮的興起,或者預示著舊思潮的衰亡。用年代劃分一代一代的讀者必然要包括不同社會、不同觀點的讀者,例如天主教徒、自由派的人道主義者以及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甚至還應包括不同性格的讀者。我們除了要求有某種正確的理解外,還必須假定有一個理解的范疇:它應該容忍那些令人懷疑的、怪異的,甚至荒唐的理解,容忍那些帶有傾向性的,和我們的觀點相左的,甚至守舊的、過時的理解。在“合法”的理解之中到底允許多大程度的“背離”,這有賴于作品本身。坎皮恩、蘭德爾或者豪斯曼的抒情詩很可能只有一種正確的理解,甚至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有多大變化。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李爾王》等則迥然不同,可以自圓其說的理解數不勝數。就《李爾王》而言,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它體現的經驗異常恢弘,內容異常豐富,而《哈姆雷特》除了以上的特點外,它本身的模棱兩可也是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假設實用批評不僅影響我們對一首詩的理解,而且影響我們對它的判斷,這樣就駁斥了那種認為理解和判斷是兩種互不相關的批評功能的觀點。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對一首詩真正的全面的解釋一定是評價性的;在我們考慮一個語句的確切意義和聯想、它與整體的關系,或一首詩的節奏和形式特點的效果時,我們要么認為它取得了好的效果,要么指出它在藝術手法上有缺陷。一種純粹的判斷性批評,如果對細節不加討論,它便失去了意義。判斷批評也許是實用批評的副產品和結論,離開實用批評它便無法存在。
實用批評到底前景如何?假若兩個讀者對一首詩的理解迥然不同,其中一個說服了另一個,使后者承認他誤解了原作,這樣一來,他們的觀點便協調了嗎?也許我們應當假設,他們雖然讀的是同一首詩,尋求的卻是不同的東西。C·S·劉易斯不同意利維斯關于《失樂園》的風格的觀點,他說,利維斯“見而憎恨之處正是我見而喜歡之處”。如果說這是在文學上持不同見解的一個典型例子,實用批評家便沒有多少作為了。但是,如果讀者的文學素養基本相同,只是在判斷一首詩的意義上有能力高下之分,那么,實用批評家便有了用武之地。對缺乏實用批評家那種敏銳的眼光、生活經歷和專業知識,或者沒有機會及大量的時間去研究一部作品的讀者,實用批評家便可以起到開導啟蒙的作用。
4.理論批評
這種批評所考慮的是文學是什么的問題。理論批評把“富于想象力的”或者“創造性”的文學作品與科學、宣傳、消遣讀物或者回憶錄等區別開,也把真正優秀的文學和低劣文學區別開。實用批評所關心的是:“這首詩有什么意義?”“這是一首好詩嗎?”而理論批評關心的卻是:“構成詩歌價值的是什么?”第一部偉大的理論批評著作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朗吉努斯的《論崇高》就意圖而言,也可以看做是理論批評著作。詩辯類的文章自古以來就十分流行,它們都傾向于系統地為詩歌辯解,因此都提出文學和文學經驗的本質是什么這一問題。
這個問題一直是,而且也應該是文學批評所關注的中心問題,而答案則因為批評家的社會或倫理觀念不同而相異,甚至因為他們對文學的目的理解不同而異。關于這個問題,見“詩歌理論”一條,這里僅討論一些主要論點。
認識性理論斷言,文學傳播知識,闡述真理。這是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文學批評的老調。這類批評認為,詩人的虛構是為了闡述某種普遍真理的手段,揭示具體真理是歷史學家的職責,而詩人的任務則是揭示普遍真理。奧古斯都時期的詩人正是利用這種觀點,為他們拒絕講明郁金香有多少條紋的詩風辯解。浪漫派詩人雖然反對這種不負責任的風格,卻依然堅持詩人貴在揭示普遍真理的理論。例如華茲華斯盛贊亞里士多德認為,詩的目的就是“揭示真理,揭示普遍真理.而不是探討個別的、具體的真理”。詩中傳遞的知識有別于生活中的、具體的知識;其區別在于一方面是想象的或情感的知識,另一方面是純理性的知識。雪萊的《詩之辯護》就貫穿著這種認識。濟慈的名言“用脈搏去證明”也蘊含了這樣的認識。但是,文學如果是純粹認識性的,它從原則上講與科學便毫無差別了;而傳統上人們又將把文學看做認識性的觀點與認為文學引起情感的觀點結合在一起了。象征主義理論和大部分與象征主義有關的詩歌首先系統地徹底否定認識性理論。瓦萊里,特別是馬拉梅和艾略特堅持認為,詩歌應該摒棄敘述、論證、說理等散文手法,而應該像音樂一樣把自己限制于建造非寫實性的宇宙之中。與這一思潮并行發展而又顯然不同的是,人們的興趣從有意識創作過程轉到無意識創作過程,提倡詩應該用夢囈般的語言而不是理性語言進行創作。蘭波、洛特雷阿蒙和路易斯·卡羅爾是這一思潮的先驅。他們的理論最后發展為超現實主義。對于文學的理論是否是認識性的,批評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而比這種爭議具有更加深遠影響的是關于文學是說教性的還是審美性的爭論。前者強調文學經驗的效果,后者則強調文學經驗的本身。傳統的觀點是說教性的。賀拉斯的名言“愉悅和有用”便是把說教觀點和言情觀點糅合在一起的產物。直到18世紀,這種說法還是人們普遍接受的信條。賀拉斯的理論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文學的兩種目的是相互獨立互不影響的。在現代讀者看來,這種假設是幼稚可笑的。只有確信文學能影響讀者的態度及行為,才能主張文學可以發揮有用的社會功能,因此,所有為詩辯護者,都堅持詩歌具有說教性的觀點。說教理論的弱點是明顯的。首先,這些理論導致文學可以被代替的推論:假若欣賞詩可以起到匡正人倫、改變人們生活態度的作用,那么改變一下環境、上一門心理分析課程或者服用一種藥品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第二,說教理論似乎與實際的詩歌欣賞風馬牛不相及。T·S·艾略特堅持認為,“詩不應該成為哲學、神學或者宗教的代替物”;濟慈反對說教理論;杜威相信,哲學家建造美學的能力大小取決于他的體系能否抓住經驗的本質。這三位互不相同的思想家所關注的問題都是相同的:評論詩歌不能歪曲其本質。最后,持說教觀點的批評家們總是情不自禁地用非本質的,嚴格地講,是用毫不相干的標準衡量一首詩。例如,約翰遜博士貶斥蒲柏的《懷不幸女士之詩》,就因為這首詩對一個敢于違抗父母之命的姑娘表示了同情。實際上,詩中沒有什么應受到如此嚴厲的抨擊之處。約翰遜博士不贊成蒲柏對這個姑娘的態度,將他的不滿轉嫁到對待這首詩上,應該受到譴責的是約翰遜。要能正確分析不同的評論,辨明什么是詩作的真正效果,從而進一步了解說教理論的意義,這是很難的。龐德和勞倫斯等現代作家都曾苦苦思索過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對理論批評提出的首要要求是,它不應該否定“新批評”思潮的成就。對于“新批評”,評論界依然爭論不休,然而,不管這一思潮堅持怎樣的目的(實用的、理論的、說教的,甚至非批評的),我們對它的最好詮釋是,它是一種批評,我們應該盡力保存和利用這種批評取得的成就。理論批評家甚至有可能像實用批評家那樣,從解釋人手;理論批評家是否這樣做取決于他是一位哲學家還是一位文學家。燕卜蓀的文章幾乎總是與具體的詩作相關,總是把自己喜愛的詩作詳細討論,認為它們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他人的欣賞,而且他關心的是詩中體現的普遍的文學和語義問題。另一極端的著作有科林伍德的《藝術原理》、約翰·杜威的《作為經驗的藝術》和理查茲的《文學批評原理》。這些專著的標題就清楚地表明了理論批評和實用批評在功能上是涇渭分明的。介乎兩個極端之間的有W·K·威姆薩特的《詞語偶像》和蘭塞姆的《世界的軀體》。英語文學批評史上每一位著名的批評家都十分關心理論問題,而對這一問題最關心的也許是柯爾律治(見其《文學傳記》第12—14章)。
文學批評將文學作為文學來研究的學問。其他一些學科也應用同樣的題材,但是不像批評那樣,必須完全集中在現代讀者的反應上,而可能為校勘、文獻學和其他形式的學術研究提供研究方法;或者為自己樹立其他目標。其中主要有兩種目標,即歷史學目標和心理學目標。研究文學史的學者關心的是前人認為詩歌是什么,或者在一首具體詩歌中發現了什么,而不是從批評家的基本假定出發,認為這首詩此時此地對他有所述說。文學心理學家關心的是一首詩與詩人個性的關系,而不注重讀者對詩的理解。毫無疑問,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和心理學家,能為批評家提供一些必要的幫助。對于一首幾百年前創作的詩,我們就需要歷史學家為我們解釋某些詞在當時的含義然后才能充分了解這首詩的內涵。但是文學史、傳記學和對創作過程的研究本身又都自成學科,它們都力求不帶個人感情色彩,而不像文學批評那樣無法擺脫主觀色彩。
二、批評的種類
人們通常視為批評種類的是批評興趣的不同模式。這些種類是在現實的文學研究中相互獨立發展而形成的。其中有些種類代表了文學批評理論的橫斷面,例如,對作品和作家的評價既不完全是分析性的描述,又不完全屬于文學理論評述,因而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種類——判斷性批評。另一些批評理論來源于超越了文學范圍的哲學領域,如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批評。這些不同的理論產生了另一系列的批評種類,也就是說,不同類屬的批評家解釋文學現象時總是從不同知識領域汲取營養。現在公認的大部分批評種類都屬于這后一種情況。
任何批評家探討文學現象時,都難免或明或暗地把它們與某一種事實或者觀念框架相聯系,而他所選擇的框架對于他能取得怎樣的結果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可能選擇把自己評論的內容限制在一些具體的文學事實和文學觀念里。例如,形式批評家就把一首詩當做一個獨立的存在看待,把詩人僅僅當做詩歌的創造者看待。另一方面,他也許會發現文學批評之路在于文學之外,在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分析或者其他有關的學科領域。因而他會覺得進行文學批評最有意義的方法就是把文學置于這些相關學科的角度來研究。這樣就產生了社會學批評、心理學批評等不同的文學批評種類。
這樣籠統地將批評家分類未嘗不可,但如果將這些標簽貼到每個批評家身上則顯然不能說明全部問題。雖然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某位批評家是歷史批評家或者心理批評家,但事實上沒有一位批評家純粹屬于某一類型。在實踐中,他可能會在不同的評論文章中應用不同的理論,輪流使用形式分析理論、文學史理論、倫理學或社會學理論等等。他這樣做只是為了學術上的需要。
1.印象批評
實際上,不論是一個漫不經心的讀者,還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批評家,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氣質和個人經歷,他的判斷必然是在個人氣質和經歷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批評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明顯地依靠自己的個人判斷進行文學批評卻因人而異。有些批評家認為,從事文學批評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起客觀的標準,盡可能地擺脫主觀色彩,而另一些批評家,特別是印象批評家則不以為然,他們任憑個人興趣驅使,評論作品時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不提出任何論證。他們認為,個人敏銳的感覺才是文學批評依賴的惟一有效條件。
印象批評家雖然也常常引用歷史等學科的知識充實自己的觀點,但是,這一流派的名稱卻源于他們自身的批評習慣:他們總是圍繞自己的直接悟性和印象進行文學批評。典型的印象批評家評論一首詩時,總是娓娓敘述該詩在他心中喚起的動人感受,總是隨心所欲地探討這些感受,盡管他有時也參照詩人的其他作品,但大部分時候是在自己的文學和生活經歷中自由馳騁。正像瓦爾特·佩特所言:“在美學批評中,認識客體本質的首要步驟是把握住自己印象的本質,即辨別自己的印象,認清自己的印象。”(《文藝復興史研究》序言)佩特極少利用文學理論強化自己的印象,對他所討論的詩歌和詩人也不做全面描述。自覺的印象主義往往依賴舞臺布局來加強戲劇效果,印象批評家也同樣把他的個人印象一一加以戲劇化。其結果是他可能創造出第二部藝術作品來解釋第一部作品。這類批評家中的知名者有哈茲里特和蘭姆、阿納托爾·法蘭士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作為批評家,這些印象主義者難以保持平衡,他們一方面要避免墮入徹頭徹尾的自傳中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陷進盲目追求感官享受的境地。但有些作者由于技巧不夠嫻熟而失去平衡,因此為這種批評方法敗壞了聲譽,直到今天人們通常還會不屑一顧地說那不過是印象主義而已。但是這種批評的最佳作品絕非像貶損它的人所說的那樣淺薄,那樣不完全;它具有自身的連貫性,并常常具有某種獨到的啟發性,從而使讀者能夠看到新的東西,因此它作為一種富于感染力的批評仍有其一席之地。
2.技巧批評
阿納托爾·法蘭士認為,批評應能使靈魂在名著中體驗到種種歷險,然而,當批評期望提供超過這一要求以外的東西時,它無疑需要發現更多的“客觀”方法。事實上,與印象批評家探討精神世界的方法相比,其他所有種類的批評提供了更易于理解的途徑,提供了某種比印象批評更正規、更易于接受的方法。每一種批評都在追求能看得見的并能用某種貫穿始終的方法描述的結果,都在探索能歸納出明確原則的結果。在所有批評種類當中,最集中于文學角度探討詩歌的是技巧批評的各個分支。這類批評除了關注文學本身以外,對其他方面了無興趣。它們最感興趣的只有詩歌的結構和風格。純粹派認為,只有這類批評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技巧批評家評論詩歌時,遵循三種互不相同而又互為補充的方法之一:把一首詩與一種類型或一類詩相聯系;將一首詩作為一個本身完整的形式實體;或者把一首詩作為某種文體現象加以研究。
(1)類型批評
這實質上是以詩的形式特征劃分詩的類型的一種方法。批評家針對作品中可能包含的因素以及可能產生的效果,首先建立一些比較明確的標準。自維達至約翰遜博士的二百多年間,這成為文學批評的基本程序。艾迪生在《旁觀者》上評論《失樂園》的文章指出,某些“種類”的詩具有獨立的特征。他們評論一部新作品時首先要問的問題可能是:“這是什么種類的詩?”如果一首詩呈現史詩的某些特征,那么便可以假設它必然包含某些章節和人們慣用的技巧,而且還包含著亞里士多德在悲劇中發現的普遍性因素(情節、人物、用詞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相互作用便產生出某種易于辨認的文學模式。一旦某些成分消失或者各種因素之間失卻平衡,詩的結構和效果將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這首詩可能與史詩在一些方面相悖而成為英雄傳奇,在另一些方面相悖而成為模擬史詩或者某種非驢非馬的形式。無論如何,不了解面前的作品屬于什么種類,批評家便無法應用適當的標準。但是一旦確定了它的種類,就可以進一步考察詩人是怎樣運用這種形式的基本手法將各個組成部分納入既定主題,使之融為一體。
類型批評在18世紀衰落了。雖然當時的批評家還沒有完全拋棄這種批評所使用的基本詞匯,但一些著名的批評家(如歌德和席勒)都在試圖重新解釋類型批評的基本原則,類型批評已不再受批評家的重視而成了文學史家研究的對象。這種批評雖然在文學史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但除了進行區分史詩、抒情詩、戲劇詩等等對于詩歌類型的傳統劃分之外,在批評主流中已失去了地位。然而,今天的批評界風行對詩的結構作細致分析,因此,類型批評的描述功能重新引起了廣泛重視。不過,我們尚不能說它是一種獨立的批評種類,更不能說它是一種主導的批評類型。但類型批評如今在批評史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批評家,不論他堅持哪種文學理論,均仍然沿用類型批評在劃分詩歌形式時所使用的標準術語,從悲劇到五行打油詩,皆是如此。批評雖然不再認為形式是自主的,但依然認為形式自有它的特殊性,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類型批評仍有其頑強的生命力。
(2)形式批評
技巧批評家應用的第二種方法是將一首詩作為一個獨特的統一體看待,認為它是將各種因素以獨特的方法糅合在一起的產物。他有時也許發現將詩劃分為不同類型的做法很有用,但是他感興趣的不是劃分詩歌的類別,而是深入分析一首具體詩作中應用的具體方法和技巧。在技巧批評家看來,一首詩的形式就像有機體的生命一樣,是個別的而不是類別的特征;因而,批評的目的便是分析一首詩的每個細節對決定其獨特形式所起的作用。20世紀文學批評發展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在這一觀點的影響下,技巧分析的勃興。批評界接受了“有機形式”這個基本比喻,重新為形式下定義,以便使形式和“意義”發生直接的聯系。
既然構成形式和意義的材料是詞匯,現代分析批評家關注的必然是一首詩中詞匯發生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他們在研究一首詩時致力于詳細解釋詞語的表面意義、比喻、象征、意象和節奏感等。在眾多的技巧批評家中,I·A·理查茲關于詩歌意義的理論著作掀起了技巧批評的浪潮,布魯克斯和華倫的《理解詩歌》一書將這種批評方法引進到無數的美國大學課堂上;他們無疑是技巧批評的佼佼者。這種批評分析詩作時,對詩本身以外的價值不屑一顧,而只分析詩作內部的相互關系,盡可能由此分辨出詩的優劣。技巧批評家應用他們的方法并不能立即指出某一首詩的優劣,也無法解釋一首詩為什么優美而另一首僅僅不錯。當然在實踐中,這種方法常常和某一套獨立的道德或社會標準相關聯,利維斯的著作就是如此;批評家以此將一首詩與更廣泛的現實聯系在一起。
(3)修辭批評
無論是類型批評還是現代的形式批評均與修辭分析有著許多相同的技術手段,也可以說,它們得益于修辭分析。修辭批評家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他們研讀詩作時,尋求的是各種修辭法的漂亮例證,而將詩的整體意義拋卻腦后,傳統的修辭學家讀詩時,也在尋找修辭手法,但絕不是因為詩的整體意義不重要才那樣做,而是因為每一種手法都加強了整體構造中的局部效果。從亞里士多德到昆提利安,所有古典修辭學權威都精辟地論述過從轉義、擬人到句法和音律等修辭手法。每種手法都是一種技巧,能加強演說效果,使演說家妙語連珠。修辭手法起初是演說家的一種應用心理學,后來被普遍應用于散文和詩歌分析;即使在古典文學時期,修辭也并非僅僅局限于演說中。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在教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盡管到17世紀,修辭學被擠出了教學界,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修辭方法又成為一種重要的詩歌技巧。今天,修辭學的地位一落千丈。盡管如此,修辭手法在今天的文學描寫中仍然俯拾皆是。隱喻、對偶、擬聲等五花八門的修辭手法在I·A·理查茲和肯尼思·伯克等現代修辭理論家的筆下也被賦予了新的內容。
(4)文體批評
但是,比這些修辭手法更重要的是這些手法背后的普遍觀念——文體學的觀念。古典修辭學認為,一段話語不僅包含某些陳述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的先后次序,而且包含著某種表達方式——即根據主題的要求和話語的目的所選擇的優雅、普通或者低下的文體。傳統修辭學家正是基于這一概念才支持類型理論的,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像悲劇和史詩這樣的高雅文學形式與喜劇和哀歌這樣的低下文學形式之間存在著明顯差別,而這種差別與其說是存在于題材上還不如說是存在于表現方式上。事實上,許多關于文學類型的討論還是圍繞對文體的這種認識展開的。但文體這一概念現在被無限拓展,從某種角度看,幾乎屬于文學的所有特征都可以看成是文體的特征。其結果是,文體批評不再是屬于修辭學家的財產,而且同樣屬于印象批評學者和歷史批評學家:印象批評學者可以摒棄一切技巧分析而集中在文體批評上;而歷史批評學家常常將文體分析視為自己分內的事。因此,批評家分析文體不僅是為了描述一首詩的語言特點(如生硬或流暢,平淡或艷麗等),也不僅是要將文學模式普遍化(如高尚、哀怨等),而且是為了確定一首詩的獨特風格(如維吉爾式、彼特拉克式、拜倫式等),或者是為了確定某種具有民族特點的表現方式(如高盧式、日耳曼式等),或者是為了概述整個時代的藝術“精神”(如希臘化時期的風格或巴羅克風格)。因此文體討論有時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偏離分析具體詩作這個方向。
文體分析學家充分利用音律分析和文體學這兩種獨立的技巧,使得他們的評論扎根于具體細節之中。盡管幾百年來,音律理論一直為語言學和節奏理論方面的一系列極其復雜的問題所困擾,但幸運的是,批評家已經能夠用各種實用的體系描寫一首詩的音律,概括某一詩人運用音律的習慣,不僅能夠在像彌爾頓或者霍普金斯的作品這樣具有強烈特色的詩歌中,而且能夠在音律風格比他們普通得多的詩作中,找到獨特的習慣用法。而這種節奏特點是研究詩人風格的關鍵,并且與他的修辭技巧、他的流派特征以及他的個人氣質密切相關。如果說音律分析是研究風格的傳統手段,那么文體學則是比較新的的研究方式。文體學旨在概括某一特定時期一種語言的整個表現體系。然而,該領域的一些學者沖破這個范圍,悉心分析某一詩人或某一時期的語言風格。他們認為千差萬別的個人風格均是從整個語言表現體系中所作的獨特選擇,因此可以通過具體而客觀的方式對其進行描寫。
3.文學研究
文學研究旨在搜集和證實各種“事實”而不是評價作品和作者,是最客觀的研究。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區別看待,稱前者為“做學問”。關于做學問與批評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人們爭論不休,這些討論常常很實用地轉向怎樣才能訓練批評式的學者和學者型的批評家這個問題(參見弗斯特《文學知識》、韋勒克和華倫的《文學理論》第6章和第20章、戴希斯的《文學批評入門》第6章)。有些作者認為在文字學、文獻學、版本學、語言學和文學史等方面的研究是進行文學批評的前提,因為必須先掌握它們的結果才能開始對作品進行恰當的解釋和評價。而另一些作者則認為,這些學科本身就包含批評。這個問題之所以變得復雜,是因為這些學科與文學評價均有程度不同的聯系。
(1)文本校勘
這既不是判斷一首詩的優劣,也不是闡釋它的意義,而是提供必不可少的、準確文本“物證”,即綜合各種證據,去偽存真,盡可能地復制出作者的原稿。但是,編輯們有時卻根據自己的標準,忽視文獻證據,武斷地對他們的材料下結論。蒲柏編輯莎士比亞的戲劇時和本特利編輯彌爾頓的《失樂園》時所采取的正是這種拙劣的做法。他們任意篡改原作,認為它們的作者不可能寫出那樣的詞句,即使刪改的部分確實出自原作者之手,那也只能證明作者已經才思枯竭,他們修改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護作者的聲望。但是現代編輯不再擅自作主。自19世紀中葉以來,編輯已普遍認為,不該用自己的觀點影響文本。他們嚴格地根據一種編輯邏輯處理稿件,即盡可能地展現一部作品的出處及寫作日期等可以查清的歷史和流傳情況,比較各種手抄本和印刷本,辨別真偽以及流傳過程中各個時期可能出現的失誤,這當然是最客觀的判斷了。不過,客觀的證據有時會因編輯的鑒賞能力而不可避免地帶上主觀色彩。盡管兩種版本都經過詳細考證,但仍需要判斷哪一種可能更接近于原文,或者僅僅需要決定某一版本是對原文的篡改、印刷錯誤或對作者風格的自由模仿。從這方面來講,最后還是要有賴于編輯在文學上的敏銳判斷力。僅就這點而言,編輯是一首詩的第一個批評家。
編輯如果還對文本加以注釋,以使讀者能讀懂其中的語言,了解其中的人名、地名和觀點所包含的典故,使詩作與其歷史背景完全相符,那么,他所做的每一步都滲透著他的文學鑒賞力。他雖然主要是提供有關事實的細節,然而所謂“有關”的根據何在卻全由他自己決定。他必須隨時判斷一段詩文是否與從前的某個作品有關,是否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聯想模式才能獲得某種閱讀效果等等。既然他必須事先解釋一首詩才能進而找出有關材料,那么在這種意義上,他的任何學術發現,都要依賴于他作為批評家的眼光和在文學方面的閱歷了。然而,他卻通常認為他的基本工作不是對作品進行評價,而是做了些具體的解釋性工作。
如果詩歌批評的興趣是在于系統地解釋詩作以外的東西,那么它的重心便從詩作本身轉移到了詩歌與其背景的關系上了。歷史批評、傳記批評、社會學批評和心理學批評等,都有各自對這種關系的明確定義以及對詩作的有關背景的研究方法。換言之,批評家有各自的標準和研究方式。雖然他們大多數都有不止一條切入批評的途徑,但是他們探討一首詩的方法都與其起源有關;他們力圖解釋詩是怎樣寫成的,受了怎樣的影響才使一首詩具備了它自身的特點。這幾種批評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揭示詩的背景來說明詩本身的特點。他們認為,既然詩僅僅是在部分意義上屬于非文學性的背景中的一種因素,那么,詩不僅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而且也是對這種背景的表現,因此,他們不免將詩當做文獻證據看待了。他們既可以用背景解釋詩,也可以用詩解釋背景。現代的形式批評家素來反對這種方法,認為詩中的觀點和經歷與詩外“相同”的觀點和經歷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這種方法在韋勒克和華倫稱之為文學研究的“外部”方式中,卻是一種標準的程序。
(2)歷史批評
歷史批評家也許同意形式分析批評家的觀點:即詩應該以它本身的特點作為衡量它價值的標準。然而,在決定什么才是詩的特點上,他們的觀點迥然不同。歷史批評家認為,詩在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現象,是在許多方面不同于現在條件的過去思想和經歷條件的產物,因而只有密切研究過去的思想和經歷產生的條件,才能使一首詩呈現出其全部意義。歷史批評家試圖將詩作重新置于它產生的時代,展現它當時產生的條件和當時讀者的反應,揭示它與當時文藝思潮的聯系,總之,要盡可能地恢復這首詩在它的同代讀者心中喚起的感受。他們還試圖挖掘一首詩的本意,并堅持認為只有學識淵博的讀者才能理解一首詩。這種極端的觀點常見于歷史批評中。按照這一觀點,批評家只有使自己能夠按照奧古斯都時期羅馬人那樣思維,而且要用拉丁文思維,才具備討論《埃涅阿斯紀》的資格。不那么嚴格的批評家認為,讀者如果了解一首詩的歷史上的意義,便會更好地理解它,并認為了解諸如宮廷戀愛的常規、幽默的心理因素、查理二世時代的政治風云、弗雷澤的《金枝》的影響等各種各樣的細節,都有助于今天對一首詩產生更清楚和更豐富的認識。盡管這些歷史批評家清楚地知道,一個現代人既不能憑意愿而變成古人,也不能憑淵博的學識使自己返回過去,不過,他們還是認為一首詩的過去隱含在它的現在之中,因而始終不遺余力地去研究它的過去。
但是作為歷史學家,他的任務不僅是弄清楚任何一首詩的背景,而是要把握整個文學界的背景,通過研究各種背景概括出文學發展的脈絡。著名的文學史家如德國的弗雷德里希·施萊格爾、法國的泰納和意大利的德·桑克蒂斯雖然在研究范圍、方法和興趣上截然不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他們不是羅列人名,敘述事件,核實日期,而是尋找事件的發展規律,揭示事件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無疑是一件艱巨的任務,因為他們必須從紛雜的史實中隨時判斷什么屬于文學,而什么不屬于文學,哪些作者無足輕重,哪些影響甚大。但是這種歷史研究除了可能偶爾將文學領域以外的格式強加在文學資料上之外,當然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文學批評上的判斷。在文學史家看來,有些作者和作品之所以超越了當時的背景,可能是因為他們應用了某種新的表現方法,或者是因為他們異常清晰地表現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某個方面。文學史家認為這類作者和作品更有意義,理所當然地要受到他們的特別青睞。這些文學史家甚至會進一步聲言這些作者本來就非常卓越,非常偉大。文學史家作為批評家當然有權做這種斷言,不過,他們這樣做時憑借的卻不是歷史知識。歷史證據本身能夠顯示詩和詩人因其作用而具有的價值——他們的代表性以及在歷史上產生的影響,但卻無法揭示詩人的自身價值和詩作的內在價值。由于不能分清這二者的區別,而產生了一種傾向,認為凡是好的作品就是有“意義”的作品,這種認識掀起了對三流作品進行考古式研究的浪潮,不僅加大了學者與批評家之間的距離,而且對雙方都沒有任何裨益。
文學史研究僅僅是文化史和思想史領域中的一部分,在兩個領域當中,文學史是研究證據的許多來源之一。文化史學者也許希望,也許不希望,發現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所有文化性創造活動之間存在著一致性。但不管怎樣,他都認為所有這些活動均表達了時代精神,同時又自成體系,具有自身的連續性。文化史研究中的一種叫做思想史,這種研究確實是在尋找某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一致性,它的前提是每個時代都有它獨特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不僅體現于當時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之中,而且還體現于當時所有機構之中。研究這種時代精神的史學家致力于研究一個時代的形式哲學、科學、藝術以及社會習俗的發展情況,他之所以研究文學僅僅是想把文學作為這個時代特定思想模式的證明;當然,也可能是把文學作為對他自己關于人類文明的理論的證明。《西方的衰亡》的作者斯彭格勒就是如此。
文化史的另一個分支是由A·O·洛夫喬伊創立的“觀念史”研究。這個分支主要研究哲學問題,而不甚關心時代精神。這個分支旨在追溯一種哲學思想在它們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對某些哲學家的哲學體系的形成以及其他文化現象的產生有著怎樣的影響。文學是為這一歷史詳細地提供解釋性材料的主要源泉(見洛夫喬伊的《存在之鏈》第1章,該章是這種研究方法的經典闡述)。批評家利用以上這些學科的知識進行文學研究,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文學與其他文化活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而更直接的原因是因為對這些學科的了解能引起他們對詩人作品的知識含義更加注意,對這些詩作的隱含意義也更加注意,而詩作的隱含意義對于作品的整體連貫性卻至關重要。
文學史批評的另一個有關的分支是社會學批評。這一批評流派認為,文學是社會的一種表達方式:詩人、詩作以及讀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力量的影響和制約,因而對詩人創造的作品也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盡管杜博斯和施塔爾夫人等許多早期的思想家都認為文學既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又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然而人們通常認為真正系統地創立社會學批評的是法國歷史學家泰納。他用嚴謹的科學方法闡釋一個民族文學的整個發展歷程,并為這一研究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種族、社會背景、時機”,這三種因素被認為是決定文學史的基本因素。三者相互結合如同化學反應一樣,使一個特定時代必然產生一個特定的作者,并決定著這個作者作品的基本特征。后來的文學社會學家基本上拋棄了泰納這個嚴謹的概括,而只保留了其中關于作家社會背景的簡明概念。不過,人們還是覺得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最終都服從于社會的總法則,至少可以說,各種藝術形式的發展歷程都可以通過分析社會環境因素而得到解釋。但是這樣做,社會學家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超出了文學批評的中心問題,因為他們將文學的各個方面作為可以進行定量分析的社會機構來研究。他們可以將詩人視為某位個人或者視為職業作家,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集中研究這位詩人的環境,詩人作品中出現的社會形象和其中隱含的社會意識形態與藝術活動之間的關系等等(見鄧肯的《社會的語言和文學》)。與這種認識一脈相承的許多實踐批評要么致力于研究一個詩人的特定社會環境對他作品的影響(如F·W·貝特森的《英語詩歌:批評導論》以及埃德蒙·威爾遜的許多論文),要么研究各種文學形式、文學常規和文學思潮的社會根源(如赫伯特·里德的《英語詩歌面面觀》)。毋庸置疑,這樣的研究必然會帶上心理傳記色彩,同時也會帶上人類學色彩。
從根本上講,這種批評并不總是描述性的和闡釋性的。將一首詩作為反映社會力量和意識形態產物的批評家,很可能武斷地認為這些力量是健康的或者是有害的,是值得贊揚的還是必須嚴厲駁斥的。他甚至還會要求作者有責任借文學形式提倡某種他的作品之外的東西,甚至為批評家自己的觀點搖旗吶喊。按照這種推理,托爾斯泰就會要求作者直接為基督教的大同社會獻身;弗農·帕林頓就會更加推崇信奉杰弗遜主義的作者;朱利恩·本達則會大加贊賞那些超越大眾思想意識并用自己的作品反對這些思想意識的作者。這樣的要求本身并不比其他要求更過分。在20世紀各種要求藝術家必須有鮮明的思想意識的批評中,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影響最大。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歷史哲學,其次才是一種政治行動的綱領。它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理論僅僅是派生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為文學批評提供一個系統的方案,把他們的經濟決定論與美學價值觀聯系起來。有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主要不在于評價藝術作品,而在于揭示產生這些藝術作品的基本社會和經濟影響。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通常采用的方法兼顧兩個方面,認為一部作品既是階級利益和作者志向的反映,同時又會為理解社會發展的真正目標產生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影響。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求作者將文藝作品當做武器,剝去資產階級文化的偽裝,大力宣揚共產主義理想,號召人們堅信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人都能享有幸福和自由,因為他們將擺脫經濟枷鎖的束縛。持這種觀點的人對于不用自己的作品宣傳這種信念的作者是不能容忍的,甚至視其為危險分子,因為他們的作品會導致人們形成錯誤的“集體心理”(布哈林)。這些原則幾乎完全將藝術品當做政治文件看待,因而有時導致怪誕的結論。有一位批評家就認為《暴風雨》是莎士比亞對殖民主義擴張的政治基礎所作的研究,而凱利班則是劇中惟一熱愛自由的人物。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批評若盡是這樣的話,那么它肯定不會在其意識形態圈子以外產生任何明顯的影響。拋開意識形態的爭論而言,許多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確實通過集中研究階級構成、財富和社會權力分配隨著時代而演變的情形,為文學史的研究拓寬了視野。在西方,一些不為經濟決定論辯護的批評家,也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得到有用的啟示,使他們能夠考察文學發展趨勢背后的經濟背景。一批觀點迥然不同的批評家要么一貫地,要么偶然地利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評論詩作。其中較著名的有克利斯托弗·考德威爾、肯尼思·伯克、威廉·燕卜蓀和D·S·薩維奇等。當代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中最有影響的是匈牙利的盧卡契。
在上述這些“起源式”批評中,詩人本身有時似乎消失在各種影響、力量和思潮形成的叢林背后。但是還有一種歷史批評——傳記批評,在這種批評中詩人無疑處于舞臺的中心。圣伯夫在他的《新月曜日》一書中寫道:“我喜歡這個作品,但卻很難在把它與其作者完全隔離開的情況下評論它。”這句話包含著這樣一個假定,即詩人的生活性格,甚至他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細節,都可能是理解他的作品的鑰匙,因而就成為欣賞他這一詩作的關鍵。當然,許多文學傳記并沒有貫穿這種觀點。詩人的生活也許有它獨特的魅力,而與他的作品并沒有必然的聯系。許多學者既對詩人的生平感興趣,同時又喜歡他的作品,但并不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聯系。比如說,鮑斯韋爾的《約翰遜傳》一書并未追尋約翰遜博士的生平與他的詩作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將約翰遜的個人品質與他的詩作價值聯系起來,而是僅僅為后輩讀者塑造了一個既是偉人也是偉大作家的形象。同樣,約翰遜自己的《詩人傳》一書也是采取將傳記內容和批評內容區別對待的方法。他通常是在敘述了詩人的生平之后,再專門對他的詩作進行評論。正如大衛·戴希斯在《文學的批評方法》一書中所說的,這種傳記既不同于那種“從詩人的心理發展過程中尋找理解和欣賞他的詩作的線索”的傳記,也不同于那種從詩作中為詩人的生平和性格尋找線索的傳記。這后兩種傳記基本是從浪漫主義文學心理學派生出來的一種形式,它們強調個人創造力并且注重詩人的思考。卡萊爾便是寫作這類傳記的泰斗。在他的研究中,他為席勒、彭斯和莎士比亞等人塑造了英雄的形象,在這些論文中他們的文學作品主要是“一個人最偉大的作品,即他所經歷的生活”當中的一些成分而已。圣伯夫與卡萊爾是極不相同的作者,但在創作文學傳記方面卻極其相似。圣伯夫以詩人的性格為軸心,以豐富的史料為背景,將詩人的生平和作品糅合在一起敘述。他的《月曜日漫談》就是這種傳記批評方面膾炙人口的典范。但是,這類批評家有陷入循環論證的危險,那就是他們交替使用詩人的生平以及作品互相說明,首先從詩中演繹出詩人性格,然后又用演繹出的性格去評價詩作。格奧爾格·布蘭德斯和后來的批評家根據莎士比亞的生平評論他的戲劇和十四行詩。他們的評論明顯地具有這種傾向。然而,在其他受斯蒂芬·喬治的“內在形式”影響的許多傳記中這種傾向是隱含的,蒂利亞德寫的《彌爾頓傳》正是如此。蒂利亞德認為,一首詩的真正主題是詩人創作時的心態。但不論是弗蘭克·哈里斯那種隨筆回憶錄式的,還是大衛·馬森那種對詩人生平與時代進行綜合研究式的,所有傳記批評都有一種基本信念,即盡管詩人的生活經歷對他的創作有所影響,然而貫穿作品始終并成為其一部分的卻是詩人的性格,在評價詩歌時如果忽視詩人的性格無異于隔靴搔癢。如果一個批評家斷言《伊利昂紀》和《奧德修紀》不是出自同一詩人之手,因為一個詩人不可能在兩首詩中對狗采取截然相反的態度,那么這位批評家所寫的傳記便很難是真實可信的。而他的這一論斷恰恰清楚地說明:從作品到詩人再回到作品的批評方法,已成為一些批評家的習慣性作法。
近年來,傳記批評從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中,尤其是從風靡一時的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中受益非淺,呈現著勃勃生機。雖然心理批評的各種分支研究詩作的方法絕不完全是起源性或傳記性的,但是除了I·A·理查茲的著作之外,最有影響的心理批評卻是那些把詩人的性格作為研究焦點的著作,或是那些對揭示詩歌創作過程的奧秘提出某種線索的著作。那種認為詩人是受非理性力量驅動的觀點并不新鮮。柏拉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在《伊安篇》里說過類似的話。每當人們在向繆斯女神的祈求中提到神奇的靈感之火時,都有著這種含義。雖然現代批評家不喜歡用靈感、繆斯等術語,他們仍然不遺余力地研究詩人的創作過程。J·L·洛斯在他著名的《通往想象力之路》中詳細分析了柯爾律治的創作活動,通過梳理柯爾律治閱讀的大量書籍,力圖追尋柯爾律治想象力的綜合過程,顯示了他所運用的原始材料及其轉化過程,不過沒有說明這種轉化的方式。C·D·阿博特也做過類似的研究。他在《創作中的詩人》一書中,根據詩人的構思和草稿分析一首詩形成的各個階段。他的分析是規范的,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心理學范疇。他著重研究詩人刻意改動的地方,而沒有觸及詩人創作靈感這個最初的神秘力量,因為正如斯蒂芬·斯彭德在《一首詩的創作》一文中所說的,靈感是“神賜”的。但是,許多批評家接受了弗洛伊德及其門徒的學說,試圖從詩人的潛意識中尋找靈感產生的奧秘。因此他們轉向精神分析理論的不同流派,對詩人創作這個謎做出了部分回答。
弗洛伊德的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不相一致;他的繼承者又自立門派,研究的側重互不相同,致使精神分析學理論紛繁復雜。即使撇開這些分歧不談,要想澄清精神分析學與文學批評的關系也不是三言兩語的事情。但總的來說,精神分析學認為一個人的精神包括被意識活動排斥和壓抑的本能需要與欲望,這些本能時常尋求發泄的渠道。由于本能活動受到意識活動的壓抑,便以偽裝的和象征的方式出現——如以夢和藝術品的方式出現。這樣,精神分析便與文學發生了聯系。按照這種認識,一首詩應該被認為是象征性地表現了詩人潛意識中的幻想和欲望,為我們理解詩人性格隱秘的深處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途徑。當然,并不是所有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都在悉心研究詩人的精神生活。查爾斯·博杜安的《精神分析學與美學》是他研究比利時詩人維爾哈倫的論著。在這篇文章中,他用了相當的篇幅探討讀者對詩作的反應當中的精神因素。不過,大部分精神分析批評都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詩人神秘的下意識。歐內斯特·瓊斯的《哈姆雷特和奧狄浦斯》可能是運用弗洛伊德理論分析文學作品最著名的文章。瓊斯在文章中首次提出,哈姆雷特之所以在行動上遲疑不決是因為他有戀母情結。如果他的分析僅此而已,那么也產生不了巨大的影響。瓊斯進一步指出。哈姆雷特的內心沖突“正是莎士比亞本人內心沖突的反映”。他分析了哈姆雷特的精神活動后斷言,“所有男人都有戀母情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弗洛伊德認為,一個人的早期性經歷對他潛在本能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盡管許多學者都反駁過這種觀點,但它的影響仍然是巨大而深遠的。批評家對一批詩人的分析是引入注目的,他們將其突出特點追溯到戀母情結、對閹割的畏懼、受到壓抑的同性戀心理或者幼兒期行徑的創傷等。但既然弗洛伊德理論認為性本能是人類固有的,那么為什么這些現象明顯地表現在詩人身上呢?其實這并不奇怪,只是因為詩人的精神活動表現于他們的詩歌中,而他們的詩作出版后又便于批評家搜集研究罷了。弗洛伊德理論以及他關于文學與個人本能相聯系的學說的巨大影響,并不是因為運用精神分析學說研究文學作品的結果。不論我們如何看待批評家的上述分析,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稱職的批評家在解釋直接受弗洛伊德理論或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影響的作品中,有一個可以進一步探索的領域。在近幾十年間,幾乎所有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弗洛伊德理論和這一理論引起的爭論的影響。批評家的任務就是指出它對具體的詩作、戲劇和小說的影響。
在弗洛伊德的《圖騰和禁忌》等著作和榮格的更大量著作中,對于反復出現的象征模式的探索,突破了對個人經歷的實用限制,而進入一個更普遍的文化傳統領域。首次提出“集體無意識”這一概念的正是榮格。他認為“集體無意識”狀態是個人精神中最原始的部分,是種族記憶的寶庫。許多批評家摒棄了榮格的其他思想,惟獨鐘愛他的“集體無意識”學說,因為運用這一學說能夠充分解釋不同時代的文學中反復出現的故事和主題的原因及其強大影響。榮格不僅強調原始意象和原始模式的作用,而且同時對人類學、比較宗教、古典考古學、繪畫藝術中的肖像學以及語言中的象征手法等等領域也進行了獨立的研究。他的這些研究重點集中在文學中儀式性的因素和神話因素。正是這些不同來源的結合產生了神話學批評學派。神話學批評目前方興未艾,在批評界影響甚大。這種興趣的主要根源既是人類學又是心理學。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奠定了神話學批評的基礎。蘇姍·朗格的《哲學的新途徑》展現了這些研究的廣度。從文學批評角度來衡量,諾思羅普·弗賴伊的《批評之解剖》是到目前為止在這一領域最詳盡的論作。在受榮格理論直接影響的論著中,最有啟發意義的仍然是莫德·博德金的《詩的原始模型》(1934)。
除了精神分析學以外,至少還有兩種與文學批評有關的心理學流派需要簡述。這兩個分支基本都不是起源式的。其中一個是實驗心理學派。從福克納到伯克霍夫以及后來的批評家都采用一系列統計學技巧,利用水平測試和選擇測試手段,例如“主題知覺測試”等,以及對美學反應的心理學研究。另一分支是格式塔心理學派。這個學派圍繞感覺過程創立了它的理論,認為美學及其他研究的特點就是把復雜的整體當做整體來研究,而不僅僅是對具體部分以及對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道格拉斯·N·摩根在他的一篇論文中對這兩個心理學流派在藝術研究方面的成就做了簡明的總結。大多數研究者都覺得實驗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并不切實可行。格式塔心理學雖然在分析視覺藝術的感覺模式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它至今仍無法成功地將其研究方法轉移到文學分析上。而魯道夫·阿恩海姆在《創作時的詩人》一書中的“做詩過程的心理筆記”一章中,又轉回去研究詩人自身了。
I·A·理查茲創立了審美經驗理論,認為審美經驗與審美沖動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他的這一理論無疑對文學批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與本文無關,在此不作討論。正如前文所述,理查茲強調詩中語言各種特性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力地推動了注重詩歌詞語分析的現代潮流。理查茲早年曾反對詩具有認識性和知識性功能的說法,重新激發批評界對藝術與“真理”的關系這一古老問題展開討論。理查茲將這一關系稱為“詩與科學”的關系。理查茲自1921年出版的《美學的基礎》后,他關于詩歌的許多觀點都有所改變。他最初對詩歌功能所做的實證主義闡述依然是現代文學理論中最富有成效的一種刺激。關于他的觀點及其影響,見蘭塞姆的《新批評》、默里·克里格的《新的詩辯家》、威姆薩特和布魯克斯的《文學理論》等。
4.比較批評
比較批評與以上討論的各種批評截然不同,它沒有鮮明的理論體系,因而與其說是靠理論獨樹一幟,不如說是靠它的研究方法。顧名思義,比較文學就是對不同的作品、作家及藝術流派進行比較研究,由于這種比較可以從上述的任何一種觀點進行,既可以從形式和風格方面,又可以從歷史學和社會學方面比較,這種批評與其他各種批評均有關聯,因而可以認為是任何一種批評的分支。盡管如此,它也有它本身的領域,因為“比較”這個名字就恰當地指出這種批評跨越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界限,可以比較莎士比亞與萊辛或者洛佩·德·維加,而且跨越不同藝術之間的界限,可以比較彌爾頓與普森,莎士比亞的《奧瑟羅》與威爾第的作品,或者奧古斯都時代典雅莊重的詩與帕拉弟奧式的建筑藝術。這種比較批評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大部分還是零散的、不系統的,尚停留在對風格的特點、對某些主題以及對不同藝術的特點類比進行孤立的研究上。不過,這種批評有著進而概括時代精神或者美學理論的自然傾向。自達·芬奇發表《比較》后,文人學者們就開始研究不同藝術和美的聯系,撰寫了幾十篇文章,論證繪畫、音樂以及其他藝術的發展與詩歌是“并行不悖”的,當然也有文章指出,一些著名的作品并沒有追隨時代潮流,并堅持認為藝術各立門庭,不可混為一談(如萊辛的《拉奧孔》和巴比特的《新拉奧孔》)。從理論上講,現代美學在理論水平上可以說是發軔于18世紀的比較批評。
上述各類批評當中無論哪一種,只要是對詩的價值和詩人的藝術地位做出判斷,那么它在這種程度上就成為判斷批評了。正如以上提到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批評即使在最初階段也必然是包含著某種價值判斷的。簡單地說,只要認識某種文學現象,就是以某種方式把它置于一定地位,哪怕是臨時性的,因此就是對它具有某種態度。這種態度可能尚不成熟,需要修正,但它從一開始就是依照標準的。僅僅這樣還不能算做真正的判斷批評,只有根據某種普遍的標準評價詩或者詩人的優劣才能夠做真正的判斷批評。雖然價值標準千差萬別,似乎毫無共同之處,但還是可以分成幾種類型。每一種批評都有它自己合適的范疇,其美學標準和意識形態標準也不盡相同。致力于對詩作本身特點進行研究的批評家所做的價值判斷基本是美學方面的,集中于作品的內在本質以及它獨特的心理效果。上述關于現代技巧分析部分講的便是如此。這類批評家在實踐中也許會應用其他標準,但主要運用形式分析和心理價值判斷兩種方法。另一方面,凡是認為一首詩的主要意義在于它對經驗做了評述的批評家,首先是用政治、社會、倫理、宗教等意識形態標準判斷詩的價值,因為把經驗作為整體來判斷時,這些標準便是至關重要的。根據某一種社會或宗教觀念建立起來的文學批評則是意識形態批評的極端例子。這種批評認為詩中的意識形態內涵便是一切,而它是一首詩這一事實卻意義不大或者無關緊要。當然在實踐中,絕大多數強調意識形態重要性的批評家并不是如此嚴守教條,并不要求詩作必須符合批評家自己的觀點,也不要求詩作必須為某種事業服務。這類批評的核心主張非常簡單,那就是,文學的大部分價值來源于一種對其他經驗的復雜而嚴肅的關系,而在鑒賞詩作時批評家就需要考察這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它的內涵是什么,有什么啟示等等。
在文藝批評的悠久傳統中,意識形態標準中的倫理價值從一開始就占據了相當的地位。自從柏拉圖將除了贊美上帝和歌頌英雄的詩作以外的所有詩歌逐出他的理想國后,詩歌具有“匡正人倫,教育感化”作用的觀點便成了文學批評中的熱門話題。賀拉斯針對詩歌的道德標準和美學標準的關系問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模棱兩可的論斷:詩歌的目的“要么是感化,要么是愉悅,抑或兼而有之”。文藝復興時期的批評家既反對詩歌庸俗化又反對詩歌哲學化的傾向,而認為詩歌應通過表現高尚行為之美而激勵人們樹立良好的道德風尚。這絕不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變通。早期類型批評理論的座右銘就是每一種體裁的詩歌都以它特有的方式發揮著道德感化作用。拉潘和勒博敘,維吉爾和斯賓塞,都認為史詩具有倫理寓意,甚至政治智慧。詩歌具有道德訓誡作用的觀點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是詩歌批評的兩個極端,處于二者之間的觀點數不勝數。因此,不同意托爾斯泰的文藝觀絕不意味著就是贊同王爾德的文藝觀。
文學表現人在具有嚴肅的道德意義的環境中所呈現的性格和行為。因而,用阿諾德的話說,文學就是對生活的批評。一旦批評家認為詩的首要功能是用道德感化的方式處理經驗,懲惡揚善,或者刻意塑造善的形象,或者說,一旦他必須判斷一首詩對生活的反映是正確或者錯誤的時候,倫理批評家就粉墨登場了。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爭論和異議,因為即使可以簡單地把藝術定義為對生活的反映,但它畢竟與它力圖表現的生活不是一回事,這樣,判斷藝術的標準就不僅要包括符合生活的一面,而且必須包括遠離生活的那一面。T·S·艾略特在《宗教與文學》中清楚地闡明了這個道理。他寫道:“盡管我們必須牢記,作品是否具有文學價值必須用文學標準衡量,但作品是否偉大卻不能僅僅用文學標準做出判斷。”雖然在總的意識形態批評之中,典型的倫理批評試圖解決文學中真實與偉大的問題,但是僅僅憑借美學或文學標準卻不能如愿以償。
批評家應用他們的判斷時,常常忽視其價值所具備的哲學意義。但長期以來,理論界爭論不休,試圖澄清這些價值的本質以及它們進入經驗的方式,批評家通常也以含蓄的方式參與這類爭論。批評家非常自信地認為,他們在詩中發現的這些價值是永恒的還是暫時的,可以隨著條件變化而變化。持第一種觀點的就是絕對主義批評家,而持第二種觀點的是相對主義批評家。前者認為世間萬物都遵循一種普遍的規律,因此不論這些價值是以怎樣的形式出現,都符合一個總的價值體系。他們還認為,判斷標準的差異不過是個人或者一個時代探討真理的能力差異的反映。今天絕對主義觀點已不再時髦。“相對主義”這個詞有多種涵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相對主義”和“歷史相對主義”,二者雖然均接受心理學而不是本體論對價值下的定義,但其含義及批評方法卻不盡一致。個人相對主義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主觀的,因此價值可以因人而異,任何個人的感知都不能認為是絕對的、地道的印象。批評家大概會接受上述觀點,盡管他仍可以相信他自己確認的價值是銘刻在事物的天性之中而不可磨滅的。歷史相對主義拋棄了個人相對主義中的絕對主觀性成分,強調社會與教育對個人的影響。它認為,價值觀念隨著時代和風尚的變化而變化,對一個時代或者一個民族有意義的價值,也許在另一個時代或另一個民族看來一文不值。因此在評價任何詩人的作品時,都必須同時考察詩人所處時代的價值標準。弗雷得里克·A·波特爾在《詩的習用語言》中對這個問題做了精辟的論述。
5.科學批評
最后一種需要評述的批評類型是科學批評。是否確有所謂“科學批評”完全取決于如何給這個術語下定義。盡管批評界有時給各種不同的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研究以及語言學批評、文本校勘、手稿考證,甚至傳記等冠以科學批評這個名稱,但是這些批評方法無一具備構成一門科學的統一標準。將上述研究稱做“科學”的大多數作者不過認為,它們對以經驗為依據的事實表現出高度的尊重,并且在描述中力求清晰與連貫。如果這是科學,那么就應該像批評家有時提議的那樣,讓文學批評也應該朝著完全成為一門科學的方向發展。但實際上.一種研究要成為科學,它所處理的材料以及材料之間的關系必須能夠經得起經驗驗證,并能從中歸納出規律,人們運用這些規律能夠預測它的發展變化。文學作品(包括詩歌)的價值不同于音素、水位和心率,不能用科學的方法測量。文學作品的價值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盡管我們可以說發現了什么價值,也可以討論這些價值,但卻不能用科學的方式來確定。例如,不能僅僅根據數字統計結果來說明濟慈詩歌的藝術價值高于或低于拜倫詩歌的藝術價值。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在文學(詩歌)批評領域,不可能有所謂的“科學批評”。以定量、定性分析為基礎的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不是文學;科學在文學研究中的作用僅是輔助性的,主要體現在資料收集、整理與統計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