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隨筆·孔子正名》譯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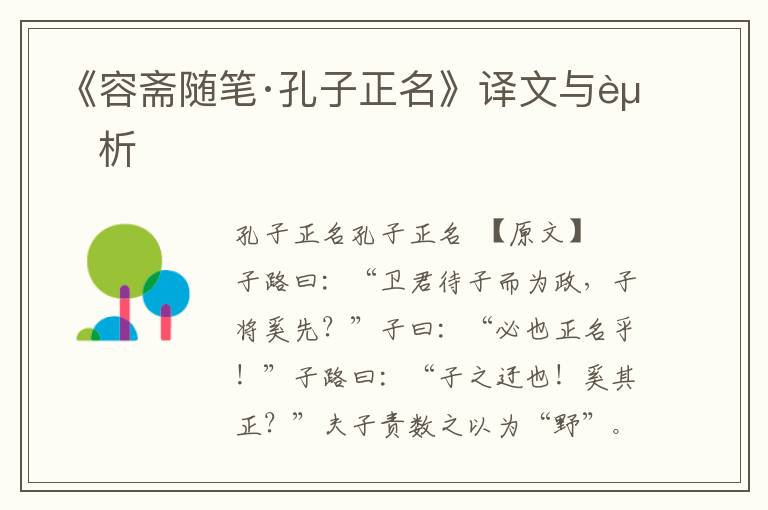
孔子正名
孔子正名
【原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圣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茍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于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悻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圣言,執迷不悟,竟于身死其難。惜哉!
【注釋】
[1]待子而為政:等待您并且讓您去處理國家政事。[2]子將奚先:您打算首先做什么事情?[3]正名:糾正名分上不當的現象。[4]迂:迂腐。[5]聞其殺鳴犢:聽說晉國的趙簡子殺死了竇鳴犢。竇鳴犢,即竇韜,號鳴犢,晉國大夫,提倡德治、教化,反對苛政、殺戮,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施政主張。因政見不合,而被正卿趙簡子殺害。[6]虛左:空著左邊的位置。古代以左為尊,虛左表示對賓客的尊敬。[7]詳味:仔細體味。
【譯文】
子路對孔子說:“假如衛君等著您去處理國政,您打算先做些什么事情呢?”孔子說:“一定先去糾正名分上不當的現象嘛!”子路說:“這有些不切實際吧!這有什么必要去糾正呢?”孔夫子責備子路說他太“魯莽”。當時孔夫子在衛國,此時輒為衛國國君,孔子之所以在衛國停留時間最長,因為輒拒納他的父親回國而奪取了君位,所以孔夫子想糾正他,這里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孔子想去晉國,聽說晉國的趙簡子殺死了鳴犢,到了黃河邊就返回來了,說是晉國殺死了無罪的賢大夫。里名有叫勝母的,因其名不順,曾參拒不進入該里,邑名有叫朝歌的,因為不適時宜,墨子坐著車又回來了,因為邑里的名字不美,兩位賢人都不去那里,為何會有聞名于世的圣人,竟肯居住在父親的國家里,服侍不孝的國君呢?這是可以知道的了。孔子所經過的地方,那里的百姓都得到了感化,沒有得到命令就可以執行,不用言語就可以得到信任,衛出公輒能等待孔子前來為官,應該不是不可改變的下愚之輩。假如衛出公輒用我的話,我一定會用天理引導他,用行動反其本真,命人駕車空著左邊的位置前往迎接他父親并不是難事。如果這樣做就可以挽回道義,豈不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嗎?為此不忍心離去而急切等待著。既然不用我,于是就慷慨離開衛國返回魯國。而衛出公輒的愚昧無知狂悖忤逆,就不能逃脫于天地間了。子路不能詳細玩味孔夫子的圣言,執迷不悟,最終在衛國以身殉難。可惜呀!
【評析】
本篇文章主要講述孔子正名的道理:孔子正名,主要是訂正君主、父子之名,實質就是維護父權和君權,是社會各等級相符,形成道德規范,是所有人都各安其分,各善其事,不越位,不犯上。只有國家禮制完善了,才能更好治理這個國家。孔子認為治國先要糾正名分,并對子路提出的疑問給予否定,并責數之以為“野”。孔子想要去晉國,聽說趙簡子殺死了賢明的鳴犢,臨河而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看重國君是否賢明的。又說道“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曾子認為勝母這個詞語有超過母親的意思,不符合禮儀,所以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說的是,墨子周游到衛國,因為曾為殷紂之都朝歌城,加之靡靡之音,他認為統治者大辦音樂歌舞,沉迷于聲色,其荒淫無度的生活是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剝削和搜刮,所以離開。由此得知,孔子與孟子對君主是否賢明是十分重視的。然而就此提出了為何孔子又會選擇長期停留在一個連自己父親不孝的衛國國君的城里呢?原因在于“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孔子正是看到了這點,才會選擇留在衛國,可見,孔子是多么有遠見啊!但是“輒之冥頑悻亂”且子路不能“詳味圣言,執迷不悟”,最終以身殉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