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下》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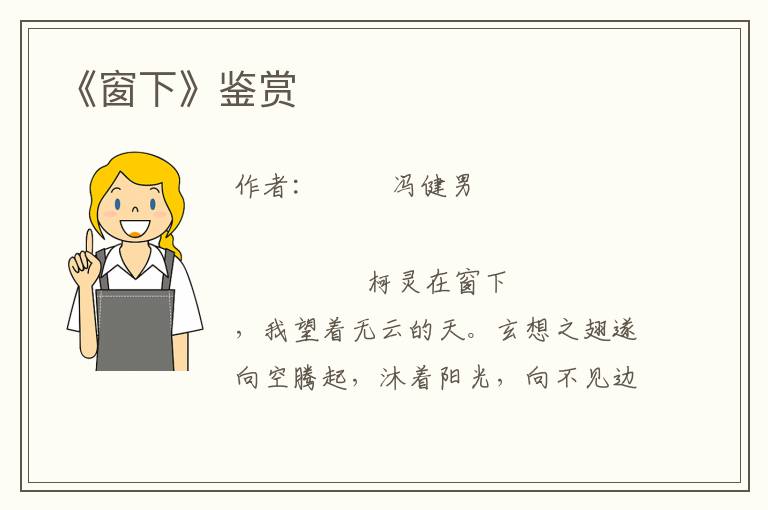
作者: 馮健男
柯靈
在窗下,我望著無云的天。
玄想之翅遂向空騰起,沐著陽光,向不見邊際的藍色飛遠了。
我曾經有孩提的心,駕風舟,泛云海,探索宇宙的奧秘,虹橋彼岸有瑰奇天地;月中宮闕是寶玉砌成;而夏晚小院的涼榻上,我且織過不止一回的摘星之夢。
稍后我又愛獨自仰臥草茵。枕著叢翠,望頂上天幕,對自由闊大的人世,射出向往的箭。
有一次我獨上危樓,正當江南雪后,陽光稀薄,寒氣逼人,天體遼廓如無極。遙望郊外白首的層巒,傲然環立;俯瞰城中密密麻麻的房宇街巷,擠著一堆興廢人事,一種無意義的感嘆,不覺油然而起。忽地,一個斷線的紅色汽球,從近處市廛飛升,我目送它直上太空,又飄飄蕩蕩飛向城外,漸遠漸小,終至于連那微塵似的灰色小點,也從目力中消失。我的不羈的靈魂,也就為它所遠引,覺得天地之寬,而自己則又渺無著落了。
也曾對怒云疾驅,期待著暴風雨的襲來,作海燕之歡舞。
也曾摸索于漆似的暗夜,無風,無星,無月。遠處卻有貓頭鷹詭秘而慘厲的鳴聲,忽而飄來,忽而中斷,如一縷游絲。于是我混身顫悸,為末世的憂懼所威脅……
誰能夠設想沒有太陽的世界將是怎樣的世界呢!
我以想象的彩筆作過兩幅圖畫,一幅是黝黯的牢獄,黑色的墻,黑色的呼吸。鐵鏈如大烏蛇,懶懶地盤在囚徒們的腳下。狹小的鐵檻窗,鑲一張枯瘦如柴的臉,怔怔地望著一角遠天。另一幅是小樓,軒明的靜室,柳絲低垂如簾幕,掩著一窗岑寂。有少婦倚欄,對叆叇的白云搜索逝去的歡樂。她昂著頭,猶如海上鮫人,晶瑩的珠串從象牙似的頰上散落。
命運降苦難于不幸的人群,但希望的種子還孕在人們心里,茁長著新的生命。失去了光的,鐵檻外還有春陽跳躍的大地;失去了愛的,人間也還有廣闊無邊的溫暖。——“生之意志”:這是我為這畫幅所擬想的笨拙的題詞。
磅礴于地球四圍的大氣,曾使古人驚奇于那浩瀚的“大塊文章”;我們則又知道它是一切生物的養命之源。而一自這城市拔去祖國的徽幟,奴隸的惡運卻使人們永遠低頭,不敢再仰望那晶明的蒼穹。偶爾從窗下窺天的人,乃也不禁有囚徒似的哀戚了。
想象著燦然如金的陽光下,是怎樣壯麗的氣象啊,山岳,江河,原野,造物者的不世的杰作!北國的宮殿峨巍,古城頭有白色鴿子,在青空下扇動皎然的雙翼,鴿鈴撒下一把和平美妙的歌聲。但如今滿綴在這些光景上面的,是異族的屈辱的暗影。
魔鬼化成似的灰色蜻蜓,又吐著喤喤的毒咒,從遠天飛近了。
我昂著頭,有鼎沸的思潮,沉重的心。——我夢想著一個狂歡的日子,盈城火炬,遍地歌聲,滿街揚著臂把,挺起胸脯的行人……
一九三九,三,十七。
人之居所設窗,是一大發明。它表現了人的開放意識。門和窗有明確的分工。門為人身的出人提供了方便,而窗為人心的開放準備了孔道。語云,眼睛是人的靈魂之窗。這個比喻既說明人目的性靈,又說明窗口的妙諦。
《窗下》這首散文詩,寫的就是一個具體的人——“我”在特定的環境中立于窗下,“望著無云的天”,鼓起“玄想之翅”而飛遠的情懷。
孩提的心總是飛向無邊的天際,駕風舟,泛云海,過虹橋,探月宮,摘星星,童心如萬里晴空,總是那么的光明、美妙、廣遠!
及至年事漸長,所注目和經心者,就不只是天上,而是還有人世了。然而,人事興廢每每引起“無意義的感嘆”,不及大自然的自由闊大,而且,天也不總是晴朗的,有暴風雨襲來的時候,夜也不總是寧靜和星月交輝的,有令人憂懼和顫悸的暗夜。……
我們讀這首散文詩,讀了多半,還不知道“我”是站在怎樣的“窗下”來窺天和玄想的。這里有“沒有太陽的世界”的設想,有“黝黯的牢獄”的描畫,那么,這是一個囚室的窗下么?
不是,這也只是“我”的“想象”的一部分。作者寫“黑色的墻,黑色的呼吸”,寫“鐵鏈如大烏蛇,懶懶地盤在囚徒們的腳下”,意在呼喚“生之意志”:“失去了光明,鐵檻外還有春陽跳躍的大地”。但這“黑”的“牢獄”還是一種想象,一種象征。
不過,作者是確有囚徒之感的。請看,作品后來寫道:“一自這城市拔去祖國的徽幟,奴隸的惡運卻使人永遠低頭,不敢再仰望那晶明的蒼穹。偶爾從窗下窺天的人,乃也不禁有囚徒似的哀戚了。”原來,“我”是在日軍侵華時已淪陷的城市里發出了“囚徒似的哀戚”。
就是在這“屈辱的暗影”中,這個“從窗下窺天”的“我”,仍然“昂著頭”,“夢想著一個狂歡的日子”,到處是慶祝抗戰勝利的火炬和歌聲。這是生命的強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