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新月集》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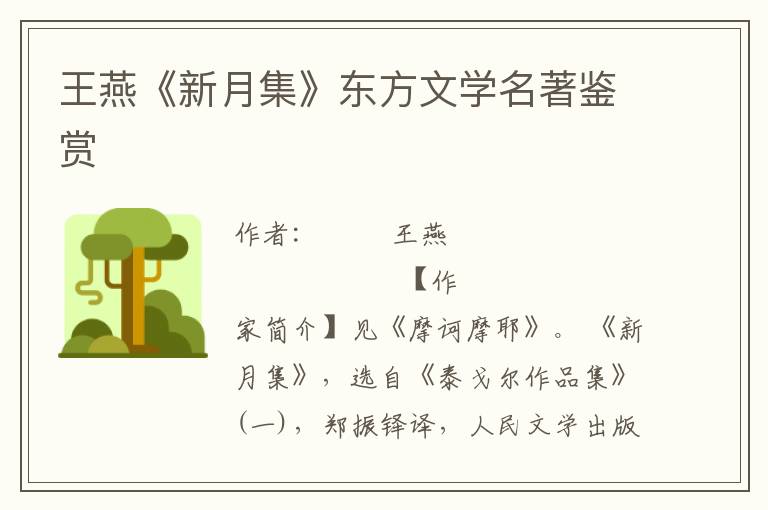
作者: 王燕
【作家簡介】見《摩訶摩耶》。
《新月集》,選自《泰戈爾作品集》(一),鄭振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出版。
【作品節選】
偷睡眠者
誰從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媽媽把她的水罐挾在腰間,走到近村汲水去了。
這是正午的時候。孩子們游戲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池中的鴨子沉默無聲。
牧童躺在榕樹的蔭下睡著了。
白鶴莊重而安靜地立在芒果樹邊的泥澤里。
就在這個時候,偷睡眠者跑來從孩子的兩眼里捉住睡眠,便飛去了。
當媽媽回來時,她看見孩子四肢著地地在屋里爬著。
誰從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去了呢?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她,把她鎖起來。
我一定要向那個黑洞里張望。在這個洞里,有一道小泉從圓的和有縐紋的石上滴下來。
我一定要到醉花林中的沉寂的樹影里搜尋。在這林中,鴿子在它們住的地方咕咕地叫著,仙女的腳環在繁星滿天的靜夜里叮當地響著。
我要在黃昏時,向靜靜的蕭蕭的竹林里窺望。在這林中,螢火蟲閃閃地耗費它們的光明,只要遇見一個人,我便要問他,“誰能告訴我偷睡眠者住在什么地方?”
誰從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只要我能捉住她,怕不會給她一頓好教訓!
我要闖入她的巢穴,看她把所有偷來的睡眠藏在什么地方。
我要把它都奪了來,帶回家去。
我要把她的雙翼縛得緊緊的,把她放在河邊,然后叫她拿一根蘆葦,在燈心草和睡蓮間釣魚為戲。
當黃昏,街上已經收了市,村里的孩子們都坐在媽媽的膝上時,夜鳥便會譏笑地在她耳邊說:
“你現在還想偷誰的睡眠呢?”
孩子的世界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凈地。
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說話,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呆呆的云朵和彩虹來娛悅他。
那些大家以為他是啞的人,那些看去像是永不會走動的人,都帶了他們的故事,捧了滿裝著五顏六色的玩具的盤子,匍匐地來到他的窗前。
我愿我能在橫過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脫了一切的束縛;
在那兒,使者奉了無所謂的使命奔走于無史的諸王的王國間;
在那兒,理智以它的法律造為紙鳶而飛放,真理也使事實從桎梏中自由了。
花的學校
當雷雨在天上轟響,六月的陣雨落下的時候,
潤濕的東風走過荒野,在竹林中吹著口笛。
于是一群一群的花從無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來,在綠草上狂歡地跳著舞。
媽媽,我真的覺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學校里上學。
它們關了門做功課。如果它們想在散學以前出來游戲,它們的老師是要罰它們站壁角的。
雨一來,它們便放假了。
樹枝在林中萬相碰觸著,綠葉在狂風里蕭蕭地響,雷云拍著大手。這時花孩子們便穿了紫的、黃的、白的衣裳,沖了出來。
你可知道,媽媽,它們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
你沒有看見它們怎樣地急著要到那兒去么?你不知道它們為什么那樣急急忙忙么?
我自然能夠猜得出它們是對誰揚起雙臂來:它們也有它們的媽媽,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媽媽一樣。
【作品鑒賞】《新月集》是泰戈爾的著名英譯散文詩集,所收詩作大部分選自詩人的孟加拉文詩集《兒童》并由他本人譯成英語,1913年由英國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發行。詩集問世后,很快被轉譯為多種文字,風行于許多國家和地區。
《新月集》的原始底本《兒童》出版于1903年,這些詩篇寫作之時正值泰戈爾連遭不幸命運的打擊——先有愛妻辭世,繼之痛失幼女——沉浸于巨大精神痛苦的非常歲月。詩人強忍悲慟,從孩子們稚氣的游戲中尋求精神慰藉,在孩子們天真的話語中淡化自己的哀思。與此同時,他又從自己兒時的體驗里汲取素材,更從眼前的情境中激發靈感。將上述種種訴諸于筆端,便有了被譽為世界兒童詩精品的《新月集》。可以認為,《新月集》是泰戈爾有感而發,直抒胸臆的產物,它向世人展現著詩人痛定思痛心態下的精神軌跡。
《新月集》中,詩人使自己處于孩子的心靈之中,以清新恬淡的風格對天真稚氣的兒童、潔白無瑕的童心、溫柔熱烈的母愛以及純凈自然的兒童世界均進行了禮贊謳歌。詩作以寧靜夜空下高懸在點點繁星之間的一彎新月作為未曾遭受權勢、金錢污染的兒童心靈的象征性喻體,進而將“生命正是青春”的孩子祝頌為具有“潔白的靈魂”的天使,孩子們生活其間的那“纖小的新月的世界”則不啻為“一切束縛都沒有”的自由王國。在孩子面前,人的心靈能夠得到撫慰,情感能夠得到凈化,罪惡可得消解,真理亦可得以昭揚。總之,成人生活中熱切向往而又無可企及的理想,在兒童的世界里都是不難實現的現實。所以,詩人切盼著自己能夠和孩子們感情相共,心息溝通,希冀著能在掙脫權力、金錢、美色和物欲的桎梏之后,在兒童的世界里作一個自由的人。
誠然,《新月集》是部兒童詩集,但卻不能全然視為寫給兒童的詩作。正如有位論者述說的,這是詩人進入孩子的心靈,展現他們的內心世界的詩作,是“充分體現出詩人對兒童心理深刻的理解和善于用兒童無邪的眼睛和心靈來觀察自然,感受生活的特點,充滿童稚的想象和純真的感情的優美動人的詩集”(石真《新月集·飛鳥集》序言)。在談及《新月集》的特點時,我國詩人郭沫若曾作如是之說:“第一是詩的容易懂,第二是詩的散文式,第三是詩的清新雋永。”(《沫若文集》卷十:《太戈兒來華之我見》)
《新月集》共收入散文詩37首,這里選了3首。
《偷睡眠者》一詩,訴諸于讀者的是幅溫馨恬淡的風情畫。正午時分,“池中的鴨子沉默無聲”,“牧童躺在榕樹的蔭下睡著了”,連白鶴也安靜地立在泥澤里,這是怎樣一個靜寂啊,可謂萬籟無息。年輕的母親“走到近村汲水去了”,回來時,卻發現安睡的孩子“四肢著地地在屋里爬著”,他被偷去了睡眠。
“誰從孩子的眼睛里把睡眠偷去了呢?我一定要知道”。短短的詩行中曾數度發出這般設問,抒情主人公也一直在尋覓著答案卻終未釋示其疑。然而,只要細讀全詩,便會發現“偷睡眠者誰”的問題早已昭然于字里行間——是美景,是良辰,既是那“醉花林中沉寂樹影里”鴿子的鳴唱,也是那“靜靜的蕭蕭的竹林”中螢蟲的閃光,一言以蔽之,偷睡眠的是美麗神奇的大自然。對于孩子來說,夢幻即現實,現實亦夢幻,周圍的一切無不莫測神奇、情趣盎然,無論是鳥叫蟲鳴、晨光夕暉,還是牧童的葦笛、媽媽的水罐,亦或山溪的泉洞、滴水的滑巖,哪樣不讓他興奮不已?又有哪樣不能“偷”去他的睡眠?想和鴿子一道飛,同鴨子一塊游,像螢火蟲那樣閃光,像溪水那樣流淌,干嘛不變成水罐,讓媽媽抱在懷里?四肢著地滿屋爬,越想越著迷,其實,偷睡眠的又是孩子自己。我們哪個人在那樂趣無窮的孩提時代,沒在無盡的遐思中丟失過睡眠呢?
《孩子的世界》一詩曾被郭沫若推為兒童文學創作的摹本和典范,在《兒童文學之管見》(《沫若文集》卷十)一文中有如下論斷:“此世界中有種不可思議的光,窈窕輕淡的夢影;一切自然現象于此都成為有生命、有人格的個體;不能以‘理智’的律令相繩,而其中自具有赤條條的真理如像才生下地來的嬰兒一樣。”確然,孩子的世界是美好的,讓人心向神往。言其好,就好在它的純凈,心是無憂無慮的童稚,人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在孩子的世界里,世界是孩子的。
泰戈爾筆下,孩子的世界是理想的樂園,圣潔純正、透澈清靈,足以使“那些大家以為他是啞的人,那些看去像是永不會走動的人,都帶了他們的故事,捧了滿裝著五顏六色的玩具的盤子,匍匐地來到”此間,作出生命的奉獻,為使自己也像孩子一樣純潔,詩人企盼著能在“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凈地”,“能在橫過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脫了一切的束縛”。這般詩句,一則告白著詩人的理想追求在向著生命的初始階段認同回歸,同時也標識出泰戈爾在現實生活中因希望之無望而產生的孤寂失落。恐怕詩人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深受污濁浸染,久歷腐敗滄桑的世人們決然無法像孩子那樣在生死、善惡以及歡樂與哀愁之間只擁有前者。孩子的世界所以令人神動,童稚情性所以讓人心怡,其原因也許蓋在于人間世相皆難純凈如斯。無疑,對孩子世界的歌贊寄寓著詩人凝重的哲理沉思,這支心曲的底蘊卻是對現實人生的失望和感傷。仔細品悟,將孩子的世界這方唯屬于孩子的凈土作為理想之所在,大可視作一種含淚的調侃。
《花的學校》是首致趣盎然的小詩,寫一個孩子面對著六月雨后的原野,觸景生情,入于遐思。詩分四節,分別記述了孩子的所見、所覺、所想、所說,讀來令人忍俊不禁,耳目亦能為之清新。在孩子眼里,茵茵綠草、簇簇繁花,全都是“穿了紫的、黃的、白的衣裳”的孩子;在孩子的腦子里,花孩子的家在天上,在地下的學校里讀書,也要做功課、做游戲,淘氣罰站,雨天不上學;在孩子的話語里,花孩子“也有它們的媽媽,就像我有自己的媽媽一樣”,由己及物,情意篤誠。詩作從孩子的視角觀察,用孩子的方式思考,以稚氣的童聲寫就,活托出了一顆靈透清純、自然天真的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