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仁山銘》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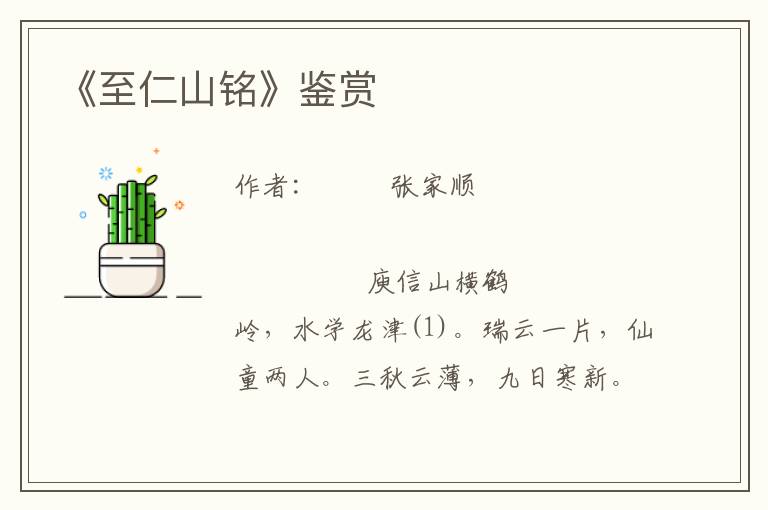
作者: 張家順
庾信
山橫鶴嶺,水學龍津(1)。瑞云一片,仙童兩人。三秋云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檐枕嶺。壁逸藤苗,窗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疏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晉宋以來,人們對山水自然美的發現、觀賞,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他們受玄學的影響,以虛靈的胸襟去體會自然,逐漸形成了如司空圖《詩品》所形容的“空源寫春、古鏡照神”那樣澄澈空明的藝術心境。以此種心境觀照自然,便能常常得其真趣,寫出極有神韻的山水畫圖。
《至仁山銘》要為山勒銘,便需從深層把握山之特質,賦予它一個靈魂。作者緊緊扣住一個“仁”字。要寫出“仁”的品格,當然會記起孔老夫子“知者動,仁者靜”的格言。所以作者便通過一個個畫面來渲染至仁山的靜謐安詳。這些畫面看似靜止而孤立,實則彼此呼應互相映襯,表現出一種宇宙秩序的圓滿與和諧。開頭兩句總寫至仁山山水之奇;仙人王子喬駕鶴云游到此不能不息駕,水中魚龍莫不欲躍入此神境而不可得,給此山此水平添一段神秘。接下兩句更將它虛靈化;瑞云祥集、神仙所居!接下四句,將此山置于特定的秋日氛圍中,尤顯得澄澈、寒肅,清凈、光潔。再下六句則寫仁人高士之所居,表現出這些仁人高士極善于領會自然之趣,亦極善于借助自然之勢,他們極力追求著天人合一,物我融匯的境界;臺階傍著山石、飛檐聳立嶺下,青滕繞著屋舍,竹影映于倚窗,寒潭上飄著菊花,山井中映著疏相之影,多么清雅,多么自然!這般意境的創造,當不讓于王維的輞川詩。最后兩句點題,把“仁”與“靜”聯系起來,賦予這個畫面以深邃的哲理意味。
全篇都是寫景,然而作者的情懷真切可感,因為作者所取的景色無不帶著作者的審美興趣,無不表現他的情志追求。作者所欣賞、所追求的“靜”,是這山水畫圖的靈魂。在這個“靜”字里面,包涵著極豐富的內涵。有對世俗紛爭的厭倦,也有對天人關系的妙悟等等,不過作者都把它們化為蘊含在畫面中的情緒信息暗中發散出來,讓人去意會去感受。
清人許梿對此篇有“有語必新,無字不雋”的評價。不過,我覺得本篇之煉,主要恐怕還不在字句上,它的“新”、“雋”之處主要在畫面的選取與組接,以及意蘊的構成方面,字句之“新”“雋”不過在于能簡煉地傳達它內在的意蘊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