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xué)與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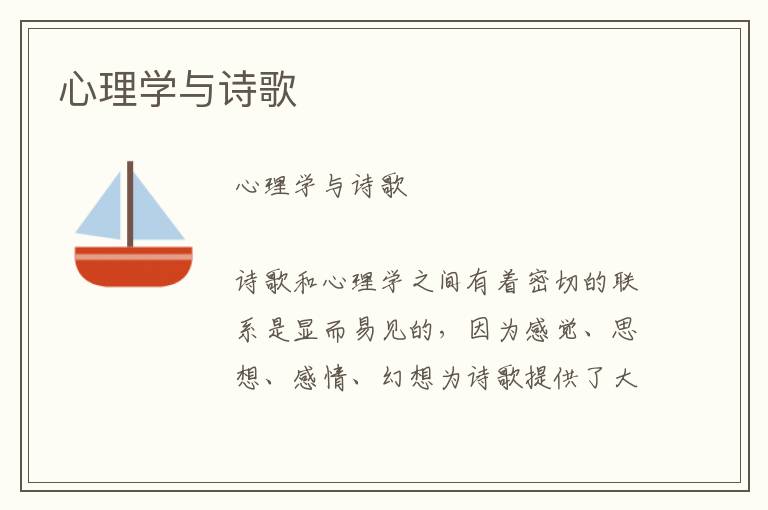
心理學(xué)與詩歌
詩歌和心理學(xué)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感覺、思想、感情、幻想為詩歌提供了大部分必不可少的素材,因為精神活動作為對詩歌產(chǎn)生反應(yīng)的機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們對這兩者密切聯(lián)系的程度以及心理學(xué)在詩歌批評中的應(yīng)用范圍,卻不甚明確。這是因為很難劃出詩歌或心理學(xué)的界線。如果把一切內(nèi)心活動的內(nèi)容和過程,都看作是精神活動的話,那么現(xiàn)實中可以被認(rèn)識的一切就都是精神活動了,詩歌的每個方面在原則上也都可能成為心理學(xué)研究的主題了。事實上,凡是尊重“精神的現(xiàn)實”的批評文章,從廣義上講,都可以說是心理學(xué)批評。心理學(xué)與詩歌的聯(lián)系是錯綜復(fù)雜的。當(dāng)弗洛伊德為了命名一個心理學(xué)概念“奧狄浦斯情結(jié)”(戀母情結(jié))時,他轉(zhuǎn)向富于戲劇性的古代詩歌,從中找到了這個名稱。他正是從文學(xué)和神話中推衍出了心理學(xué)概念。關(guān)于奧狄浦斯的故事以及弗洛伊德從中看到的意義模式不僅存在于這個科學(xué)概念之前,而且也帶上了神話的色彩。同樣復(fù)雜的是,許多從心理角度對詩歌所作的重要評論,都是在論述文學(xué)藝術(shù)的著作中偶爾述及的,而不是在研究詩歌的著作中專門論述的。因此可以認(rèn)為心理學(xué)所描寫的是任何形式的精神活動的性質(zhì)。下面主要談?wù)勁u界自覺運用實驗心理學(xué)對詩歌性質(zhì)所作的各種研究。
每個時代的心理學(xué)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人類精神活動的作用提出自己的見解,這種見解或者為詩人所采用,或者為詩人所反對。了解詩人所處時代在心理學(xué)方面的見解,會有助于說明詩歌作品。例如,知道伊麗莎白時代關(guān)于靈魂的看法有助于解釋莎士比亞的作品。又如,讀過W·詹姆斯的《心理學(xué)原理》(1890),了解這部書對“意識流”的見解,就有助于說明現(xiàn)代詩歌和小說。然而,J·L·洛斯對柯爾律治的研究表明批評并非一定要借助于心理學(xué)這樣一個系統(tǒng)化的學(xué)科,批評本身就能對詩人的心理活動提出許多見解。大部分運用心理學(xué)闡明詩歌的批評論述都是從精神分析學(xué)當(dāng)中派生出來的;文學(xué)界注意這一學(xué)說是在S·弗洛伊德于1900年發(fā)表《夢的解析》以后開始的。精神分析學(xué)反映了歷史的、也是文學(xué)研究的一個重要時刻。K·伯克曾說:“在產(chǎn)生偉大戲劇的時代,觀眾理解劇中人物為什么要采取他們所采取的行為。”H·J·馬勒也曾講過:“穩(wěn)定的文化產(chǎn)生穩(wěn)定的和標(biāo)準(zhǔn)的行為模式;行為動機也和生活方式一樣帶有社會性。雖然劇中人物可能在短暫的時間里會感到迷茫、困惑甚至產(chǎn)生逆反心理,但是他們最終會和觀眾一樣清楚地認(rèn)識到他們的動機。”在文化崩潰的時期,當(dāng)D·H·勞倫斯等小說家和詩人宣稱應(yīng)把注意力從“舊有的、穩(wěn)定的自我”轉(zhuǎn)向同一精神成分的“同素異形現(xiàn)象”時,弗洛伊德的學(xué)說在提供一種新的社會化動機上就顯得異常重要。而且,精神分析學(xué)也使得文學(xué)批評家能集中研究詩歌創(chuàng)作和反應(yīng)當(dāng)中一些過去未曾受到注意的成分。
雖然弗洛伊德偶爾也寫過一些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的論述,但是精神分析學(xué)中關(guān)于文學(xué)的理論大都來自他在對宗教史、文化史、戲謔、失言、神秘事物,特別是夢境方面進(jìn)行分析時所作出的一些提示。弗洛伊德通過對夢的解析分析文學(xué)及其他精神產(chǎn)物的途徑,也部分地被L·蒂克、A·叔本華、J·保羅、F·尼采、F·菲舍、W·狄爾泰等人所采納。他們發(fā)現(xiàn)在做夢與文藝創(chuàng)作之間存在著類似的情形。按照精神分析的觀點,做夢使人的本能性沖動獲得幻覺性的滿足,而藝術(shù)則占領(lǐng)著“愿望難以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世界與實現(xiàn)愿望的幻想世界之間的地帶”(弗洛伊德)。像做夢一樣,藝術(shù)作品不僅有表達(dá)于外的明顯內(nèi)容,而具有隱藏于內(nèi)的潛在內(nèi)容,后者來源于充滿本能的潛在意識,而且早期的精神分析式批評當(dāng)中很大一部分的目的就在于提示文學(xué)作品中具有活力的潛在內(nèi)容。因此,弗洛伊德和后來的E·瓊斯,都把《哈姆雷特》看作是表現(xiàn)主角的亂倫戀母愿望和對父親的矛盾心理,認(rèn)為這部作品所取得的戲劇和詩歌效果是通過在觀眾心理上引起和表現(xiàn)戀母情結(jié)而達(dá)到的。按照這種觀點,語言的意義主要是用以滿足內(nèi)心世界對感覺及邏輯推理的需要,因此就要減輕對被禁止的愿望的反對,容許滿足這些愿望。正如N·霍蘭德在《關(guān)于弗洛伊德理論的概述》(1966)一書中指出的那樣,“藝術(shù)形式的真正樂趣來之于不合邏輯和荒謬無理的事物,而這些事物又反過來表現(xiàn)了‘精神活動的省力原則或者是表現(xiàn)了從理性壓制下解脫出來的輕松狀態(tài)’。我們的快感來之于使我們保持正常邏輯理性的精力獲得放松或減輕;我們都體驗過突然精力有余的感覺,體驗過節(jié)省精力突然在精神上所獲得的裨益。”
近期的文學(xué)批評反映了從20世紀(jì)20年代以來弗洛伊德創(chuàng)始的精神分析學(xué)在理論上的發(fā)展,主要的研究者有:A·弗洛伊德、H·哈特曼、E·克里斯、M·克萊因等。這些發(fā)展所關(guān)注的主要是:自我為了維持本身活動以及為了在內(nèi)外因素的作用下取得某種可行的平衡的力量。精神分析式的文學(xué)批評反映了這些興趣,它開始把文學(xué)作品不僅看作是隱蔽地表達(dá)被禁止的愿望,而且看作是反映“自我”在應(yīng)付處理這些愿望與對待覺察到的道德感時所采取的不同程度的策略性方式方法。因此,文學(xué)作品表達(dá)出來的明顯內(nèi)容反映了潛在意識中幻想的轉(zhuǎn)化;作品的形式和意義,不僅是對潛在幻想的掩飾,而且服務(wù)于這種轉(zhuǎn)化過程。藝術(shù)能使人們的精神活力實現(xiàn)從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的轉(zhuǎn)變,這種轉(zhuǎn)變的本身就能給人以快感。而且這些轉(zhuǎn)化和轉(zhuǎn)變與潛在意識的非理幻想成功地進(jìn)行升華的過程非常相似。正像霍蘭德指出的,文學(xué)形式“對我們起著防護(hù)自衛(wèi)的作用——它分裂、隔離、破壞、轉(zhuǎn)移、消除(通過抑制或否定)幻想中快樂的但引起焦慮的因素”。精神分析學(xué)涉及詩歌形式的重要概念有“凝聚”(即一個形象或角色具有不同的心理傾向)和“轉(zhuǎn)移”(即一種心理傾向具有不同的具體表現(xiàn),如弗洛伊德認(rèn)為麥克白夫婦屬于同一心理傾向但具體表現(xiàn)不同)。
有一部分精神分析式文學(xué)批評被稱作“心理傳記”——即運用精神分析學(xué)或心理動力學(xué)的觀點和方法評述某個人的生平。在運用這種方法寫作的一些文學(xué)性傳記中,如B·邁耶的《約瑟夫·康拉德傳》,確實令人信服地窺見了作家生活及作品中不為人知的隱蔽部分。有人曾以這種方法對幾位詩人進(jìn)行過分析,包括M·波拿巴對愛倫·坡、J·科迪對E·狄更生的分析;科迪就是根據(jù)精神分析學(xué)理論和精神病臨床理論作出結(jié)論的。以精神分析理論作精密的聯(lián)想研究可見于P·德特林對R·M·里爾克的分析;他不僅把詩人的創(chuàng)作動機追溯到傳統(tǒng)的戀母情結(jié),而且追溯到近幾十年來精神分析所探討的前戀母階段的發(fā)展。里爾克的“自戀欲”被看作是一種復(fù)雜的誘發(fā)性模式,表現(xiàn)為一組復(fù)雜的、可變的、展開的詩意象征,其中包括“天使”這個象征。克利斯、霍蘭德、A·埃倫茨韋格等研究者,近年來以比前輩批評家更加微妙的方式探討文學(xué)感應(yīng)的問題。精神分析學(xué)現(xiàn)在已經(jīng)接觸到一些尚待探索的領(lǐng)域,可能對詩歌批評有重大的意義,例如,由J·A·M·梅爾洛所提出的未發(fā)展的預(yù)感,即詩歌節(jié)奏表達(dá)出有機體幼兒時期的古老反應(yīng),表達(dá)出固有的生物信號密碼。另一個領(lǐng)域是由H·科胡特提出的,他認(rèn)為自戀欲預(yù)示著自我發(fā)展并形成這種發(fā)展的基礎(chǔ);自戀欲還含蓄地見之于某些創(chuàng)作活動的形式及其所受到的干擾。還有一個領(lǐng)域是埃倫茨韋格提出來的,他注意到一些有助于形成藝術(shù)形式的、超出意識控制的整理排列過程。而且,精神分析學(xu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能夠?qū)Ω鞣N重要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提出了某種心理學(xué)方面的解釋,在這點上是沒有其他學(xué)派可以與之匹敵的。
除了弗洛伊德,從心理學(xué)角度進(jìn)行批評的著名人物是榮格。和弗洛伊德不同,他的主要興趣是文學(xué)中的超個人因素;而這一興趣的重點是精神原型。因為精神原型大體上相當(dāng)于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形相因(本質(zhì)性起因)而與動因(近存性起因)不同,后者是精神分析學(xué)文學(xué)批評的對象。所以精神原型這一概念可以有助于心理學(xué)批評家溝通詩歌結(jié)構(gòu)的較低層次與較高層次。榮格認(rèn)為,詩人有預(yù)卜先知的能力;他對藝術(shù)的觀點使他與柏拉圖、錫德尼和強調(diào)詩歌與預(yù)言關(guān)系的浪漫主義流派批評家一脈相承。他對精神活動的過程持預(yù)見論或定命論的觀點,他認(rèn)為潛在意識是由群體因素共同組成的,這就使他對詩人和潛意識的關(guān)系有著與精神分析學(xué)不同的解釋。M·博德金認(rèn)為,能夠?qū)ψ髌返男问郊捌鋵ψx者的效果作出解釋的主要是精神的形式創(chuàng)造力和它的神秘表現(xiàn)力。因此,藝術(shù)主要不是通過部分地解除壓抑感而獲得效果的;相反,藝術(shù)家經(jīng)常表達(dá)的內(nèi)容是在潛意識中已經(jīng)充分形成而尚未被“意識”所知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具有補償?shù)男再|(zhì),不僅為詩人也為其時代提供了糾正片面性世界觀所必需的材料。
藝術(shù)家可能確有精神病理學(xué)所分析出來的特點,但這個事實不能用來解釋他的作品;從精神分析學(xué)的觀點來看,作品是通過加強自我對威脅自我的力量的控制來為自我服務(wù)的。相反,榮格認(rèn)為藝術(shù)家經(jīng)常處于苦惱之中,因為他的天才和職責(zé)要求對某些心理功能進(jìn)行超乎尋常的發(fā)展,從而忽視了對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義的其它功能。T·舒安納曾采用榮格關(guān)于精神的這種觀點對T·S·艾略特的詩歌進(jìn)行了分析(1971)。G·霍夫曾對“詩歌與精神”作過更一般化的論述。舒安納還曾試圖闡明文學(xué)批評和分析心理學(xué)對“精神原型”這一術(shù)語的使用問題(1970)。榮格派的觀點對文學(xué)批評似乎比對文學(xué)性傳記的分析更加適用,但K·威爾遜卻運用榮格的觀點對濟慈的《夜鶯頌》進(jìn)行了深入的探討,并闡明它在濟慈一生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意義。在她看來,這首詩歌是以自我對精神原型的體驗、對個性最深層的中心的體驗為基礎(chǔ)的,這種體驗導(dǎo)致濟慈在詩歌觀點上的轉(zhuǎn)變,導(dǎo)致他與他本身的靈感泉源之間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威爾遜還運用榮格關(guān)于心理態(tài)度的類型和功能的學(xué)說闡明了濟慈詩歌語言的獨特性質(zhì)。G·巴舍拉爾根據(jù)榮格的學(xué)說創(chuàng)立了局部上超越個人的“靈魂現(xiàn)象學(xué)”。他認(rèn)為,詩歌的意象是“夢境意識”的產(chǎn)物;在這種意識狀態(tài)下,“主觀與客觀的二重性一直在不停地轉(zhuǎn)化,閃爍著彩虹般的光彩。”
K·科夫卡等形態(tài)心理學(xué)家的觀點有時也曾被批評家采用(如穆勒),不過在文學(xué)討論中還不常見。在繼續(xù)和擴大形態(tài)心理學(xué)關(guān)于認(rèn)知作用的全面性質(zhì)研究中,M·佩卡姆提出了關(guān)于藝術(shù)(包括詩歌在內(nèi))的一種綜合性觀點。他認(rèn)為,人“最向往的是一個可預(yù)見的、有序的世界……由于人對那樣一個世界的向往非常強烈,因此他必然會排斥任何關(guān)于他的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預(yù)言,拒絕任何對于他的努力方向的誤導(dǎo),反對任何對于他的信念的懷疑。只有當(dāng)他受到保護(hù)的情況下,即由精神絕緣的高墻把他同外界隔絕的情況下,他才可能認(rèn)識到他的興趣(即他的期待或目標(biāo))和他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影響下所形成的思想之間的差別”。佩卡姆認(rèn)為,藝術(shù)的功能就在于提供這樣一種體驗。J·O·洛夫則根據(jù)發(fā)展認(rèn)知心理學(xué),分析了V·伍爾夫小說中的神話性特征。心理語言學(xué)也被應(yīng)用于詩歌批評。由于詩歌充滿著對人世狀態(tài)的洞察,能激起某種情緒,并提供對待這些情緒的方式,所以詩歌也被用作精神療法的一種手段。但是精神療法中強調(diào)的主要是詩歌與散文同樣具有的撫慰和教誨性質(zhì),而不是使詩歌具有虛擬性而非直陳性的預(yù)示性質(zhì);所以文學(xué)研究者不會從中學(xué)到什么東西。
做夢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及反應(yīng)之間潛在的相似之處對文學(xué)批評有著持續(xù)的影響。例如伯克和N·弗賴伊仍然在批評中使用“夢境”這個術(shù)語。自弗洛伊德以后,對做夢的解釋也不斷發(fā)展變化。進(jìn)行過這方面研究的有榮格、A·阿德勒、E·S·陶伯、K·霍尼、B·S·羅賓斯、E·弗羅姆、W·博寧等等,他們的觀點對一些心理學(xué)批評都有很大助益。因此,榮格認(rèn)為:“夢境是自我對抗的一種體驗,其目的是揭示而不是掩蓋。其中存在的象征性事物不是作為欺哄或虛飾,而是作為比喻性的參照。”按照榮格關(guān)于夢的觀點,對弗洛伊德關(guān)于夢的潛在內(nèi)容和明顯內(nèi)容的差別基本上可以不予考慮;對夢的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都不能看作是隨意的,而應(yīng)看作為支配戲劇性材料的一種必要條件;所以夢的功能不能看作主要是為了實現(xiàn)愿望,而是通過對一種片面的、有意識的觀點加以補償而對精神活動進(jìn)行自我調(diào)整并且使人格保持統(tǒng)一完整。阿德勒等學(xué)者指出,“不借助認(rèn)為潛意識是進(jìn)攻性及性本能沖動的儲藏所這種概念也能保留夢的能動意義。……夢境奇特的思想活動可以理解為個人經(jīng)歷的一種奇特表達(dá)方式,而不是潛意識思想方式的突然迸發(fā)。”(厄爾曼)這些似乎可以與古代認(rèn)為夢和詩歌相類似的看法聯(lián)系起來,更一般地說,可以與詩歌和有關(guān)幻想這個詩歌的基本因素的來源、性質(zhì)和功能等問題聯(lián)系起來。這些觀點中有一部分在文學(xué)研究中得到的反響很小,這可能表明在運用心理學(xué)觀點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方面的可能性尚待進(jìn)一步探索。
榮格曾指出,每一個心理學(xué)觀點都包含著一種主觀自白的重要成分,而現(xiàn)在還不可能產(chǎn)生出為人們所公認(rèn)的統(tǒng)一心理學(xué)。但是總的來說,在批評界中,對于心理學(xué)與詩歌之間關(guān)系的探討已經(jīng)成為一個富有成果、業(yè)已確立的研究領(lǐng)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