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火》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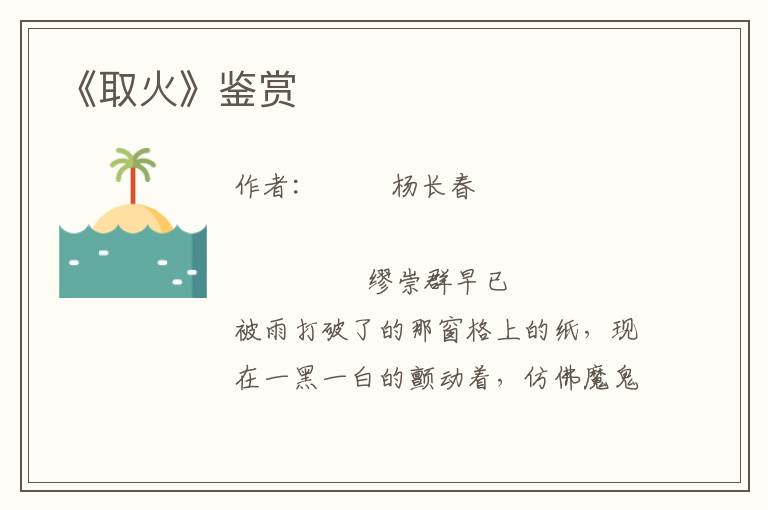
作者: 楊長春
繆崇群
早已被雨打破了的那窗格上的紙,現(xiàn)在一黑一白的顫動著,仿佛魔鬼在空的房里眨著眼。
還沒有落盡的枯葉,寂寂地掛在槎枒上。不知哪里吹來的一陣風,它們全體抖擻著,我隔著玻璃望見了:如同急驟的淚珠,縱橫地流在蒼白的天底面頰上。
凍紅的鼻子,縮短了的頸子,和從口里噴出來的那一股一股白蒸氣,很足構成一幅圖畫的景色了。
風吹過了電桿,磁瓶,樹梢,是尖尖的哨子,或是猛烈的呼號,都給寒冷的進行曲做了一種伴奏。
盤旋在灰色的空中的幾只老鷹,不知為什么啁啾地叫得那般凄愴。我想起了那永不則聲的白熊;也想起了那不分晝夜,奔馳在西伯利亞原野上的狼群了。
冰、雪給大地披上一件最潔凈的喪衣。
“讓一切的回憶,一切的愛、恨、思、怨,都永遠地埋葬在它的下面,恬靜地不再復蘇罷!”我獨自喃喃著,祈禱著,可是遠不及自然默默著來得沉痛與偉大。
有許多的日子我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一盆火的前面,(我不記得它是我取來的,還是誰送了來的。)先是有著咝咝的聲音,不久又發(fā)出一種清脆的迸裂響。幾塊煤或木炭,好象自成一所建筑,但不久就坍倒了,崩陷了,成了一堆象骨骼樣的灰燼。短短的過程中,世界也轉變成另外的一個了。
能流動的水,都凝結了。血沒有停滯的緣故,那是為了心還是溫暖的。愛,永恒地是火的燃物!給我火,給我光,我就會幸福,就會創(chuàng)造出幸福來。
一九四二,一,六。
繆崇群不足40歲的人生道路十分坎坷,個人遭遇不能不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基調。而且他生逢的那個時代正是中國社會動蕩不安、發(fā)生劇變的年代。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具有特定的心態(tài)。通過《取火》這篇短文,可以看出那個時代一種常見的情緒:身外世界作為一種異己力量對自身的擠壓,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不滿、詛咒,進而尋求一種獨特的解脫方式來抵制這殘酷的外部世界。
作品開頭以相當篇幅表現(xiàn)了作者對現(xiàn)實的感受。這里,一個個場景令人感到猙獰、悲涼、凄厲:窗格上破紙的顫動,“仿佛魔鬼在空的房里眨著眼”;樹上枯葉在風中的抖擻,“如同急驟的淚珠,縱橫地流在蒼白的天底面頰上”;人們在嚴冬中的瑟縮和寒風尖利的呼嘯,匯成了寒冷的進行曲;等等——在作者心中,世界是如此陰冷,如此充滿敵意。應當說,這不僅僅是對自然環(huán)境的描寫,其中更多的是外部的社會環(huán)境在作者心中投下的陰影。
當心靈過于壓抑的時候,人們便不能不尋求著忘卻。看到冰雪對大地的覆蓋,作者衷心地祈禱著:“讓一切的回憶,一切的愛、恨、思、怨,都永遠地埋葬在它的下面,恬靜地不再復蘇罷!”然而,這是不可能的。而在寒冷中尋求溫暖恰恰是人們的另一種本能。顯然,只有火的溫暖才能驅散這世界帶給自己的冰涼陰冷。于是,作者想起他獨自向火時的感受了,他情不自禁地呼喚著:“給我火,給我光,我就會幸福,就會創(chuàng)造出幸福來。”
作者所呼喚的火當然別有深意。他認為,火的溫暖其實來源于愛:“愛,永恒地是火的燃物!”作者最終發(fā)出的乃是對愛的呼喚。對于不滿現(xiàn)狀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現(xiàn)代知識者而言,無奈中也只有發(fā)出這種呼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