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經法》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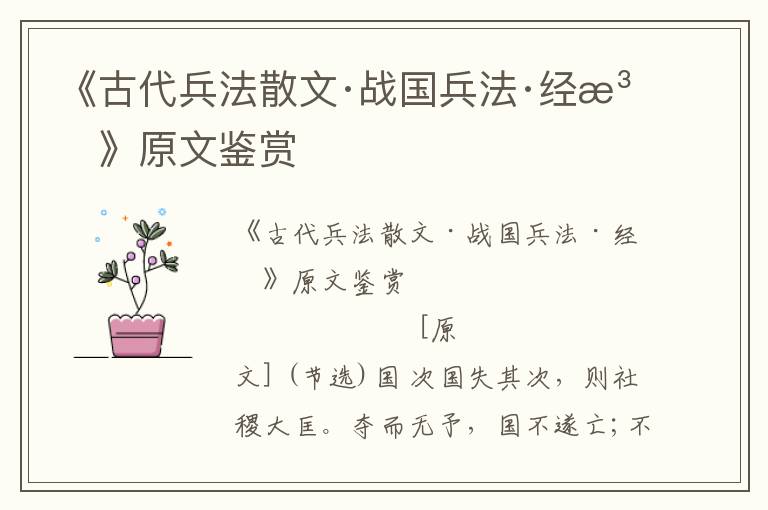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經法》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國 次
國失其次,則社稷大匡。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伐當罪當亡,必虛(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胃(謂)天功。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天地立,圣人故載。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人強朕(勝)天,慎辟(避)勿當。天反朕(勝)人,因與俱行。先屈后信(伸),必盡天極,而毋擅天功。
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郎(廓)廟,聽其鐘鼓,利其資財,妻其子女,是胃(謂)□逆以芒(荒),國危破亡。故唯圣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故圣人之伐殹(也),兼人之國,隋其城郭,棼(焚)其鐘鼓。布其資財,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以封賢者,是胃(謂)天功。功成不廢,后不奉(逢)央(殃)。
毋陽竊,毋陰竊,毋土敝,毋故執,毋黨別。陽竊者天奪[其光,陰竊]者土地瓦(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執者流之四方,黨別[者]□內相功(攻)。陽竊者疾,陰竊者幾(饑),土敝者亡地,人執者失民,黨別者亂,此胃(謂)五逆。五逆皆成,□□□□,□地之剛(綱),變故亂常,擅制更爽,必欲是行,身危有[殃。是]胃(謂)過極失當。
君 正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無賦斂,則民有得。四年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則朕(勝)強適(敵)。俗者,順民心殹(也)。德者,愛勉之[也。有]得者,發禁(弛)關市之正(征)殹(也)。號令者,連為什伍,巽(選)練賢不宵(肖)有別殹(也)。以刑正者,罪殺不赦殹(也)。□□□□□□□□殹(也)。可以正(征)者,民死節殹(也)。若號令發,必廡而上九,壹道同心[上]下不?,民無它志,然后可以守單(戰)矣。號令發必行,俗也。男女勸勉,愛也。動之靜之,民無不聽,時也。受賞無德,受罪無怨,當也。貴賤有別,賢不宵(肖)衰也。衣備(服)不相逾,貴賤等也。國無盜賊,詐偽不生,民無邪心,衣食足而刑伐(罰)必也。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 (攻),反自伐也。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 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并行,則天下從矣。
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恥,有恥則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則守固單(戰)朕(勝)之道也。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治之安。無父之行,不得子之用; 無母之德,不能盡民之力,父母之行備,則天地之德也。三者備則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桀(杰)票(驃)雄,則守御之備具矣。審于行文武之道,則天下賓矣。號令闔(合)于民心,則民聽令。兼愛無私,則民親上。
亡 論
守國而侍(恃)其地險者削,用國而侍(恃)其強者弱。興兵失理,所伐不當,天降二央(殃)。逆節不成,是胃(謂)得天。逆節果成,天將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贏極必靜,動舉必正。贏極而不靜,是胃 (謂)失天。動舉而不正,[是]胃(謂)后命。大殺服民,戮降人,刑無罪,過(禍) 皆反自及也。所伐當罪,其禍五之,所伐不當,其禍什之。國受兵而不知固守,下邪恒以地界為私者□。救人而弗能存,反為禍門,是胃 (謂)危根。……
三雍(壅): 內立(位)朕(勝) 胃(謂)之塞,外立(位)朕(勝)胃(謂)之□,外內皆朕(勝)則君孤直(特)。以此有國,守不固,單(戰)不克。此胃 (謂)一雍(壅)。從中令外[謂之]惑,從外令中胃 (謂)之□。外內遂凈(爭),則危都周,此胃(謂)重雍(壅)。外內為一,國乃更。此謂三雍(壅)。
三兇: 一曰好兇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縱心欲。此胃 (謂)[三兇。昧]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抹(昧)一國之利者,受一國之禍。約而倍之,胃 (謂)之襦傳。伐當罪,見利而反,胃 (謂)之達刑。上殺父兄,下走子弟,胃 (謂)之亂首。外約不信,胃 (謂)之怨媒。有國將亡,當□□昌。
[鑒賞]
《經法》是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4種失傳2千余年的古佚書之一。分《道法》、《國次》、《君正》、《亡論》等9篇。無編者和年代。歷史學家考證認為,《經法》與同時出土的《十六經》、《稱》、《道原》四書就是《漢書·藝文志》里列出的《黃帝四經》。故成書年代,當在戰國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400年前后。其作者很可能是鄭國的隱者。
《經法》的主要思想體系,屬黃老學派。主要觀點繼承老子而加以發揮,同時也受到儒、墨思想的影響。從本書收錄的《國次》、《君正》、《亡論》3篇原文來看,該書體現的軍事觀點也是如此。
一、《國次》是帛書《經法》中的第2篇,首句是“國失其次”,因以為篇名。文章圍繞戰爭問題,論述了三個方面的觀點。第一,作者首先提出“天極”(天道的限度)這個觀念。他認為進行征伐,不能違背天極。“誅禁不當”,就是違背天極,必然自受其禍;誅禁得當,就一定要把戰爭進行到底,徹底清除敵人的守備能力。他還提出“先屈后信(伸)”,要人們依時而動。第二,用對比的方法說明進行戰爭的兩種不同的原則及其后果。一種是征服性掠奪性的戰爭。另一種完全相反,勝利之后,“布其資財,散其子女,襲其地土,以封賢者。”就對待戰爭的態度而言,與儒、墨有些距離;就勝利后的處置而言,與法家不大一樣。其關鍵,在于謹守天極,不擅天功。這個天,是黃老之天。第三,“毋陽竊”以下一段,似指進行戰爭的準備和方法策略而言,把內部的團結一心和作戰的剛柔結合等等歸納為五項原則。違反這五項原則,就叫“五逆”,就是過極失當,會招致災禍。
二、《君正》是《經法》的第3篇,論述一國之君如何治國治兵的正確原則,篇名當取此意。本篇首先談到以7年為期,治好國政,創造征戰的條件。這治國的內容,包括順民之欲(收攬民心之一法),選用賢德,也包括減輕賦稅,使民富足,以及加強號令刑罰,等等。作者認為,做到了這些,就可以征戰了;因為這些措施是“因天之生也以養生”,“因天之殺也以伐死”。看來,這一大段是黃老學派廣泛汲取戰國各家加以融合的一種治國治兵思想。接著“人之本在地”一段論述土地和民力、薄賦和富民的重大意義,其基本宗旨接近管仲學派,和商鞅的農戰頗不相類。最后,“法度者”一段,強調法度的重要性,認為是“正之至也”;同時又談到節制賦斂,不奪農時,兼愛得民等等。
三、《亡論》是《經法》中的第7篇,宗旨在于論述國家滅亡的原因,因以名篇。這些亡國的原因包括“六危”、“三不辜”、“三壅”、“三兇”等,概括相當全面。這里節錄了三段。第一段,首先指出防守不能單憑地險,攻戰不能單憑兵強。然后著重闡述“興兵失理”的危害。作者說,如果所伐不當(攻伐無罪之國),屠殺人民,上天要降給大禍;如果所伐當罪,上天會賜給大福。其哲學根據是,“贏極必靜”,這和《老子》的物極必反正好相應。看來,這樣說的目的是利用老子哲學來反對非正義的掠奪戰爭。第二段,講“三壅”的危害,與法家韓非的某些思想有類似之處,強調國君的威權號令必須得到確保,要防范內宮后妃和外朝大臣對國君的包圍和蔽塞;否則,君以不顯,就要出現“守不固,戰不克”的局面,甚至會更換國君。第三段論“三兇”,反對好戰、好勇和貪欲;其中對見利忘義、貪利受禍說得較多,關于“好兇器”、“行逆德”沒有論述,全段文字也有些條理不清,疑有脫誤,以致不易看出全段的中心及其與《老子》某些章節的聯系。








